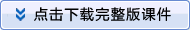第二十四章
新儒家:两个学派的开端
新儒家接着分成两个主要的学派,真是喜人的巧合,这两个学派竟是兄弟二人开创的。他们号称“二程”。弟弟程颐(1033—1108年)开创的学派,由朱熹(1130
—1200年)完成,称为程朱学派,或“理学”。哥哥程颖(1032一1085年)开创的另一个学派,由陆九渊(1139—1193年)继续,王守仁(1473一1529年)完成,称为陆王学派,或“心学”。在二程的时代,还没有充分认识这两个学派不同的意义
,但是到了朱熹和陆九渊,就开始了一场大论战。一直继续到今天。
在以下几章我们会看出,两个学派争论的主题,确实是一个带有根本重要性的哲学问题。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说,这个问题是,自然界的规律是不是人心(或宇宙的心)创制的。这历来是柏拉图式的实在论与康德式的观念论争论的主题,简直可以说,形上学中争论的就是这个主题。这个问题若是解决了,其他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这一章我不打算详细讨论这个争论的主题,只是提示一下它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开端。
程颢的“仁”的观念
程氏兄弟是今河南省人。程颢号明道先生,程颐号伊川先生。他们的父亲是周敦颐的朋友,张载的表兄弟。所以他们年少时受过周敦颐的教诲,后来又常与张载进行讨论。还有,他们住的离邵雍不远,时常会见他。这五位哲学家的亲密接触,
确实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佳话。
程颢极其称赞张载的《西铭》,因为《西铭》的中心思想是万物一体,这也正是程颢哲学的主要观念。在他看来,与万物合一,是仁的主要特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即《西铭》。——引者注)意思乃备言此体
,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匆忘,匆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在第七章,对于在以上引文中提到的孟子的那句话,作过充分的讨沦。“必有事焉”,“勿助长”,这是孟子养浩然之气的方法,也是新儒家极其赞赏的方法。
在程颢看来,人必须首先觉解他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道理。然后,他需要做的一切
,不过是把这个道理放在心中,做起事来诚实地聚精会神地遵循着这个道理。这样的工夫积累多了,他就会真正感觉到他与万物合一。所谓“以诚敬存之”,就是“
必有事焉”。可是达到这个合一,又必须毫无人为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他一定
“未尝致纤毫之力”。
程颢与孟子的不同。在于程颢比孟子更多地给予仁以形上学的解释。“易传”
中有句话;“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传下》)这里的“生”字可以当“产生”
讲,也可以当“生命”讲。在第十五章,把“生”字译作“产生”,是因为这个意思最合“易传”的原意。但是在程颢和其他新儒家看来,“生”的真正意义是“生命”。他们认为万物都有对“生命”的倾向,就是这种倾向构成了天地的“仁”。
中医把麻痹叫做“不仁”。程颢说:“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遗书》卷二上)
所以在程颢看来,从形上学上说,万物之间有一种内在联系。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都不过是我们与他物之间这种联系的表现。可是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不忍人之心”被自私蒙蔽了,或者用新儒家的话说,被
“私欲”,或简言之,“欲”,蒙蔽了。于是丧失了本来的合一。这时候必须做的
,也只是记起自己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并“以诚敬存之”而行动。用这种方法,
本来的合一就会在适当的进程中恢复。这就是程颢哲学的一般观念,后来陆九渊和王守仁详细地发挥了。
程朱的“理”的观念的起源
第八章已经讲过,在先秦时代,公孙龙早已清楚地区分了共相和事物。他坚持说,即使世界上没有本身是白的物,白(共相)也是白(共相)。看来公孙龙已经有一些柏拉图式的观念,即区分了两个世界:永恒的,和有时间性的;可思的,与可感的。可是后来的哲学家,没有发展这个观念,名家的哲学也没有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相反,这个思想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过了一千多年,中国哲学家的注意力才再度转到永恒观念的问题上。这样做的有两个主要的思想家,就是程颢、朱熹。
不过程朱哲学并不是名家的继续。他们并没有注意公孙龙,也没有注意第十九章讲的新道家所讨论的名理。他们直接从“易传”发展出他们的“理”的观念。我在第十五章已经指出,道家的“道”与“易传”的道存在着区别。道家的“道”是统一的最初的“一”,由它生出宇宙的万物。相反,“易传”的道则是多,它们是支配宇宙万物每个单独范畴的原则。正是从这个概念,程朱推导出“理”的观念。
当然,直接刺戟了程朱的,还是张载和邵雍。前一章我们看到,张载用气的聚散,解释具体的特殊事物的生灭。气聚,则万物形成并出现。但是这个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事物有不同的种类。假定一朵花和一匹叶都是气之聚,那么,为什么花是花,叶是叶?我们还是感到茫然。正是在这里,引起了程朱的“理”的观念。程朱认为,我们所见的宇宙,不仅是气的产物,也是理的产物。事物有不同的种类,
是因为气聚时遵循不同的理。花是花,因为气聚时遵循花之理;叶是叶,因为气聚时遵循叶之理。
邵雍的图,也有助于提出理的观念。邵雍以为,他的图所表示的就是个体事物生成变化的规律。这种规律不仅在画图之先,而区在个体事物存在之先。邵雍以为
,伏羲画卦之前,《易》早已存在。二程中有一位说:“尧夫(邵雍的号。——引者注)诗:……‘须信画前原有易,自从删后更无诗。’这个意思古原未有人道来
。”(《遗书》卷二上)这种理论与新实在论者的理论相同,后者以为,在有数学之前已有一个“数学”。
程颐的“理”的观念
张载与邵雍的哲学联合起来,就显示出希腊哲学家所说的事物的“形式”与“
质料”的区别。这个区别,程未分得很清楚。程朱,正如柏拉图、亚力士多德,以为世界上的万物,如果要存在,就一定要在某种材料中体现某种原理。有某物,必有此物之理。但是有某理,则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相应的物。原理,即他们所说的
“理”;材料,即他们所说的“气”。朱熹所讲的气,比张载所讲的气,抽象得多
。
程颐也区别“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两个名词,源出“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系辞传·上》)在程朱的系统中,这个区别相当于西方哲学中“抽象”与“具体”的区别。“理”是“形而上”的“道”,也可以说是“抽象”的;“器”,程朱指个体事物,是“形而下”的,也可以说是“具体
”的。
照程颐的说法,理是永恒的,不可能加减。他说:“这上头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它元无少欠,百理具备。”(《遗书》卷二上)又说:“百理具在平铺放着。
几时道尧尽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尽子道,添得些子道多。元来依旧。”(同上)
程颐还将“形而上”的世界描写为“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同上)。它“冲漠无朕
”,因为其中没有具体事物;它又“万象森然”,因为其中充满全部的理。全部的理都永恒地在那里,无论实际世界有没有它们的实例,也无论人是否知道它们,它们还是在那里。
程颐讲的精神修养方法,见于他的名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遗书》卷十八)我们已经知道,程颢也说学者必须首先认识万物本是一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从此以后,新儒家就以“敬”字为关键,来讲他们的精神修养的方法。于是“敬”字代替了周敦颐所讲的“静”字。在修养的方法论上,以
“敬”代“静”,标志着新儒家进一步离开了禅宗。
第二十二章指出过,修养的过程需要努力。即使最终目的是无须努力,还是需要最初的努力以达到无须努力的状态。禅宗没有说这一点,周敦颐的静字也没有这个意思。可是用了敬字,就把努力的观念放到突出的地位了。
涵养须用敬,但是敬什么呢?这是新儒家两派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下面两章再回转头来讲这个问题。
处理情感的方法
我在第二十章说,王弼所持的理论是,圣人“有情而无累”。《庄子》中也说
:“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王弼的理论似即庄子之言的发挥。
新儒家处理情感的方法,遵循着与王弼的相同的路线。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将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程颢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
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明道文集》卷三)
这是程颢答张载问定性的回信,后人题为《定性书》。程颢说的“廓然而大公
,物来而顺应”,勿“自私”,勿“用智”,与周敦颐说的“静虚动直”,是一回事。讲周敦颐时所举的《孟子》中的例证,在这里一样适用。
从程颖的观点看,甚至圣人也有喜有怒,而且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因为他的心
“廓然大公”,所以一旦这些情感发生了,它们也不过是宇宙内的客观现象。与他的自我并无特别的联系。他或喜或怒的时候,那也不过是外界当喜当怒之物在他心中引起相应的情感罢了。他的心象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任何东西。这种态度产生的结果是,只要对象消逝了,它所引起的情感也随之消逝了。这样,圣人虽然有情,
而无累。让我们回到以前举过的例子。假定有人看见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如果他遵循他的自然冲动,就会立即冲上去救那个小孩。他的成功一定使他欢喜,他的失败也一定使他悲伤。但是由于他的行为廓然大公,所以一旦事情做完了,他的情感也就消逝了。因此,他有情而无累。
新儒家常用的另一个例子,是孔子最爱的弟子颜回的例子,孔子曾说颜回“不迁怒”(《论语·雍也》)。一个人发怒的时候,往往骂人摔东西,而这些人和东西都显然与使他发怒的事完全不相干。这就叫“迁怒”。他将他的怒,从所怒的对象上迁移到不是所怒的对象上。新儒家非常重视孔子这句话,认为颜回的这个品质,
是作为孔门大弟子最有意义的品质,并认为颜回是仅次于孔子的一个完人。因此程颐解释说:“须是理会得因何不迁怒。……譬如明镜,好物来时,便见是好;恶物来时,便见是恶;镜何尝有好恶也。世之人固有怒于室而色于市。……若圣人因物而未尝有怒。……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遗书》卷十八)
可见在新儒家看来,颜回不迁怒,是由于没有把他的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一件事物的作用可能在他心中引起某种情感。正如一件东西可能照在镜子里,但是他的自我并没有与情感联系起来。因而也就无怒可迁。他只对于在他心中引起情感的事物作出反应,但是他的自我并没有为它所累。颜回被人认为是一个快乐的人,对于这一点,新儒家推崇备至。
寻求快乐
我在第二十章说过,新儒家试图在名教中寻求乐地。寻求快乐,的确是新儒家声称的目标之一。例如,程颢说:“昔受学于周茂叔(即周敦颐。——引者注),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遗书》卷二上)事实上,《论语》有许多章就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乐趣,新儒家常常引用的包括有以下几章: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另一章说,有一次孔子与四位弟子一起闲坐,他要他们每个人谈谈自己的志愿
。一位说他想当一个国家的“军政部长”、一位想当“财政部长”,一位想当赞礼先生。第四位名叫曾点,他却没有注意别人在说什么,只是在继续鼓瑟。等别人都说完了,孔子就要他说。他的回答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为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
·先进》“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以上所引的第一章,程颐解释说,“饭疏食饮水”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乐的。这一章意思是说,尽管如此贫穷,孔子仍然不改其乐(见《程氏经说》卷六)。以上所引的第二章,程颢解释说:“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其’宇当玩昧,自有深意。”(《遗书》卷十二)这些解释都是对的,但是没有回答其乐到底是什么。
再看程颐的另一段语录:“鲜于诜(无此字:ocr)问伊川曰:‘颜子何以能不改其乐?’正叔曰:‘颜子所乐者何事?’诜对曰:‘乐道而已。’伊川曰:‘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程颐的这个说法,很像禅师的说法,所以朱熹编《二程遗书》时,不把这段语录编入遗书正文里,而把它编入《外书》里,似乎是编入
“另册”。其实程颐的这个说法。倒是颇含真理。圣人之乐是他的心境自然流露,
可以用周敦颐说的“静虚动直”来形容,也可以用程颢说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来形容。他不是乐道,只是自乐。
新儒家对于圣人之乐的理解,从他们对于上面所引的第三章的解释,可以看出来。朱熹的解释是;“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
,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论语集注》卷六)
我在第二十章曾说,风流的基本品质,是有个超越万物区别的心,在生活中只遵从这个心,而不遵从别的。照朱熹的解释,曾点恰恰是这种人。他快乐,因为他风流。在朱熹的解释里,也可以看出新儒家的浪漫主义成分。我说过,新儒家力求于名教中寻乐地。但是必须同时指出,照新儒家的看法“名教”并不是“自然”的对立面,而无宁说是“自然”的发展。新儒家认为,这正是孔孟的主要论点。
要实现这种思想,新儒家的人成功了没有呢?成功了。他们的成功,可以从以下两首诗看出来,一首是邵雍的诗,一首是程颢的诗。邵雍是个很快乐的人,程颢称他是“风流人豪”。他自名其住处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他的诗,
题为《安乐吟》,诗云:
安乐先生,不显姓氏。
垂三十年,居洛之俟(无此字:ocr)。
风月情怀,江湖性气。
色斯其举,翔而后至。
无贱无贫,无富无贵。
无将无迎,无拘无忌。
窘未尝忧,饮不至醉。
收天下春,归之肝肺。
盆池资吟,瓮牖荐睡。
小车赏心,大笔快志。
或戴接篱,或著半臂。
或坐林间,或行水际。
乐见善人,乐闻善事。
乐道善言,乐行善意。
闻人之恶,若负芒刺。
闻人之善,如佩兰蕙。
不侵禅伯,不谈方士。
不出户庭,直际天地。
三军莫凌,万钟莫致。
为快活人,六十五岁。
(《伊川击壤集》卷十四)
程颢的诗题为《秋日偶成》,诗云: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明道文集》卷一)
这样的人是不可征服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是“豪雄”。可是他们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豪雄”,他们是“风流人豪”。
在新儒家中,有些人批评邵雍,大意是说他过分卖弄其乐。但是对程颢从来没有这样的批评。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在这里找到了中国的浪漫主义(风流)与中国的古典主义(名教)的最好的结合。
新儒家:两个学派的开端
新儒家接着分成两个主要的学派,真是喜人的巧合,这两个学派竟是兄弟二人开创的。他们号称“二程”。弟弟程颐(1033—1108年)开创的学派,由朱熹(1130
—1200年)完成,称为程朱学派,或“理学”。哥哥程颖(1032一1085年)开创的另一个学派,由陆九渊(1139—1193年)继续,王守仁(1473一1529年)完成,称为陆王学派,或“心学”。在二程的时代,还没有充分认识这两个学派不同的意义
,但是到了朱熹和陆九渊,就开始了一场大论战。一直继续到今天。
在以下几章我们会看出,两个学派争论的主题,确实是一个带有根本重要性的哲学问题。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说,这个问题是,自然界的规律是不是人心(或宇宙的心)创制的。这历来是柏拉图式的实在论与康德式的观念论争论的主题,简直可以说,形上学中争论的就是这个主题。这个问题若是解决了,其他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这一章我不打算详细讨论这个争论的主题,只是提示一下它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开端。
程颢的“仁”的观念
程氏兄弟是今河南省人。程颢号明道先生,程颐号伊川先生。他们的父亲是周敦颐的朋友,张载的表兄弟。所以他们年少时受过周敦颐的教诲,后来又常与张载进行讨论。还有,他们住的离邵雍不远,时常会见他。这五位哲学家的亲密接触,
确实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佳话。
程颢极其称赞张载的《西铭》,因为《西铭》的中心思想是万物一体,这也正是程颢哲学的主要观念。在他看来,与万物合一,是仁的主要特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即《西铭》。——引者注)意思乃备言此体
,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匆忘,匆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在第七章,对于在以上引文中提到的孟子的那句话,作过充分的讨沦。“必有事焉”,“勿助长”,这是孟子养浩然之气的方法,也是新儒家极其赞赏的方法。
在程颢看来,人必须首先觉解他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道理。然后,他需要做的一切
,不过是把这个道理放在心中,做起事来诚实地聚精会神地遵循着这个道理。这样的工夫积累多了,他就会真正感觉到他与万物合一。所谓“以诚敬存之”,就是“
必有事焉”。可是达到这个合一,又必须毫无人为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他一定
“未尝致纤毫之力”。
程颢与孟子的不同。在于程颢比孟子更多地给予仁以形上学的解释。“易传”
中有句话;“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传下》)这里的“生”字可以当“产生”
讲,也可以当“生命”讲。在第十五章,把“生”字译作“产生”,是因为这个意思最合“易传”的原意。但是在程颢和其他新儒家看来,“生”的真正意义是“生命”。他们认为万物都有对“生命”的倾向,就是这种倾向构成了天地的“仁”。
中医把麻痹叫做“不仁”。程颢说:“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遗书》卷二上)
所以在程颢看来,从形上学上说,万物之间有一种内在联系。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都不过是我们与他物之间这种联系的表现。可是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不忍人之心”被自私蒙蔽了,或者用新儒家的话说,被
“私欲”,或简言之,“欲”,蒙蔽了。于是丧失了本来的合一。这时候必须做的
,也只是记起自己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并“以诚敬存之”而行动。用这种方法,
本来的合一就会在适当的进程中恢复。这就是程颢哲学的一般观念,后来陆九渊和王守仁详细地发挥了。
程朱的“理”的观念的起源
第八章已经讲过,在先秦时代,公孙龙早已清楚地区分了共相和事物。他坚持说,即使世界上没有本身是白的物,白(共相)也是白(共相)。看来公孙龙已经有一些柏拉图式的观念,即区分了两个世界:永恒的,和有时间性的;可思的,与可感的。可是后来的哲学家,没有发展这个观念,名家的哲学也没有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相反,这个思想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过了一千多年,中国哲学家的注意力才再度转到永恒观念的问题上。这样做的有两个主要的思想家,就是程颢、朱熹。
不过程朱哲学并不是名家的继续。他们并没有注意公孙龙,也没有注意第十九章讲的新道家所讨论的名理。他们直接从“易传”发展出他们的“理”的观念。我在第十五章已经指出,道家的“道”与“易传”的道存在着区别。道家的“道”是统一的最初的“一”,由它生出宇宙的万物。相反,“易传”的道则是多,它们是支配宇宙万物每个单独范畴的原则。正是从这个概念,程朱推导出“理”的观念。
当然,直接刺戟了程朱的,还是张载和邵雍。前一章我们看到,张载用气的聚散,解释具体的特殊事物的生灭。气聚,则万物形成并出现。但是这个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事物有不同的种类。假定一朵花和一匹叶都是气之聚,那么,为什么花是花,叶是叶?我们还是感到茫然。正是在这里,引起了程朱的“理”的观念。程朱认为,我们所见的宇宙,不仅是气的产物,也是理的产物。事物有不同的种类,
是因为气聚时遵循不同的理。花是花,因为气聚时遵循花之理;叶是叶,因为气聚时遵循叶之理。
邵雍的图,也有助于提出理的观念。邵雍以为,他的图所表示的就是个体事物生成变化的规律。这种规律不仅在画图之先,而区在个体事物存在之先。邵雍以为
,伏羲画卦之前,《易》早已存在。二程中有一位说:“尧夫(邵雍的号。——引者注)诗:……‘须信画前原有易,自从删后更无诗。’这个意思古原未有人道来
。”(《遗书》卷二上)这种理论与新实在论者的理论相同,后者以为,在有数学之前已有一个“数学”。
程颐的“理”的观念
张载与邵雍的哲学联合起来,就显示出希腊哲学家所说的事物的“形式”与“
质料”的区别。这个区别,程未分得很清楚。程朱,正如柏拉图、亚力士多德,以为世界上的万物,如果要存在,就一定要在某种材料中体现某种原理。有某物,必有此物之理。但是有某理,则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相应的物。原理,即他们所说的
“理”;材料,即他们所说的“气”。朱熹所讲的气,比张载所讲的气,抽象得多
。
程颐也区别“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两个名词,源出“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系辞传·上》)在程朱的系统中,这个区别相当于西方哲学中“抽象”与“具体”的区别。“理”是“形而上”的“道”,也可以说是“抽象”的;“器”,程朱指个体事物,是“形而下”的,也可以说是“具体
”的。
照程颐的说法,理是永恒的,不可能加减。他说:“这上头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它元无少欠,百理具备。”(《遗书》卷二上)又说:“百理具在平铺放着。
几时道尧尽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尽子道,添得些子道多。元来依旧。”(同上)
程颐还将“形而上”的世界描写为“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同上)。它“冲漠无朕
”,因为其中没有具体事物;它又“万象森然”,因为其中充满全部的理。全部的理都永恒地在那里,无论实际世界有没有它们的实例,也无论人是否知道它们,它们还是在那里。
程颐讲的精神修养方法,见于他的名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遗书》卷十八)我们已经知道,程颢也说学者必须首先认识万物本是一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从此以后,新儒家就以“敬”字为关键,来讲他们的精神修养的方法。于是“敬”字代替了周敦颐所讲的“静”字。在修养的方法论上,以
“敬”代“静”,标志着新儒家进一步离开了禅宗。
第二十二章指出过,修养的过程需要努力。即使最终目的是无须努力,还是需要最初的努力以达到无须努力的状态。禅宗没有说这一点,周敦颐的静字也没有这个意思。可是用了敬字,就把努力的观念放到突出的地位了。
涵养须用敬,但是敬什么呢?这是新儒家两派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下面两章再回转头来讲这个问题。
处理情感的方法
我在第二十章说,王弼所持的理论是,圣人“有情而无累”。《庄子》中也说
:“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王弼的理论似即庄子之言的发挥。
新儒家处理情感的方法,遵循着与王弼的相同的路线。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将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程颢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
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明道文集》卷三)
这是程颢答张载问定性的回信,后人题为《定性书》。程颢说的“廓然而大公
,物来而顺应”,勿“自私”,勿“用智”,与周敦颐说的“静虚动直”,是一回事。讲周敦颐时所举的《孟子》中的例证,在这里一样适用。
从程颖的观点看,甚至圣人也有喜有怒,而且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因为他的心
“廓然大公”,所以一旦这些情感发生了,它们也不过是宇宙内的客观现象。与他的自我并无特别的联系。他或喜或怒的时候,那也不过是外界当喜当怒之物在他心中引起相应的情感罢了。他的心象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任何东西。这种态度产生的结果是,只要对象消逝了,它所引起的情感也随之消逝了。这样,圣人虽然有情,
而无累。让我们回到以前举过的例子。假定有人看见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如果他遵循他的自然冲动,就会立即冲上去救那个小孩。他的成功一定使他欢喜,他的失败也一定使他悲伤。但是由于他的行为廓然大公,所以一旦事情做完了,他的情感也就消逝了。因此,他有情而无累。
新儒家常用的另一个例子,是孔子最爱的弟子颜回的例子,孔子曾说颜回“不迁怒”(《论语·雍也》)。一个人发怒的时候,往往骂人摔东西,而这些人和东西都显然与使他发怒的事完全不相干。这就叫“迁怒”。他将他的怒,从所怒的对象上迁移到不是所怒的对象上。新儒家非常重视孔子这句话,认为颜回的这个品质,
是作为孔门大弟子最有意义的品质,并认为颜回是仅次于孔子的一个完人。因此程颐解释说:“须是理会得因何不迁怒。……譬如明镜,好物来时,便见是好;恶物来时,便见是恶;镜何尝有好恶也。世之人固有怒于室而色于市。……若圣人因物而未尝有怒。……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遗书》卷十八)
可见在新儒家看来,颜回不迁怒,是由于没有把他的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一件事物的作用可能在他心中引起某种情感。正如一件东西可能照在镜子里,但是他的自我并没有与情感联系起来。因而也就无怒可迁。他只对于在他心中引起情感的事物作出反应,但是他的自我并没有为它所累。颜回被人认为是一个快乐的人,对于这一点,新儒家推崇备至。
寻求快乐
我在第二十章说过,新儒家试图在名教中寻求乐地。寻求快乐,的确是新儒家声称的目标之一。例如,程颢说:“昔受学于周茂叔(即周敦颐。——引者注),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遗书》卷二上)事实上,《论语》有许多章就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乐趣,新儒家常常引用的包括有以下几章: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另一章说,有一次孔子与四位弟子一起闲坐,他要他们每个人谈谈自己的志愿
。一位说他想当一个国家的“军政部长”、一位想当“财政部长”,一位想当赞礼先生。第四位名叫曾点,他却没有注意别人在说什么,只是在继续鼓瑟。等别人都说完了,孔子就要他说。他的回答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为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
·先进》“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以上所引的第一章,程颐解释说,“饭疏食饮水”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乐的。这一章意思是说,尽管如此贫穷,孔子仍然不改其乐(见《程氏经说》卷六)。以上所引的第二章,程颢解释说:“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其’宇当玩昧,自有深意。”(《遗书》卷十二)这些解释都是对的,但是没有回答其乐到底是什么。
再看程颐的另一段语录:“鲜于诜(无此字:ocr)问伊川曰:‘颜子何以能不改其乐?’正叔曰:‘颜子所乐者何事?’诜对曰:‘乐道而已。’伊川曰:‘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程颐的这个说法,很像禅师的说法,所以朱熹编《二程遗书》时,不把这段语录编入遗书正文里,而把它编入《外书》里,似乎是编入
“另册”。其实程颐的这个说法。倒是颇含真理。圣人之乐是他的心境自然流露,
可以用周敦颐说的“静虚动直”来形容,也可以用程颢说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来形容。他不是乐道,只是自乐。
新儒家对于圣人之乐的理解,从他们对于上面所引的第三章的解释,可以看出来。朱熹的解释是;“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
,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论语集注》卷六)
我在第二十章曾说,风流的基本品质,是有个超越万物区别的心,在生活中只遵从这个心,而不遵从别的。照朱熹的解释,曾点恰恰是这种人。他快乐,因为他风流。在朱熹的解释里,也可以看出新儒家的浪漫主义成分。我说过,新儒家力求于名教中寻乐地。但是必须同时指出,照新儒家的看法“名教”并不是“自然”的对立面,而无宁说是“自然”的发展。新儒家认为,这正是孔孟的主要论点。
要实现这种思想,新儒家的人成功了没有呢?成功了。他们的成功,可以从以下两首诗看出来,一首是邵雍的诗,一首是程颢的诗。邵雍是个很快乐的人,程颢称他是“风流人豪”。他自名其住处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他的诗,
题为《安乐吟》,诗云:
安乐先生,不显姓氏。
垂三十年,居洛之俟(无此字:ocr)。
风月情怀,江湖性气。
色斯其举,翔而后至。
无贱无贫,无富无贵。
无将无迎,无拘无忌。
窘未尝忧,饮不至醉。
收天下春,归之肝肺。
盆池资吟,瓮牖荐睡。
小车赏心,大笔快志。
或戴接篱,或著半臂。
或坐林间,或行水际。
乐见善人,乐闻善事。
乐道善言,乐行善意。
闻人之恶,若负芒刺。
闻人之善,如佩兰蕙。
不侵禅伯,不谈方士。
不出户庭,直际天地。
三军莫凌,万钟莫致。
为快活人,六十五岁。
(《伊川击壤集》卷十四)
程颢的诗题为《秋日偶成》,诗云: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明道文集》卷一)
这样的人是不可征服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是“豪雄”。可是他们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豪雄”,他们是“风流人豪”。
在新儒家中,有些人批评邵雍,大意是说他过分卖弄其乐。但是对程颢从来没有这样的批评。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在这里找到了中国的浪漫主义(风流)与中国的古典主义(名教)的最好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