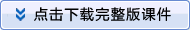灌溉系统自主治理与不对称问题的解决
[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罗伊·加德纳 著
校者按:本文是美国政治学家、公共行政学家和新制度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其合作者有关水资源问题研究的重要论文之一。该文的特色是运用博弈模型和实证研究方法,以灌溉系统为例,探讨在公共池塘资源使用者相互不对称条件下,何种自主治理制度能够使公共池塘资源能够得以持续开发和发展。作者最后指出,外部力量的干预,往往因为改变了使用者之间的博弈地位,以及由于其缺乏地方知识,难以设计适用的制度规则,而使得情形更糟。中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灌溉系统往往由于缺乏适当的制度结构而难以可持续地得以开发和发展。许多地方都在为争水而械斗,而这都与分水缺乏合理且有效的制度规则结构相关;严重的黄河断流,也无疑与上下游的博弈格局不对称,上游无意节水,下游难以对上游施加影响有关。本文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发生的包括黄河断流问题在内的因灌溉系统使用者博弈地位不对称而造成的“公地灾难”(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本文是校者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公共政策的制度基础”的翻译成果。本文原文载于美国《经济观察》杂志1993年秋第7卷第4期。中文版权已经获得版权所有者的许可。
导 言
公共池塘资源是指具有非排他性和产出可减少性的自然或人造资源(Gardner, E.Ostrom and Walker, 1990)。这类物品具有两个特性,即非排他性和产出可减少性。它的第一个特性非排他性和纯公益物品的特点相似,而第二个特性产出可减少性又与纯私益物品具有相似的特点。这些大量的公共池塘资源,其自然形式各异,规模小的如沿海渔场、灌溉系统和牧场,大的如海洋和生物圈。
公共池塘资源第一个特性非排他性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包括分配和圈占资源所花费的成本,以及为实现对资源的排他性占有而进行的产权设计以及实施所花费的成本。如果排他性不结合以适当的制度安排,那么在公共池塘资源供给过程中,就会出现搭便车行为。如果非贡献者与贡献者能得到相同的收益,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理性行为会有助于维护自然资源系统呢?公共池塘资源的供给程度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取决于偏好是如何显示和加总的,并与资源的流动性相关。
公共池塘资源第二个特性产出可减少性是理解如何产生“公地悲剧”机制的关键。一个人从公共池塘资源中占有一定的份额,如多少水、多少吨鱼、多少捆草料,那么其他人就不能再占有这些。这样,除非利用制度转变占有者面对的这种激励,否则人们只会不断地去过度占用。例如,那些把湖中现有的鱼全都打尽的渔民获取了所有的收益,而渔业资源耗尽所造成的损失却要与所有其他渔民来共同分担。这样的话,他们所获得的个人收益与分担到自己身上的那份社会损失相比较,个人收益大于应承担的社会损失,出现不均衡。或者,换个说法,如此则没有哪个渔民会对自身行为加以约束以防止渔业资源的耗竭。这样,除非对这种激励加以制度的约束,否则渔业资源必然会沦于灭绝的边缘。
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重要基础设施供给的搭便车行为被认为是实现经济成功发展的主要障碍。戴维·弗里曼(David Freeman, 1990: 115)对灌溉中的这一问题进行了准确的描述:
“个人理性效用追求者的逻辑与社群效用逻辑是不一致的。比如,如果农民各自都觉得需要改进他们有问题而水流不畅的渠道。根据个人理性,他们不会采取改善的举动。因为数量众多的农民,每个都这样盘算:如果一个农民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对流经他自己土地上的那段河渠加以改善,但其他农民并不协调行动,也作出相应的投资的话,那么他提高水的供给和控制(集体物品)的回报是微乎其微的。
相反,如果很多农民在他们的地块都采取措施加以改善,而有一个农民作为个人理性决策者并不这样做,他仍然会不付任何代价然而却能从其他农民所提供的收益中享有一定的份额。所以,无论如何,理性的、专为自己打算的人都会选择不采取任何措施。尽管有关人对提高河渠的潜在收益都拥有完全和准确的信息,并具备所需的知识和资源,而集体物品仍然不会自动地生产出来。”
使问题更麻烦的是,为了长期维护一个灌溉系统需要劳动和资金的不断投入,而收益却难以衡量,并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动越加分散。不管官方或农民为灌溉系统建立了什么样的分配规则,农民总是想暗地里占有比规定更多的水,在不属于分配给自己的时间里取水,或投入少于按规定对于水资源分配需要做的相应投入。比如,种水稻的农民喜欢让自己的水田总是灌满水,因为水稻极需水而不能忍受干旱。更多的水还能够使杂草得到控制,并能更有效地增加稻米的产出。
实地的和实验的经验证据充分表明,没有有效的制度,公共池塘资源将处于低度供给和过度使用的状态(Cordell, 1978; E. Ostrom, Gardner and Walker, 1993; Clark, 1974; Larson and Bromley, 1990)。但是,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存在大量的分歧。很多分析家认为,公共池塘资源占用者陷入了一个霍布斯自然状态,他们不能自己制定规则去控制他们所面对的不合理的激励。这种观点的逻辑结论就是建议由一个外部权威即所谓的政府去接管公地。而且,当技术知识和规模经济发展起来的时候,这一外部力量就应该是一个大的中央政府。农村地区有权有势的人较少参与集体投资但却想获得不相称的收益,要打破他们的控制,必须要有中央政府的干预。这样,政府将进行广泛的政策干预,从影响市场,到直接管理公共池塘资源。
理论假设提供集体物品,组织集体行动,如提供灌溉工程,需要一个外部的中央政府。殖民经历强化了这一假设。在殖民时代,亚洲的很多地方和非洲的一些地方,建立了大规模的政府机构去开发早先没有灌溉系统的区域。这些区域向拓荒者开放,并转而生产用于出口的经济作物。水利灌溉设施的兴修使得政府权力不断集中。在很多情况下,随着殖民统治退出舞台,这一趋势为随后建立的政府所继续。但是,在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和治理权集中于国家,同时地方权利和创制权衰落了,这高度扭曲了”灌溉的发展(Barker et al., 1984: 26)。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全国政府逐渐被认为是水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所有者”(Sawyer, 1992)。根据这一观点,全国政府成了唯一应该或能够投资于建设和管理灌溉系统的机构。第二个假定认为,提供灌溉系统所需要的相当专门的技术,这是地方所难以具备的,这强化了中央集权是必要的观点。所有这些使人相信“稀缺的专门技术存在于强有力的国家机构中,只有在那里专门技术才能得以有效使用”(Barker et al., 1984: 26)。国际援助机构乐于直接与政府的中央部委打交道,通过它们分发援助资金。这种做法强化了一个偏好,就是对灌溉水资源供给进行专业性的中央控制。
近来很多研究对占用者不能设定规则影响公共池塘资源使用的理论假设提出了挑战。很多实地和实验的经验证据证实,占用者常常制定和实施他们自己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很起作用。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这些群体,其占用者之间的有关财产、收益和物质条件的主要关系是对称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所面对的问题是较易于解决的。占用者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放下正在做的操作决策,转而设计规则以提高他们所能获得的共同产出(E. Ostrom, 1990; E. Ostrom, Gardner and Walker, 1993; Berkes, 1989; V. Ostrom, Feeny and Picht, 1993; Berkes et al., 1989; McCay and Acheson, 1987; Wade, 1988; Bromley, 1992)。例如,西班牙、日本和瑞士的一些地方性社群,地方占用者多少世纪以来,设计、监督和实施规则,以维持集中使用公共池塘资源(Maass and Anderson, 1986; Mckean, 1992; Netting, 1981)。
现在,我们就碰到了较棘手的问题,它们集中于个人是否能够制定规则以提高共同产出,公平分配这些产出,而这些人的经济或政治资产、信息或物质关系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Johnson and Libecap, 1982; Keohane, McGinnis and E. Ostrom, 1993)。当然,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所以这一研究计划的任务就是对这一系列的条件形成统一认识。当个人之间存在大量差异时,这些条件提高或降低自主组织的能力。
具体来说,本文集中于大部分灌溉系统中存在的那种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水源和远离水源的农民之间所产生的非对称性。本文首先解释灌溉系统上游和下游农民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他们是否决定出力维护灌溉系统,以及如何在各方之间讨价还价,从而为各方带来好处。最后,我们对尼泊尔的灌溉制度进行经验考察,并讨论我们的调查结果的更为广泛的实际意义。
灌溉的自然状态博弈
在大规模集中建造的灌溉系统中,分别位于上游和下游的农民的位置截然不同。狭隘自私的上游农民可能不管其行动是否引起下游农民水资源的短缺。如果上游农民占用了大部分水,那么下游的农民将更少有理由愿意对灌溉系统进行长期的维护。所有的公共池塘资源都会产生占用和供应的问题。对于灌溉系统来说,占用问题就是对农业生产的水资源的分配;供应问题是指灌溉系统的维持运行。灌溉系统上游农民和下游农民之间存在着非对称性,这增加了长期维护灌溉系统的难度。
我们对灌溉系统中上游农民(局中人1)和下游农民(局中人2)相互策略的互动建立了如下模型:有一个临时建筑的渠首工程,灌溉系统靠它把水引入整个系统。这一设施需要每年维修。引入系统的总的水量W取决于上游农民提供的劳动量L1和下游农民提供的劳动量L2。提供劳动的决策处于完全信息的条件下。一旦水流入,上游农民首先享用,从而占用了最大份额,即75%,而下游农民占有剩下的部分,为25%。整个灌溉系统提供一单位劳动的机会成本是常数,为1。
因为系统中上游和下游每一个方面的收益都与上下游的共同行为有关。这样,他们所面对的情形就是一个博弈。但是系统上下游所具有的激励是不一样的。上游农民占据有利的地理位置,能够取得大部分水。对于上游农民劳动的一阶条件是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其机会成本(.75/=1)。对于下游农民劳动的一阶条件是他的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边际成本(.25/=1)。在正常的凹性假定条件下,一阶条件表明上游农民比下游农民提供更多的劳动。我们应该观察上游农民长期的行为模式,即贡献较多的劳动,并获得较多的水。
这一模型用尼泊尔的桑比西(Thambesi)灌溉系统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灌溉系统是由农民管理的。桑比西河提供水源,从而易于开辟水道,这样每年就需要较少的维护(不像大部分农民管理的系统)。桑比西灌溉系统的渠首工程是一个简单的灌木和石块构成的分流工程,它很容易根据水源的变化每年进行调整(Yoder, 1985: 129)。季风雨来临之前的常规维护只需要“所有成员参加仅4到5个小时的工作”(180)。所以,只需要部分农民就可以维持该系统的运行。这样,“拥有下游土地的农民就不能以不参与维护系统和其他行动来要胁那些拥有在他们之上的土地的人,要求给予他们等量的水”(179)。
桑比西是那种为数不多的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之一,这种系统明确地在系统中建立上游农民对其他农民具有优先权。在每一次灌溉中,前面的农民总是比后面的农民先把自己的田灌满水(Yoder, 1986: 292)。在季风雨季来临之前,系统的上游农民种植需要大量水的稻米。其他农民则不能种植灌溉作物。如果上游农民不种植水稻,而种植小麦,那么在季风雨来临之前就可以灌溉10倍以上的土地(313)。在这一系统中,谷物产出量与位置上离渠首工程的距离相关。大量可以进行灌溉的土地主要靠降雨。
上游农民比下游农民作出更多付出的博弈均衡,从产出低于最佳产出和系统未得到充分维护的意义上来说,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下游农民取得的水少,付出的劳动也少,整个系统就遭受损失。这些考虑表明灌溉者有充分的理由摆脱自然状态,并重新构造他们自己的系统,设计需要遵守的较好的规则。实际上,当均衡处于极其无效时,这时寻求建立新的制度的激励就最大。下面,我们来考察博弈规则的谈判问题。
博弈规则的谈判
处于比桑比西系统需要更多劳动投入系统的农民,如果他们控制和管理自己灌溉系统的权利被确定下来,或至少不被干预,他们就可以在季节之间抽出时间设法增加和改革原有规则,从而提高系统的效果(Gardner and E. Ostrom, 1991)。由灌溉者参加的年度大会来决定规则,而规则的决定将影响系统的占用和供应活动。这可以概括为谈判问题。如果在这些年度会议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那么灌溉则将回到先前所讨论的自然状态的博弈均衡。
谈判的挑战是为了寻求比以前的自然状态均衡对各方较有利的结果。所以,如果各方都未得到改善,他们将不会接受交易。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数值例子来说明这一思想。水资源生产函数是W=2(L10.5+L20.5)。整个系统的目标函数是,以较小的劳动的机会成本,使水资源的供给最大化,也就是说使W_L1_L2最大化。当系统中农民的劳动边际产出等于其机会成本1时,得到最优解。求解一阶条件,我们得到系统中上下游农民供给1单位劳动就产出4单位水。与自然状态的均衡相比较,上游农民将提供0.56个单位的劳动,下游农民提供0.06个单位的劳动,这时只产出2个单位的水。劳动远未实现充分的供给,水资源供给只达到应有供给的一部分。在这些水资源供给中,75%(1.5个单位)提供给了上游农民,25%(0.5个单位)提供给了下游农民。
在这种情况下,谈判是由水资源和劳动的替换所构成的。也就是说,上游农民愿意付出更多的劳动,下游农民也是一样。与之相交换,上游农民将得到较多一些的水资源。一种可能的谈判结果如下:上游农民增加0.86的劳动,下游农民增加0.98的劳动,这使他们都达到1单位的劳动,达到最优的劳动投入。与增加的劳动相对应,水资源也相应增加。下游农民将得到新增水资源的0.94/(0.44+0.94)=0.68,到达下游农民地域的水将从0.5上升到0.5+0.68(2)=1.86,而上游的农民将由此达到1.5+0.32(2)=2.14个单位的水资源。每个人都得到了较多的水。
这一谈判结果有重要的经验意义。可以看出由于谈判,分配给上游农民的水量和分配给下游农民的水量之间的差距缩小了。在自然状态下,这一差距是1.5-0.5=1;而谈判后只有2.14-1.86=0.28。尽管差距仍然存在,但它大大下降了(0.36)。这一水资源分配差距的缩小数量值将在经验证据中表现出来。下一节将验证这一假设,即在农民有权安排协议的系统中,上游农民和下游农民所获得的水资源差距较小。
实地有几个因素会影响上游农民和下游农民之间的谈判。例如,如果渠首工程是永久性的,使劳动需求彻底减少了,这样就会有利于上游农民而不利于下游农民,从而使谈判破裂。上游农民靠自己就可以维持整个系统,他就可以对水资源进行随心所欲地占用。这样一个供给的非对称性强化了位置的非对称性。另一方面,如果存在真正依赖,下游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就会抵消上游农民分配上的优势。这样非对称性将相互抵消,谈判结果相对来说会趋于对称。
在对称的情况下,在实际操作上有一整套轮灌规则用来使灌溉者均衡地分配水和劳动。如下面有两种轮灌规则可以保证自然状态的博弈转化为具有对称性的谈判结果的博弈。
根据轮灌规则A,在奇数年份,水先供应上游农民,在偶数年份,水先供应下游农民。为了维护灌溉系统,上游农民和下游农民任何时候都共同劳动。有一个相似规则的例子,它是基于季节而不是年份,那就是尼泊尔马士塘(Mustang)区域的马法(Marpha)农民管理系统。在此冬天种植大麦,夏天种植荞麦。种大麦的土地是按照先上游后下游的原则来灌溉的,而种荞麦的土地灌溉顺序正好相反,先下游后上游,下游地块先获得水资源(Messerschmidt, 1986)。
根据轮灌规则B,在季节的偶数日,系统所有水都分配给上游农民,而季节的奇数日,则全分配给下游农民。对于水渠的维护,上游农民维护一段时间,下游农民维护一段时间,两者的时间相等。这一规则可以用杨帕芬特(Yampaphant)系统加以说明。
这两种规则都导致一种占用权利和供给义务的均等分割。不管是否明确地写出来,这种形式的轮换规则是农民管理系统中所有参与者的共识。此外,农民主动彼此监督对这些规则的遵守(Weissing and E. Ostrom, 1991, 1993)。
经过一段时间,这些规则能够很容易地调整为水资源和劳动按不均等但成比例的方式进行分配。例如,轮换规则A可能被改进为,在不能被3整除的年份,水资源首先供应上游农民,而在能被3整除的年份,水资源首先供应下游农民。在共同维护灌溉系统方面,上游农民提供两倍于下游农民的劳动。类似的,轮换规则B转化为这样的形式,就是在季节中不能被3整除的天数里,系统中所有的水资源都分配给上游农民,在季节中能被3整除的天数里,系统中所有的水资源都分配给下游农民。上游农民用于维修水渠花费的时间两倍于下游农民。
当然,在实地环境下实际发现的规则并不是这样呆板的。它里面包含的轮换常常要复杂得多。与固定的维护有关的规则也远不同于那些与紧急修理有关的规则。同时,比例也可以是多维的,水资源的分配比例是一个变量,劳动供给比例是另一个变量。构成比例基础的变量集可以包括土地的拥有,家庭户数量,田间劳动,物质资本和在一个投票系统中拥有的选票。当规则是基于一个明确的比例原则基础上,而且所有参与者意识到这些规则使他们能够比可行的“自然状态”博弈情况下得到更好的结果;同时,所有人都准备对违反规则人员进行处罚。这时,较高产出的均衡实现了,并长期得以维持。尽管任何给定的一个灌溉系统其细节看起来是多么复杂难懂,从实地得来的数据却表明,我们上面所揭示的策略原则是一个反复起作用的规则。现在我们来讨论经验数据。
经验证据
对这些种种理论结果进行经验测试是困难的。所获得的净收益水平,灌溉系统中上游和下游之间的分配,其存续的时间,效率和公平程度,在这些方面人们可以看到存在着巨大的结果差异。现实世界存在着大量复杂的变量,这增加了这一风险,即理论的错误可以通过事后引入一个新的解释变量得到辩护。直到最近,没有具有适当变量的大型数据库能够用于这一目的。我们在尼泊尔收集了农民和政府管理的灌溉系统的大量数据,由此建立了尼泊尔制度和灌溉系统数据库。在这一数据库中记录了127个灌溉系统的资料(E.Ostrom, Benjamin and Shivakoti, 1992)。
尼泊尔国土面积141 000平方公里,略大于英格兰。其1800万居民大部分从事农业。在大约650 000公顷灌溉面积中,由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占大约400 000公顷,也就是62%(Small, Adriano and Martin, 1986)。剩下的灌溉区域是由各类机构管理的灌溉系统,其中很多是1950年以来由各类捐献者资助建设的。在一些机构管理的系统中,农民自主组织起来,进行第二层次的规则选择博弈。但是,在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中,他们设计占用和供应规则的积极性较高。
在山地(常常十分陡峭)、在河谷(地面波浪起伏),以及在只是由于成功地根除了瘴气才被广泛用于农业生产的国土南部的平坦和较肥沃的泰拉(Terai)地区,灌溉是很普遍的。在山地灌溉系统中,有几个块高地,在那里第一级高地的农民很容易得到水。在水流到第二级和第三级高地之前,第一级高地的农民把大部分的水都灌进了他们的地里。由此,人们认为这种地理方面的非对称性问题在泰拉地区要比山区容易处理一些。
在尼泊尔,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获得的农业生产率水平较高。在尼泊尔数据库的127个灌溉系统中,有108个系统有生产率数据。86个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平均每年每公顷6吨;22个机构管理的灌溉系统每公顷5吨,统计显著性水平p=0.05。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倾向于有较高的种植密度。作物100%的密度意味着灌溉系统的所有土地在一季中被充分使用,或者多季中被部分使用以致于达到同样的作为覆盖面积。类似地,作物200%的密度就是二季的充分使用;300%就是土地三季里充分使用。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的平均种植密度(247%)比政府机构管理的灌溉系统(208%)高。这一差异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农民的农业产出和种植密度依赖于在冬季和春季当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的时候水资源的供应能否得到充分的保证。如表1所示的,在尼泊尔,有一个较高的百分比,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中上游和下游农民在所有三个季节中都能够得到充足的水资源。在水资源特别缺乏的春季,大约四分之一的农民管理系统能够保证足够的水资源到达系统下游的农民,而机构管理的灌溉系统的这一比例只有十二分之一。在夏季季风雨季,大约只有一半机构管理的灌溉系统能够有足够的水资源供给下游农民,而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却能够达到差不多90%。显然,大部分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进行了大量的谈判,通过采用自己公认的明晰的规则,从而得以避免自然状态的博弈,并取得高水平的均衡。
为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比机构管理的灌溉系统较可能在上游农民和下游农民之间进行公平分配,我们进行了一项回归分析。这一分析表明物质变量和治理结构类型如何结合起来,共同影响管理系统上游和下游农民所获得的水资源的差异的。
在我们的回归模型中,因变量称为“水资源获取差别”。这个变量是系统所获水量,再经三季平均。我们用三种可能性来度量水资源的获取量:足够的得2分,有限的得1分,稀缺或没有得0分。总的得分0分表明,在所有三个季节中,系统的上游和下游水的足够程度是一样的。0.33分表明,在一个季节中,上游得到足够的水而下游得到有限的水,或上游得到有限的水而下游缺水。
回归模型中的自变量包括系统水渠的长度(单位米)、劳动力投入(每年投入到常规维护的劳动日数除以家庭数);四个样本变量,即是否有永久性的渠首工程、水渠是否畅通、系统是否在泰拉地区、系统是否是农民管理的;此外还有一个常量。
表1 治理结构与季节水资源的充足程度
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
政府机构管理的灌溉系统
季节
中上游有充足的水源的百分比
中下游有充足水资源的百分比
中上游有充足水资源的百分比
中下游有充足水资源的百分比
季风雨季
97
88
92
46
冬季
48
38
42
13
春季
35
24
25
8
注:根据实地观察和案例研究的结构化编码,水资源的充足程度从“适当”到“不存在”分为四类。
76个灌溉系统都有关于所有这些变量的数据。水渠长度和劳动投入变量接近于0。但是,渠首工程的系数(0.34)和系统是否是农民管理的系数(-0.32)都在95%的显著水平上,而水渠是否疏通的系数(-0.14)都在95%的显著水平上,而水渠是否疏通的系数(-0.14)和系统是否在泰拉的系数(-0.10)都在90%的显著水平上。回归方程还有一个0.64的常数项,处在95%的显著水平上。但是回归的R2只有0.28。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认为这些结论只是初始的和暂时的。1993年夏天,实地研究小组从更多的系统收集了数据,所以将来可就更大的数据系列进行补充分析。
初步分析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灌溉系统物理特征如何影响相互合作公平分配所得到的能力。在这些尼泊尔灌溉系统中,上游和下游所获得的水量差异显著地与泰拉地区呈负相关,可能是因为上游农民的优势在平原地区没有山区显著。永久性的渠首工程的存在,这常被认为是现代化的、运作良好的灌溉系统的标志之一,但这与上游和下游所得水资源不公平呈正相关。其原因之一可能是永久性的渠首工程增加了上游农民相对于下游农民的谈判地位。另一方面,疏通水渠给下游农民提供了更多的水,而减少了水资源获取的差异。最后,农民管理灌溉系统中上游与下游所获水资源的差异相对于机构管理的灌溉系统,显著缩小了。这大概是因为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较可能就自己的运行规则谈判的结果,而这些规则比较有效地考虑到了下游农民的利益。
永久性渠首工程的建造常常得到资源的资助,这样农民就不需要偿付这项投资的成本。这种形式的外部援助大大减少了每年动员劳动力或其他资源去维护灌溉系统的需要,这种减少在项目计划中常被完全解释为收益。但是,这种纯粹收益的结论下得过早。广泛的基础设施的建造不要求受益人迅速偿付资本投资存在两个相反的结果。首先,没有明确要求偿付资本投资,农民和地方政府官员有积极性进行寻租活动,并会过高估计先前年度的花费以获取外部援助(Repetto, 1986)。其次,这种形式的援助会改变系统内部农民之间的关系模式,从而减少了上游农民和下游农民之间相互依靠和互惠模式的认同感,而正是这些长期维持着系统的运行。外部援助因为否决了下游农民参与投资以改善基础设施的机会,可能使得那些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不能维护利益分享的权利(Ambler, 1990)。让我们提供一个发生于机构管理的灌溉系统中的这些不良后果的例子。
卡马拉(Kamala)灌溉工程位于泰拉地区,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建造复杂而昂贵的资本结构而不注意会带来占用和供应决策紧密结合的制度设计,卡马拉工程是70年代由灌溉局(后来称作灌溉、水利和气象局)建造的。它最初设计服务于泰拉地区一个25 000公顷的区域。那里的农民从事于依靠降雨的农业,而先前并未组织他们提供自己的灌溉系统。在亚洲开发银行的资助下,建造了一个永久性的坚固的渠首工程和一条笔直的水渠。系统在1983_1984农业年完成。此后,从来没有强制征收过水费。系统从来没有向正式服务区域的所有土地提供灌溉水。卡马拉工程的职员是靠中央政府的税收来资助的。极少收集资金用于系统的持续运行和维护。工程全体职员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操作和维护巨大而坚固的渠首工程,用它把卡马拉河(Kamala River)河水分流到主渠和支渠中,极少有时间能维护系统的其他部分。由于极少建造田间水渠,农民就把支渠打开取水。
对于渠首工程以下的系统的运行和维护,政府和农民都不负任何责任。对水资源的使用标准缺乏组织导致了严重冲突,并形成了水资源不公平分配的模式。这些如以下的一个实地考察队所描绘的那样(Laitos et al., 1986: 147):“水资源的分配是来之即用。这样,上游农民倾向于获取所需的所有水资源,结果是下游农民常得不到足量的和可靠的水资源供给。这种情况常导致上游农民和下游农民之间的冲突。有时,来自中部村庄帕塞(Parshai)附近的成百农民拿着标枪和大棒一起到渠道上游的村庄巴拉马吉亚要求放水。而巴拉马吉亚的农民也使用武器来保卫他们的水资源。即使放水以后,帕塞的农民还不得不继续使用武力来保卫,以确保水渠的畅通。”
甚至在所有投资都用于物质工程的情况下,相对于建立规则分配水资源或供应义务来说,这一灌溉系统是在“自然状态”下运行的。系统中农业产出受所获水量的影响,变动非常巨大,但是种植密度通常低于平均水平:上游为180%,下游是150%。
与卡马拉灌溉工程呈鲜明对照的是另一个机构管理的灌溉系统,即匹苏瓦(Pithuwa)灌溉工程,也位于泰拉地区。当灌溉局投资于建造和修直16个支渠的时候,并未试图建造一个永久性的进水设施。系统设计规模是灌溉600公顷土地,但是农民通过每隔一年在季风雨季把田地用于水稻生产从而把系统服务面积扩大到1300公顷。很多大的土地所有者位于系统的下游(在此,靠近东西公路从而降低了售往市场的运输成本)。这是一个偶然的情况,弥补了政府对制定互补分配和资源流动的规则注意的不足。尽管存在很多不种地的地主和租佃安排,这一系统仍达到了相当程度的自主组织。
匹苏瓦系统灌溉的区域尽管有很多有效的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但该区域仍然依赖于依靠降雨的农业,而且在水渠建造之前并未组织起来。在工程起用之初,水资源的分配是基于“强权即权利”的原则,并且像卡马拉工程至今仍然存在的那样充满着冲突和不和。匹苏瓦目前农民参与的程度较高,其起源是很有趣的。它从系统下游的一个支流的组织演变为整个系统的组织(Latitos et al. 1986: 126-127)。“……一位杰出的农民发起组织第14支渠的其他农民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第14支渠沿线的水资源分配制定规则。随着农民参与委员会的活动,支渠沿线水资源分配而引发的冲突迅速减少。其他支渠开始效仿第14支渠的做法。最终,所有支渠的农民都为水资源的分配设立了支渠委员会。……一旦支渠委员会能够有效地工作,把支渠委员会联合起来就创建了一个农民大会和一个主渠委员会。”从最初的组织发展到现在的两级体制,该体制覆盖了整个系统并管理整个系统运作的各个方面,以及对16个支渠中的每一个分别制定规则以进行管理。主渠委员会负责在16个支渠中间分配水资源。当季风雨季水资源充足时,所有支渠都有水。在作物轮作的情况下,一半的农民种水稻,而另一半种蔬菜、种子和纺织原料。这种作物的轮作与水资源的轮换相一致,使得灌溉面积成倍增加。然而,当水资源稀缺的时候,“委员会安排一个轮换制度。他们首先把水资源分配几天给下游河渠,接着再分配几天给上游河渠”(Laitos et al., 1986: 130)。每隔支渠委员会决定他们自己的分配规则,这些规则各支渠各不一样。“在支渠1和支渠2,每比格(bigha,相当于0.66公顷)分配4小时水,而在支渠3和支渠16,每比格分配2小时水。分配的时间是按照土壤的性质、田地的大小、所能得到的水量以及作物所需的灌溉次数来分配的。在一些支渠,白天的水是用于输送的,而晚上的水是把这些输送的水分配到田间。每个委员会在他们的支渠都制定适合他们的土壤、作物和可获得水量的规则。”此外,为确保每个支渠的上游和下游有充分的代表性,确定一个规则就是如果支渠委员会的主席是来自某个支渠的上游区域,那么秘书就必须来自下游区域,反之亦然(Giri and Aryal, 1989: 15)。
考虑到支渠委员会和系统委员会的能力,灌溉局逐渐把系统的维护和运作转交给农民。每年春季季风雨季来临之前对进水设施的修理是一项繁重的任务,是由政府出动推土机帮助实施,并且政府为这些推土机的用油制定预算。清理支渠的任务被分配给每个支渠委员会,由它们使用几种办法去清理。一些支渠按照竞价规则把清理河渠的工作用契约包出去。那些最低报价的人赢得为期一年的合同。支付这一维护的资金是由农民委员会按照估价,根据每个农民财产的规模而从农民中收取的。在另一些支渠,农民自己清理水渠,动用劳动的规则也是由支渠决定。
该系统的农业实践是机构管理的灌溉系统中最好的。系统下游的平均种植密度(228%)略高于上游(221%),其原因是大农庄位于系统的下游,而且下游靠近全天候的公路,这也提供了极大的动力。土壤和其他因素在整个系统中是近似的。尽管这个系统开始是一个机构管理的系统,但该系统的农民享有与农民管理灌溉系统相似的权力。
在农民管理灌溉系统中,所采用的占用和供应规则多种多样,这与所需维护系统运行的劳动类型紧密相关。例如,杨帕芬特灌溉系统这样一个非常古老的灌溉40公顷土地的山区灌溉系统,其经营者在春季不需要动员大规模的资源就可以建造和修理渠首工程,因为它们和邻近的一个系统已经建造了一个永久性的储藏设施储藏永不停止的泉水。但是在季风雨季节,他们的12个泄水工程每日都需要维修,所以他们为劳动力需求的高峰期制定了一个轮流劳动的制度(Laitos et al., 1986: 97)。“在夏季稻谷生产季节,维修系统的义务每天在12个泄水工程轮换。每个泄水口每天需要1个劳动力。12天以后,维护义务又轮回到服务第1个泄水口的农民头上。每条田间水渠有一个泄水口。此外,农民还要为主系统的维修轮流值班。每个农民都要当班检查主渠并做一些必需的修补。在紧急时刻,则每个人都要参加。”在水量充足期间,水资源是能满足需要的。在缺水的冬季,上游的6个泄水口一次接水24个小时,接着换为下游的6个泄水工程接水24小时。杨帕芬特的农民因此设计出很像前面所提出的规则B的一套规则。这些农民每年每公顷平均产出7.75吨。系统上下游大部分农民每年都种三季,所以上游和下游产出的差异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泰拉地区克拉巴里(Kerabari)灌溉系统的农民面临不同的资源动员问题,从而采用了一套不同的规则。这个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由农民修建于70年代,它从一条河(Khadam Khola)里取水,而这条河在季风雨季从山脚下带来了大量的沉积物。尽管由农民建造的主渠被外人认为“是一个工程上的伟绩”,但农民和政府建造的一些永久性进水设施的都被冲垮了(Laitos et al., 1986: 217)。这样,尽管过去政府努力帮助克拉巴里农民建设,以节省农民每年建造暂时渠首工程所需付出的劳动,农民还必须长期对付洪水和决口。如1985年春天,150个农民工作了15天来修复主渠(Laitos et al., 1986: 219)。两个支渠服务于卡达姆上游和卡达姆下游的农民。这个系统中的所有农民都拥有自己的土地,而且这些土地的分配是相对公平的。
当该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最初组建的时候,在两个支系统上有一个委员会,但是“卡达姆下游农民认为卡达姆上游农民对系统的维护和运作不积极和不热情。他们把委员会分为上游和下游两个,但是同意两个委员会只设一个公认的主席(该主席在两个系统中都拥有土地)”(Laitos et al., 1986: 22)。当水量丰富的时候,每个农民都可随意取水。在春季水资源短缺的时候,就在两个支委会内部决定种植方式并设计轮作制度,以确保这种联合建立的种植方式有足够的水资源保证。
所有拥有少于2比格(1.32公顷)土地的家庭,大约是自由自营农民的三分之二,他们要根据联合委员会的决定安排一个劳力用于每天的维护。那些拥有多于2比格土地的家庭要按每2个比格提供一个劳动力的比例来提供。假使很多农民拥有少于1比格的土地,那么这项规则设定的负担就是小土地所有者重于大土地所有者。联合委员会从农民中征集资金修直河渠,寻求外部帮助处理渠首工程问题。在三个生产季节的每一季,位于上游和下游至少90%的田地进行了种植。农民采用高产品种和良好的农业耕作方式,从而达到了约每年每公顷9.1公顷的产出,大大高于平均水平。
政策意义
面临公共池塘资源供应和占用问题的参与者之间存在的非对称性,使得克服上游农民和下游农民之间“自然状态”博弈缺乏动力的问题很难解决。但是,在农民意识到他们相互依赖情况下,这些非对称性常常可以克服。毕竟,上游农民在需要长期维护系统的时候,他们就会需要下游农民提供资源。此外,如果局中人得到一些保证,他们为设计和实施新的占用和供应规则所作出的努力将不被外部权威所削弱,这时,有关新规则的讨价还价就能起作用。如在一个货币化的靠自由资金运行的系统,除非他们获得充足可靠的水资源以致于增加产出,而这又大于对他们所征收的费用,否则,下游农民不愿为水付费。
在尼泊尔、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允许自主管理的发展中国家,有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规则的多样性,并且这些规则是农民在其年度会议上艰苦地谈判制定的(Coward, 1980; Geertz, 1980; Hunt, 1989; Korten and Siy, 1988; E. Ostrom, 1992; Siy, 1982; Tang, 1992)。正如我们的理论分析所预期的,并不是所有这些谈判努力都能获得提高效率和公平的规则。但是,只要所有参与者相互依赖的关系是明确的,并且他们希望长期乃至未来都相互保持这种关系,那么从发展中国家的农民那里就可以看到他们所展示的创制规则和实施规则的强大能力,这些规则能够提高产出和降低结果的非对称性。很多政府机构设想强制实施匹苏瓦和克拉巴里系统中的种植模式,或征收类似于匹苏瓦农民收集的货币资金,但是并不能得到农民的充分合作从而实现这些政策目标。
发展文献的大部分都强调提高灌溉和农业业绩的有形技术,而不是制度的重要性。毫无疑问,恰当地设计现代化的灌溉工程能够提高农业产出和很多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的效率。但是,局外人的干预可能导致农民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瓦解,这将产生较坏的而不是较好的结果。比如,用于投资于灌溉系统的有形资本的赠款或贷款,这些贷款从来没有被那些直接受益的人所偿还,将使上游农民不需要考虑下游农民对水资源的需要。在维持对水资源自然状态博弈方面,如果没有人为维护系统付费和提供劳动力,即使在外部援助的情况下,灌溉系统的供给水平也将下降。
相信外部机构有能力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人应该同时认识到外部机构有时能起到削弱的作用。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各种制度安排处理形形色色问题的能力和局限性,但是自主管理的公共池塘资源组织已经表明了他们有能力实现高水平的效率和公平。
| 课件名称: | 水利政策 |
| 课件分类: | 水质水利 |
| 课件类型: | 参考资料 |
| 文件大小: | 769.11KB |
| 下载次数: | 0 |
| 评论次数: | 0 |
| 用户评分: | 0 |
- 8. 水利政策:我国水资源的严重性与危险性
- 9. 水利政策:我国现行水管理体制亟待改革
- 10. 水利政策:水权转让
- 11. 水利政策:水环境保护和水污染控制方面的政策分析
- 12. 水利政策:水资源开发利用要综合考虑社会和环境效益
- 13. 水利政策:水资源的制度分析制度 评论之五十四
- 14. 水利政策:水资源的管理与补偿机制
- 15. 水利政策:水资源问题及其对策
- 16. 水利政策:清华案例:黄河断流,到底该怎么办?
- 17. 水利政策:灌溉系统自主治理与不对称问题的解决
- 18. 水利政策:西北水资源 开发需创新
- 19. 水利政策:解决海河流域缺水问题的思考
- 20. 水利政策:转型期水资源配置的公共政策:准市场和政治民主协商
- 21. 水利政策:黄河水资源情势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