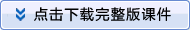【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4
【原刊页号】117~143
【分 类 号】D410
【分 类 名】法理学、法史学
【复印期号】199909
【 标 题】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
【 作 者】夏恿
【作者简介】作者夏恿,1961年生,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摘 要 题】本文通过梳理法治的渊源、规诫和价值,把法治依次解释为一项历史成就、一种法制品德、一种道德价值和一种社会实践。作者首先分析了经典法治概念的形成过程和构成要素,认为既不宜把法治理解为世俗化运动的结果,也不能简单地看做近代革命的产物。接着,作者展示了富勒、莱兹和菲尼斯把法治作为制度品德的逻辑理由和论证过程,并论述了作为法治的普在要素的十大规诫。进而,作者对法治的工具价值和道德价值做了谨慎的区分,在揭露工具主义谬误的同时又肯定了法治的工具品性,并通过评述哈耶克、德沃金和罗尔斯等人的学说,揭示出法治对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意义。最后,作者指出法治的内在矛盾,强调把法治理解为社会实践概念的重要性,并勾勒出中国法治语境的特殊性和法治思考的进程。
【 正 文】
法治是法律史上的一个经典概念,也是当代中国重新焕发的一个法律理想。作为经典概念,法治蕴涵隽永,然幽昧经年,即便在标榜法治传统的西方亦不曾有过一个公认的定义。作为法律理想,法治为制度注入锻骨强魄的理性,为学术提供激浊扬清的活力,然又因承载过多的政治意愿和社会情感而臃杂不纯,以致时常被曲解。因此,当我们高扬法治旗帜的时候,不妨平心静气地问一问:法治究竟是什么?这样,或许有助于准确把握当前我国朝向法治的各种努力的历史与逻辑定位以及所处语境的特殊性,从而使我们的法治理论和实践皆有一个良好的起步。
一、法治的历史渊源
法治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或者说,法治应该首先被看做人类的一项历史成就。这种黑格尔式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法治概念的背景和基础(注:伯尔曼(Harold Berman)也认为,法治的含义应该通过对政治、社会和法律制度的历史研究来理解。参见Harold J.Berman,Toward an Integrative Jurisprudence:Politics,Morality,History,76,Calif-ornia Law Review,1989,pp.779,787。)。追寻法治的源头,应该从亚里士多德说起。在《政治学》里,亚里士多德说:“若要求由法律来统治,即是说要求由神qí@①和理智来统治;若要求由一个个人来统治,便无异于引狼入室。因为人类的情欲如同野兽,虽至圣大贤也会让强烈的情感引入歧途。惟法律拥有理智而免除情欲”(注:The Politics,Book III,Ch,16.本文里的若干译文可能与已有的中译文有较大出入,例如,该段译文参照了商务印书馆译本《政治学》,但有较大不同。)。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话包含三个推论:第一,良好的统治当免除情欲,即免除任意和不确定;第二,人的本性使任何人皆不能免除任意和不确定;第三,惟法律的统治即法治可免除任意和不确定。显然,此言既表述了诉诸法治的逻辑理由,亦透现出法治在宇宙秩序论、人性论等方面的哲学基础。不过,它并没有说明究竟什么是法治,换言之,它没有说明法治究竟何以能够免除任意和不确定。亚里士多德又说:“法治应包含两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可以说,这段话已然从逻辑上粗略地勾画出法治的形式要件,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说明究竟何谓“普遍的服从”、何谓“制定得良好”。这要由生活于具体的社会场合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通过他们的信念、制度和活动来赋予涵义。法治内涵的形成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罗马人和诺曼人的法律传统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一项历史成就,西方的法治概念是以罗马法和诺曼法的历史文本为基础的。这些文本迄今仍然为许多关于法治含义和功能的讨论所倚重。与其他的法律传统形成鲜明对照并饶有趣味的是,罗马人和诺曼人乃是从那些重视操作而非耽于理想的法律实践者的视角和需要出发而走近法治的(注:“法律实践者”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它甚至不能根据职业来界定。在这里,我把它界定为一群关注如何治理现存的社会甚于关注如何创造和运用纯理论的理想目标的人。)。正如查士丁尼《国法大全》所展示的那样,罗马法律制度历经五个世纪而发展成为程序和实体规则的一种混合表述,它体现了对这样一种信念的强烈承诺:由法律而不是由专横的权力来提供私人纠纷解决方案的语境(注:尽管在公法方面仍然流行“国王居于法律之上”的观念。参见Friedrich A 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p.167。)。《国法大全》最重要的部分《学说汇纂》的第一部开篇说:“万民……皆受法律和习惯的统治。”(注:I The Digest of Justinian 9,Theodor Mommsen & Paul Krueger eds.,Alan Watson trans.,1985.)这确认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政治社会应该是一个法律社会。更重要的是,这些文本显示出罗马的实践家和法学家创造了一种详细而复杂的关于合法性的语言,这种语言和那些从特定的案件里衍生出来的规则一起贯穿于范围广泛的法律原理和法律概念(注:关于罗马法律实践及其对于法治的意义的一种较好的评注式讨论,见Bruce W.Frier,Autonomy of Law and the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11 Cardozo Law Review,1990,p.259。)。同样,诺曼人的法律制度也表现出对法治原则的喜好。例如,作为英格兰普通法的第一部系统著作,1187年格兰维尔(Glanvill)的《论英格兰王国的法律与习惯》总结了亨利二世在法律技术和法律规则方面的变革,增强了王室法律的确定性和权威性,被认为是法律科学的一次革命。尤其是他在以令状形式界定王室的司法管辖权的同时限制了这种管辖权,使“令状统治”富有法治的意味(注:“用梅特兰的话讲,令状的统治即法律的统治。”参见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54页。)。70年后布莱克顿(Henry de Bracton)的《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则是为了确保普通法为13世纪的英国法官统一适用而写作的。在这本书里,布莱克顿把他自己的使命解释为通过评论和编纂“英格兰王国每天发生且匆匆而过的案件”,为当时的执业法官提供一本权威的教本(注:参见Henry De Bracton,On the Law and Customs of England,George E.Woodbine ed.,Samuel E.Thome Trans.,1968,p.20。)。他在书中提出,国王有义务服从法律,因为国王处在上帝和法律之下。不是国王创制法律而是法律造就国王。格兰维尔和布莱克顿的文本虽然不像罗马人的著述那样广博,但它们同样显示出,英国的实践者和法官也创造了一种丰富的、贯穿于法律原理和出自讼争的特定规则的关于合法性的语言。
罗马人和诺曼人丰富的法律语言和辉煌的司法成就不仅铸入中世纪欧洲教会法和世俗法的恢宏体系,而且被用来继续锻造关于法治的理想、原则和规则。这一过程在当时既得到复合多元的政治经济结构、法律渊源和司法管辖权的支持,也得到盛行的宗教意识形态的支持。因为根据神学信条,世界本身是由规则支配的,仁慈的上帝掌管着一个依照法律来统治的世界,赏罚分明。所以,人们之间的关系,包括宗教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关系,都要由基于法律的正义和基于正义的法律来界定。
首先,教会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司法管辖权关系的构造和维系必须而且只能诉诸法律的权威。按照当时的政治法律实践,倘若教会应该享有一些不可侵犯的权利,那么世俗的国家就必须把这些权利作为对自己的最高权力的一种合法的限制来接受。同样,国家的一些权利也构成对教会最高权力的一种合法限制。因此,教俗两种权力只有通过法治的共同承认,即承认法律高于它们,两者才能够和平共处。
其次,在教会体系内部,12、13世纪的教会法学家曾描述了对教皇权力的所谓“宪法性限制”,例如,教皇不得从事与整个教会的“地位”相悖的行为,不得颁布旨在损害教会的特性、一般利益或公共秩序的法律。即便是崇尚权力主义的教皇之一英诺森四世(1243-1254)也承认,如果教皇的命令包含着有损教会的不公正的内容,便可以不服从教皇。尽管对教皇权力的宪法性限制由于缺乏一种可以向教皇挑战的有效的法庭而被削弱,但是,即便在教皇权力登峰造极之时,这种限制权力的理论仍然拥有坚实的基础和广泛的支持,并因此推动地方自治的发展。史家写道:“教会是一个Rechtsstaat[法治国],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度。与此同时,对教会权威的限制,尤其来自世俗政治体的限制和教会内部特别是教会政府的特定机构对教皇权威的限制,培育出了某种超出法治国意义的依法治理(rule by law)的东西,这些东西更接近于后来英国人所说的‘法律的统治’”(注: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259页。)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世俗的世界里不仅同样流行着统治者必须在法律之下统治的信念,而且创造了许多关于法治的原则和规则(注:有不少学者仅仅把法治观念理解为某种世俗化运动的产物。例如,勒内·达维在一本对中国法学研究和教育颇有影响的书里以这样的方式描述12、13世纪法规观念的复兴:“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复兴,社会上终于认为只有法才能保证秩序与安全,以取得进步。以仁慈为基础的基督教社会的理想被抛弃了;……人们不再把宗教与道德同世俗秩序与法混淆在一起,承认法有其固有的作用与独立性,这种作用和独立性将是此后西方文明与观点的特征。”(《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这种观点反映了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又一种不同的解释。)。例如,13世纪早期的《萨克森明镜》明示:“上帝自身即是法律,故法律为上帝所钟爱”(注:转引自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628页。)。据此,人人有权利抵制国王和法官的违法判决。随着世俗法律体系里封建法、庄园法、商事法、自治城市法和形形色色的王室法的发展,权利义务关系变得更客观、更明确、更少专断性,也变得更普遍、更一般、更统一。法治不仅仅是与正义、公平、良心和理性相联系的抽象理念,而且具体体现在像1215年英格兰《自由大宪章》、1222年匈牙利《金玺诏书》和市镇特许状那样的法律文件里。如《大宪章》规定:“不得凭借某种没有确凿可信证据的指控使任何人受审。”“任何自由民都不受逮捕、监禁、没收财产、褫夺公权、放逐或任何方式的伤害,……除非那么做是按照与他地位相等的人的合法判决或按照国家法律”。“只有通晓法律的人才能任命为法官、治安长官、郡长或执行吏。”《金玺诏书》除了相似的规定外,最后还宣布,若国王及其继承者违反本法,人人皆享有通过言语和行动反抗的权利,而且此一权利具有永恒性,不应招致叛国的指控。还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司法客观性、确定性的信念和制度。13世纪的法兰西和英格兰的法官们通常都认为忠于法律和上帝要甚于忠于他们的国王和领主。也是在这个时候,“同类案件同样判决”成为流行的法律格言。
在以上意义上,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法治观念当做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和近代政治革命的产物(注:当然,如何解释法治的渊源,涉及不同的历史观和法治观,涉及对西方法律传统演化的不同解释,如对教皇革命的估价、对资本主义兴起的评析。例如,在这一点上,前引伯尔曼一书与泰格和利维所著《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便是道分二途(参见陈方正《法律的革命与革命的法律:论西方法制史的两个对立观点》,载该书中译本序第1-8页)。又如,昂格尔把法治理解为一种与“习惯法”和“官僚政治法”相对照的“合法秩序”,因而认为法治是“伴随着现代欧洲自由主义社会而出现的”,也就是说,法治直到17世纪才出现(参见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另见伯尔曼对昂格尔的评论,伯尔曼前引书第八章注51,第740页。)。概而言之,滥觞于近代革命以前的法治观念至少有三:其一,法律至上。尽管从大多数统治者的主观意愿来讲,尊重法律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依法而治”的权宜之计(注:“在官僚法里,普遍性不过是权宜之计”。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第46页。),但与此同时,关于私人权利平等、权力分立、自治、公正审判的法律原则和相关的程序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普通人提供超出统治者工具性动机的正义,从而培育法律的权威。可以说,统治者们寻求通过法律制度系统地实施其政策,而其自身亦不得不受用以为治的法律制度的约束,乃是走近法治的一个政治过程。其二,权力分立与制衡。虽然这个时候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主要是就同一地域内不同的政治实体而非同一政治实体内各部分的关系而言的,但权力由此而分立,并发展出一套分权制衡的法律规则。更为重要的是,分权制衡及其规则有效地将权力的存在和运作置于法律之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世把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立制衡当做法治的基本要求,甚至等同于法治本身(注:“为了确保普遍性,行政必须与立法分立;为了确保一致性,审判必须与行政分立。实际上,这两种分立恰恰是法治理想的核心。”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第53-54页。)。其三,法律来源于某种超越于现实政治权力结构的实在,因而,法律被视为普遍、客观而公正的。这种超验的实在在当时被理解为神意和自然正义,在后世的法治理论里则通过自由、人权、民主等价值来解说。
与法治传统生成与演化的丰富多彩的历史相比,理论家们的解说未免显得苍白和含混。一位西方学者曾说,造成法治概念时常模糊不清的原因是,“法治的分析语境出自西言的思想和实践这两个不同的来源。法律实践家和法官总是站在法治对话的前沿,他们的实践则为理论家所解释。尽管法治有着丰富的、难以割断的实践的历史,但理论家所做的将它理论化的尝试却常常是杂乱无章的”(注:Guri Ademi,Legal In-timations:Michael Oakeshott and the Rule of Law,Winscosin Law Review,1993,p.845.)。不过,同样应该注意的事实是,理论家们关于法治的解说连同关于自然法、自然权利和民主的思想为锻造近代法治概念和法治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理论资源(注:关于自然权利理论的生成、意义及其与法治的关系,参见夏恿《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修订)版,第86-116、159-168页。),而且,在通过接引西方学说而启蒙变法的非西方国家里,这些解说似乎成了关于法治概念的最具权威性的文本来源,并因此比作为其原初解说对象的西方制度传统似乎更具影响力。例如,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的统治乃是上帝的道德秩序和为确保这种秩序能够通过理性而为人类所理解的神灵启示的一个自然映现;霍布斯提供了第一个关于法治的现代表述公式,依此,法治被看做建立和维持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减缓人类对因暴力和非自然死亡而丧失尊严的恐惧的一种方法;洛克主张政府必须遵循确定的、有效的法律,而不应享有绝对的专断的权力;孟德斯鸠把三权分立作为遏制政府权力专横、维持法律权威与公民自由的一种关键性的制度安排;黑格尔把法治从超验的自然、理性或神圣秩序里剥离出来,作为人类的一种建设,特别是作为欧洲的一项历史成就,他那关于法治国的复杂而又模糊的理式为后来许多对法治进行批判性分析的理论家们提供了语境。
我们还要特别关注近代以来那些善于把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理论家对法治的贡献。例如,英国18世纪法学家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所著《英国法释义》一书系统阐述了英国的法律制度,并将17、18世纪盛行的古典自然法学说与英国的普通法结合起来。邓·肯尼迪(Duncan Kennedy)评论说,布莱克斯通并没有发明使权利作为基本矛盾调和者的观念,这种观念是约翰·洛克、17世纪的激进主义者、《权利宣言》和光荣革命的成就。但是,布氏把作为自由主义政治口号的“权利”转化为几千个普通法规则。如果没有像他这样的人把权利观念引入技术性的、几乎被人遗忘的、显然又极其重要的普通法领域,自由主义学说就不可能完备,权利观念也不可能自圆其说。(注:邓·肯尼迪:《布莱克斯通〈释义〉一书的结构》,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2-423页。)就法治理论而言,19世纪的英国法学家戴雪(A.V.Dicey)通常被视为近代西方法治理论的奠基人。戴雪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法治概念,这一阐述乃是以已有的法治体制及其经验为根据的。在《宪法性法律研究导言》里,他写道:
构成宪法基本原则的所谓“法治”有三层含义,或者说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
首先,法治意味着,与专横权力的影响相对,正规的法律至高无上或居于主导,并且排除政府方面的专擅、特权乃至宽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
其次,法治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或者,意味着所有的阶层平等地服从由普通的法院执掌的国土上的普通的法律;此一意义上的“法治”排除这样的观念,即官员或另类人可以不承担服从管治着其他公民的法律的义务,或者说可以不受普通审判机构的管辖。……作为其他一些国家所谓的“行政法”之底蕴的观念是,涉及政府或其雇员的事务或讼争是超越民事法院管辖范围的,并且必须由特殊的和或多或少官方的机构来处理。这样的观念确实与我们的传统和习惯根本相忤。
最后,法治可以用作一种表述事实的语式,这种事实是,作为在外国自然地构成一部宪法典的规则,我们已有的宪法性法律不是个人权利的来源,而是其结果,并且由法院来界定和实施;要言之,通过法院和议会的行动,我们已有的私法原则得以延伸至决定王室及其官吏的地位;因此,宪法乃国内普通法律之结果。(注:Albert.V.Decey,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1885),1960,pp.202-203.)
概括地讲,这段被奉为经典的话大致有三层意思:第一,人人皆受法律统治而不受任性统治;第二,人人皆须平等地服从普通法律和法院的管辖,无人可凌驾于法律之上;第三,宪法源于裁定特定案件里的私人权利的司法判决,故宪法为法治之体现或反映,亦因此,个人权利乃是法律之来源而非法律之结果。当然,对戴雪的经典定义也有不少不同的理解和评论。例如,昂格尔只同意戴雪的前两层意思,认为第三层意思只是英国政治史和近代自然权利理论的产物,不宜作为法治定义(注: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第二章注释11。)。还有学者认为,戴雪的概念包含两个作为法治基本要素的信念:一是个人应该由法律而不能由其他人的专横意志来统治,二是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功能必须保持分立(注:Guri Ademi,Legal Intimations:Michael Oakeshott and the Rule of Law,Winscosin Law Review,1993,pp.844-845.)。莱兹(Joseph Raz)则揶揄地说,英语世界的作者们被戴雪的不恰当的法治定理催眠得太久了(注:Joseph Raz,The Authority of Law: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Clarendon Press,1979,p.218,footnote 7.)。的确,尽管戴雪对法治的解释为近代法治概念奠定了基础,但这段话无疑是在特写的语境里讲的,他所主要关注的只是探讨英国议会制度与宪法传统之间的关系(注:例如,戴雪把法治看做“英国宪法的一个特色”(Albert.V.Decey,187)。)。
戴雪的经典概念及其相关的不同意见激励我们探寻较为确定、较为普适的法治含义。俾于20世纪末端回眸作为人类历史成就的法治,我想是可以得到比布莱克顿时代和戴雪时代明晰而深刻一些的认识的,尽管我们会遇到或许更多、更严重的新的困惑与不确定。在这里,让我们先从几位有代表性的当代著名学者的论述入手,梳理一下至少是以语言的相对确定性为基础的法治概念里所包含的基本规诫。
二、法治的主要规诫
(一)富勒、莱兹和菲尼斯的界说
富勒在《法律之德》一书里把法律之德区分为内在之德和外在之德,认为法治是法律内在之德的一部分(注:富勒所说的"morality"虽然在许多场合包含汉语通用的“道德”一词的含义,但与后者还是有些不同。故译为“德”。富勒给他关于法治的一章取名为“使法律成为可能的德”。这种成法之德或使法律之为法律的品德是内在于法律之中,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不甚相同。富勒又把这种内在之德称作“程序自然法”。见Lon L.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Revised Ed-i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在他看来,具备法治品德的法律制度由八个要素构成:一般性、公布或公开、可预期、明确、无内在矛盾、可遵循性、稳定性、同一性(注:见Lon L.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pp.46-94。)。富勒的八项要求中的第一项“一般性”其实指的不过是应该有法律规则,其他七项都是关于法律规则怎样才能够被遵循。可以说,这八项要求表述了法治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必须有规则,二是规则必须能够被遵循。这两个原则在逻辑上并没有超出我们在前文提及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形式要件的两个方面,但在实体上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内涵。应该注意的是,这两个原则表面看起来我们经常说的“有法可依”、“依法办事”颇为相似,但细细推究起来,却是很不相同的(注: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法律必须能够被遵循”与“依法办事”不尽相同。前者的重点放在对法律本身的质量合格性的要求,即“法律可依”,而不是一味地对遵守和执行法律的要求(富勒的第八项实际上也是对规则本身的要求:旨在实施规则的执行或行政规则要与被实施的规则相适应)。第二,在富勒的两类原则里,法治的主体问题是不彰显的。准确地讲,这两类原则一是有法律可遵循,或有法可循,二是法律可以被遵循,或法律可循,而不是“有法可依”和“依法办事”。按汉语习惯,“依法”与“循法”似乎有微妙的不同。“循法”的主体是一切人,而且一切人都在法律之下,平等地作为法律规则的对象。“依法”的主体却似乎容易被误解为与法律平列地站着,相依相靠,法律只是其办事的器用。)。富勒的重心放在“法律可依”。也就是说,为了能够被遵循,法律必须具有某些品德。有的学者认为,富勒的后七项要求表述了合格的法律应当具备的两个特征:“可知性”和“可用性”。也就是说,为了让规则的接收者知道他们被命令去做什么,命令必须是公开的、协调的、不矛盾的、清楚得足以明白的,而且不能改变过快;为了规则的接收者去做他们被命令去做的事情,命令必须是可预期的(不溯及既往)、不相矛盾或抵触的,并且在物理上、精神上或环境上不是对被命令的人来讲不可能遵循(注:Margaret Jane Radin,Reconsidering The Rule of Law,69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1989,p.786.)。还要注意的是,富勒认为,他所归纳的法治原则是法律存在的必备要素,一种法律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必定与法治相符合,因为在法律和道德之间存在一种本质的联系。
莱兹也把法治看做法律制度的一种重要品德。他指出,广义的法治指一切人都服从法律并受法律的统治。但是,按照政治法律理论,法治又作狭义解,表示政府应由法律来统治并服从法律。这种意义上的法治理想通常用一个习语来表达:“法治而非人治”,但这句话的意思又是模糊的,因为政府的治理必须既通过法律也通过人。有这样一种说法:法治意味着一切政府行为必须基于法律并由法律赋予权威。莱兹问道,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同义反复呢?因为不由法律赋予权威的行为不可能是作为一个政府的治理行为,它们不具备法律效果并通常是非法的。莱兹认为,如果区分作为政治概念的“治理”和作为法律概念的“治理”,同时区分专业意义上的“法律”和非专业意义上的“法律”,那么就可以避免同义反复。因为,法治所诉求的是作为政治概念的治理。即有权势的人和官府里的人像其他人那样服从法律;法治意义上的法律不是律师眼里的法律,而是非法律专业的普通人眼里的法律,即一套公开、普遍并且相对稳定的规则。不过,莱兹马上补充说,法治原理并不否认法律制度既由公开、普遍和相对稳定的规则,也由特定的、细节性的规则构成,后一种规则是行政官、法官和律师一类人手里的十分重要的工具。法治原理所要求的只是特定规则的制作必须受公开的相对稳定的一般规则的指导(注:Joseph Raz,The Authority of Law,pp.211-213.)。
莱兹接着指出,法治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们应该受法律的统治并服从法律;二是法律应该让人们能够受其引导。他认为,应该关注的是后一种含义。因为一个人只是在不破坏法律的意义上遵守法律,只有当他的法律知识构成了他守法理由的一部分时,他才服从法律。所以,法律要被人们服从,就必须能够引导人们的行为。为此,他提出了法治的八条原则:第一,法律必须是可预期的、公开的和明确的。这是一条最根本的原则。第二,法律必须是相对稳定的。第三,必须在公开、稳定、明确而又一般的规则的指导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第四,必须保障司法独立。第五,必须遵守像公平审判、不偏不倚那样的自然正义原则。第六,法庭应该有权审查政府其他部门的行为以判定其是否合乎法律。第七,到法院打官司应该是容易的。第八,不容许执法机构的自由裁量权歪曲法律。(注:Joseph Raz:The Authority of Law,pp.214-218.)莱兹解释说,以上八条原则可以分为两组。第一至第三条原则要求法律应该符合某些能够使它有效地引导行为的标准。第四至第八条原则是用来确保法定的执法机关不得通过歪曲执法来消解法律的行为指引能力,并确保能够监督遵循法治和提供有效的救济。至于为什么确定这些原则而没有涉及其他一些在别人看来或许更重要一些的原则,是因为“所有这八项原则都直接关涉与法治直接相关的事务中的政府制度和方法”(注:Joseph Raz,The Authority of Law,pp.218-219.)。莱兹解释说,他之所以抛弃富勒八项要素中的一些要素,主要是因为他对同一种体系内的法律之间的冲突持有不同的看法(注:见Joseph Raz,The Authority of Law,p.218,footnote7。)。在莱兹看来,由于法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模糊之处,完全符合法治是不可能的;由于某些受控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尚受青睐,最大限度地符合法治也是不受欢迎的。因此,符合法治只是、也只能是一个度的问题。与富勒不同,莱兹认为法治是法律必须与之相符合的一种理想标准,但法律可能并且有时的确最剧烈地、最系统地违反这些标准(注:见Joseph Raz,The Authority of Law,pp.222-223。)。
有趣的是,另一位当代著名学者菲尼斯(John Finnis)所列举的法治要件也是八项。在《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一书里,菲尼斯指出,法治是法制的一种特定德性(注:见John Finnis,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Clarendon Press,1980,p.270。关于法治与法制的不同,另见该书第271页。)。一种法律制度在如下八种意义上体现法治:第一,规则是可预期、不溯及既往的;第二,规则无论如何也不是不能够被遵循的;第三,规则是公布的;第四,规则是清楚的;第五,规则是相互协调的;第六,规则足够地稳定以允许人们依靠他们关于规则内容的知识而受规则的引导;第七,适用于相对有限情形的法令和命令的制定受公布的、清楚的、稳定的和较为一般性的规则的引导;第八,根据官方资格有权制定、执行和适用规则的人,一要对遵循适用于其操作的规则是负责的、可靠的,二要对法律的实际执行做到连贯一致并且与法律的要旨相符合。菲尼斯解释说,这八条都涉及制度和程序的品格,而不能仅仅看做某种语义的表达。例如,“一致”不仅仅要求法律起草中逻辑谨严,它还要求司法拥有权威,并积极超越相交叉或相冲突的规则的惯常公式去建立特别的和附加的调整性规则,而且在相关的同类案件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法院发生时遵守那些调整性规则。接着,菲尼斯指出,我们在每一个点上都可以看到法治涉及程序的某些品格,这些程序品格只有通过一种设立司法权威并且依靠那些在专业上合格并有循法动机的人来运用司法权威的制度才能够获得制度化的保障。这样一来,法治就还有许多由历史经验所表现的进一步的要素,诸如司法独立,法院程序公开,法院拥有不仅对其他法院而且对大多数其他官方机构的程序和行为进行审查的权力,以及法院对一切人(包括穷人)来讲可以方便地进入。(注:见John Finnis,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pp.270-271。)另外,菲尼斯认为,法治的各种规诫只是一个度的问题(注:见John Finnis,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p.270。)。
富勒、莱兹和菲尼斯在侧重和表述上虽有不同,但他们都把法治作为法律制度的一种特定品德,而且,他们对这种品德的把握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这里应注意的是,要把法律的一般特性与法律的特定品德区别开来,把法制与法治区别开来。我们可以说法律具有强制性、规范性,这是法律的一般特性,也就是说,这是法律有别于道德、宗教和政策的特性,是法律之为法律的缘由。但是,不是所有的法律制度都具备法治这个特定品德(注:菲尼斯在论述法治的要件之前,先论述了法律秩序的五个特征,它们证成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为基本的法律秩序提供基础,而法治作为基本法律秩序的一部分,保证该秩序运作良好并且有效能(同本文第126页注⑥书,pp.266-270)。)。我们可以说我们需要法律,但这并不必然表示我们需要法治。柏拉图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就象最野蛮的兽类一样”(注:转引自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卷,第127页。),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坚持人治。作为制度品德,法治相当于古人所说的“使法必行之法”(注:“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管子·七法篇》)。)。它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也不是凭靠严格执法或“一断于法”就可以实现的。应该把遵循法律与遵循法治严格地区分开来。
法治的规诫是法治之为法治的规定性,是法治的普适要素。综采诸说而损益之(注:这里有必要提请读者注意此前中国学者关于法治原则的一些讨论,例如,陈弘毅把法治概念分解为十个层次:社会秩序和治安、政府活动的法律依据、行使权利的限制、司法独立、行政机关服从司法机关、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基本的公义标准、合乎人权的刑法、人权和自由、人的价值和尊严(参见陈弘毅《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第62-69页);郭道晖把法治的基本问题概括为三:“什么法?谁来治?治什么?”并认为法治以治国家机器、治吏为重点,以宪治为本(参见郭道晖《法的时代精神》,第496-498页);张志铭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把“法治价值”叙述为合理预期、确定性、公开性以及高度和谐一贯(参见张志铭《法律解释的操作分析》,第188-190页);本人曾提出法治有三要素:通过法律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宪法和法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以维护民主、平等和自由为核心价值(见《中国人权百科全书》“法治”条);等等。),我们可以把法治的要件或要素表述为以下十个方面,这十个要素也是养成法治品德所必须牢记和依循的基本规诫。
(二)法治的十大规诫
1.有普遍的法律
法治所要求的法律普遍性主要有三层意思。第一,规范的制作要有一般性。就是说,法律规范要比特定的案件或细节宽泛或一般,能够包罗、涵盖后者,不能一事一法,一事一例。规则表述的抽象程度与规则调整的普遍程度是成正比的。古代罗马人得以最终用法律征服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法学家们创造了用抽象概念表述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技术。在现代法律里,作为母法或根本法的宪法在原则和规则的表述上尤其必须具备高度的抽象性、一般性,不能因事立法、因人设制。同样基于对法律一般性的要求,对现代社会里驳杂不纯的乡俗里规之于法治的意义不宜做出过于幼稚的估量。第二,规范的适用要有一般性。这主要指相同的情况必须得到相同的对待。就是说,在规则中的操作性语词的外延范围之内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被确认是在操作性语词的外延范围之内,并因此是在规则的范围之内。如果一项规则命令:“为本法21条所管辖的人不得加入沙龙”,那么,它就必然适用于受21条管辖的一切人和一切沙龙。我们不能从中挑出某些人或某些沙龙,然后说,我们的规则只适用于这些人和这些沙龙。一般性还表示法官和其他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应该限制在适用或解释规则的范围内。倘若官员能够对于同属操作性语词的外延之内并因此是在规则管辖内的两件事情做出不同的处理,那么,规则的一般性就遭到否定。如果官员对某些未成年人或沙龙给予不同的对待而并没有说明他们(它们)不是“真正的”未成年人或“真正的”沙龙,那么,就没有法治所要求的“规则”(注:参见Margaret Jane Radin,Reconsidering The Rule of Law,69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1989,pp.785-786。)。第三,法律制度具备统一性。此乃古人所谓“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注:《尹文子》。)。在此意义上,一国可以有两制或多制,但不能有两法或多法。一国之内可以有属于不同法系、不同语言、不同渊源、乃至不同政治性质的法律制度,但是,这些不同的法律制度在法理上严格说来都应该看做一法之下的两制或多制。综上述三点,可以认为,一个相对成熟的法律体系是法治的前提,无论它是以法典为主导,还是以判例为主导。这大概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对法律普遍性的“思维地理解”(注:“否认一个文明民族和它的法学界具有编纂法典的能力,这是对这一民族和它的法学界的莫大侮辱,因为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其内容是崭新的法律体系,而是认知即思维地理解现行法律内容的被规定了的普遍性,然后?它适用于特殊事物”(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第220页)。)。
2.法律为公众知晓
法律必须公布,晓之于民众,以便被指望服从规则的人们了解规则是什么。富勒就此提出三条理由:第一,即便百人里仅有一人去了解公布的法律,也足以说明法律必须公布,因为至少此人有权利了解法律,而此人又是国家无法事先认定的;第二,人们通常不是因为直接了解法律而是因为仿效了解法律者的行为样式而守法,故少数人的法律知识可以间接地影响许多人的行为;第三,法律只有公布后才能由公众评价并约束其行为(注:Lon L.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p.51.)。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子产与叔向曾就成文法及其公布问题展开争论。此后,关于法律宜向常人公布的理论占据主导,并有不少精彩论述。例如,“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乱法者也。”(注:方孝孺:《深虑论》,载《逊志斋集》卷二。)让守法者知立法之意,已经超出了关于法律公布与否的争论,对“晓之于民众”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实际上,这正是现代法治论者们所考虑的。例如,菲尼斯在解释作为其法治要素之一的“公布”(promulgation)时指出,“‘公布’不是单单通过印制许多清晰易读的法规、决定、格式和先例的官方文本就可以完全达成的:它还要求存在一个职业的律师阶层。律师们从事在浩瀚的法律书典里寻知引路的工作,任何需要知道自身处境的人都可以从律师那里获得咨询,而无需遭遇不应有的困难,付出不应有的代价”(注:John Finnis,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p.271.)。这一条规诫及菲尼斯的解释,为我们从法治的立场进一步理解十余年来我国的普及法律常识运动和规设方兴未艾的法律援助事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3.法律可预期
规则之存在须在时间上先于按规则审判的行为。“法无明文不罚”。无人能遵循溯及既往的法律,因其行动时该项法律并不存在。所以,既不能制定也不能适用溯及既往的法律。可预期性是支撑法治价值的一个较为关键的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讲,本文所述法治的其他规诫都是为了保证可预期性或为可预期性所要求的。哈耶克曾把法治定义为要求“政府的所有行为由事先已经确立并公布的规则来限定,规则使得用公平的确定性预见当局在给定的情况下怎样运用其强制权力成为可能”(注:Freidrich A.Von Hayek,The Road to Sefdom,1944,p.54.)。不过,如所周知,二战后对德国纳粹的审判牵涉到法律的溯及既往问题。莱兹认为,某些时候如果要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也不能与法治原则相冲突。菲尼斯认为,法律的可预期只有通过对司法采用新的法律解释施加某种约制才能得到保障(注:参见John Finnis,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p.271。)。
4.法律明确
规则必须能够为其接收者所认知和理解。商鞅认为,法律应该是为普通人而不是为圣贤订立的规则,所以“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知偏能知之”(注:《商君书·定分篇》。)。晋代法律家杜预则主要从知识角度来讲这个道理:“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易见则人知所避,难犯则几于刑措。”(注:杜预:《上律令注解奏》。)在现代社会,立法机关如果制定模棱两可的法律,就构成了对法治的侵犯。富勒说,人们一般认为,只有行政官、法官、警官和检察官才会侵犯法治,立法机关只有在违反宪法对其权力的限制时才会危害法治。其实,立法机关制定一项模糊不清、支离破碎的法律也同样会危害法治。当然,强调法律的明确性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在立法中使用像“诚信”和“适当注意”等准则。对法律的明确性要求也不能过分,一种华而不实的明确性比老老实实的含糊不清或许更有害于法治。
5.法律无内在矛盾
被期待服从规则的人们不能同时被命令去做既为A又非A的事情。富勒说,如果一项法律里有一条规定车主应该在1月1日换照,另一条却规定在1月1日从事任何劳动皆属犯罪行为,就会危害法治。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院应该通过解释来解决矛盾,如只承认前一条,使车主在1月1日装牌照不构成犯罪,或者只承认后一条,使车主将装牌照的时间合法地推迟到1月2日。但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将这两种解释结合起来,使车主无论在1月1日还是推迟到1月2日装牌照均属合法,这样,就使得公民能够自行解决法律的矛盾而不致损害自己。(注: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60页。)除了同一法律的不同规定之间的矛盾外,更常见的情形是几个法律之间的矛盾。公认的解决原则是“后法优于前法”,基本法优于派生法。有时则通过前述的调整矛盾条款的办法来解决,但这种办法也会带来不少的困难。总的说来,因立法草率造成的法律矛盾对法治是极为有害的。
6.法律可循
规则的接收者必须能够使他们的行为与规则相符合。富勒说,人们通常认为,任何神智健全的立法者,甚至邪恶的独裁者,也不会有理由制定一项要求人们去做不可能做的事情的法律,但现实生活却与此相反。立法者可能微妙地、甚至善意地制定出这样的法律,这就像一位好教师为增长学生的知识而对学生提出超出其能力的学习要求。但是问题在于,倘若学生未能完全实现教师的不切实际的要求,教师可以就学生已完成部分要求而表示祝贺;如果立法不切实际,政府官员就会面临这样的困境:要么强迫公民为其不可能为之事,以至造成严重的不义;要么对公民违法视而不见,从而削弱对法律的尊重。(注:参见Lon L.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pp.70-79。)在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里,规则应该具备的首要品性就是“必须做的即可能做的”。它有三层意思:一是法律规则所要求或所禁止的行为是人们能够被合理地期待去为或不为的行为;二是立法者、法官和其他官员必须相信法律能够被服从并预设命令能够得到贯彻,而且这种诚信为守法者所认可;三是与规则相符合的不可能性因此应该被确认为一种辩护理由。(注:参见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236-237。)
7.法律稳定
规则不能改变过快以至难以学习和遵守。若法律变动过于频繁,人们便难以了解在某个时候法律是什么,而且不可能在法律的指导下作长远规划。当然,法律应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动,及时地废、改、立,但是,频繁改变的法律和溯及既往的法律一样危害法治(注:美国宪法的制作者詹姆士·麦迪逊曾严厉谴责当时美国议会频繁改变法律。他认为,法律随政策而变化,将会使立法成为有权有势、胆大妄为者的专利,成为勤奋劳动、消息蔽塞者的圈套。参见《联邦党人文集》第44篇,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0页。)。法律不稳定之所以会危害法治,是因为它一方面会破坏法律所应有的确定性、可预期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则会造成社会的权势者通过法律侵害私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在这个意义上,保持宪法的稳定对于一国的法治至关紧要。稳定性乃是宪法内在的“刚性”,它与通常所说的与“柔性宪法”相对应的“刚性宪法”里的“刚性”有些不同。后者可以说是一种外在的“刚性”,它仅就宪法修改的程序设计而言,与宪法是否稳定并无必然关联(注:柔性宪法与刚性宪法的划分出自英国学者布莱斯(Bryce),依此,修宪机关和手续皆同于普通法律者,宪法为柔性;异于普通法律者,则为刚性。王、钱二氏认为,刚性宪法之优点在于“含有固定性”,柔性宪法因修改甚易而缺乏固定性。但他们又承认,欧战后新起国家的宪法绝大多数为刚性宪法,但其刚性程度“均不甚高”,而且法西斯德国“使刚性宪法变成柔性”(王士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3页)。这样的论点有些似是而非。因为宪法的“固定性”并不必然取决于其修改机关和手续。法西斯所为不是使刚性宪法变为柔性宪法,而是蹂躏宪法,是让宪法成为一纸空文。)。对于宪法的稳定性来讲,最重要的,一是制定出一部好的宪法,它的原则和规则可以镂之金石,恒久不变;二是宪法的修改或解释须忠实于宪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则,从而有别于宪法的重新制定。或许正因此,在美国,宪法判决过程中的遵循先例原则被看做法治的关键性要素。
8.法律高于政府
任何社会里的法律皆有权威,法治所要求的法律权威是立于政府之上的权威。任何社会里的政府皆有权威,法治所要求的政府权威是置于法律之下的权威。这里的“政府”包括一切掌握国家管理权力或执政的个人、群体、组织或机构,不仅仅指行政机构。作为一个与“人治”相对立的概念,法治本身就是为了通过法律遏制政府权力而不是为了通过法律管治普通民众而提出来的。一种符合法治要求的政治可以称作“宪政”。一种符合法治要求的法律制度,一方面,要通过法律的普遍、公开、明确、稳定、可预期等品性来体现,另一方面,要通过关于立法、司法、行政的一套制度性安排来保障。这种制度性要求要有三:第一,官方行为与法律一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注:《孟子·离娄篇》。)一般的、公开的、明确的和相对稳定的规则都要通过政府来实行。问题在于,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时常通过特定的法律命令将弹性引入法律。一个维持交通、颁发执照的警察若任意妄为,虽然只涉及法律的极微小而短暂的一部分,也足以危害法治。因为它使人们难以根据自己的法律知识来规划生活。因此,必须有一套确保官方行为与法律一致的制度和原则。这就是富勒所说的同一性,即业已确立的规则必须与能够从官员(如法院和警察)的执行模式里推断出来的规则相适应(注:“可以肯定地讲,法治的实质是:在对公民发生作用时(如将他投入监牢或宣布他主张有产权的证件无效),政府应忠实地运用先前宣布的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其权利和义务的规则。倘若法治不是指这个意思,那就什么意思都没有”(Lon L.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pp.209-210)。)。用莱兹的话说,就是应该在公开、稳定、明确而又一般的规则的指导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或者说,特定的命令应该只能在由更持久的并且对特定的法律所导致的不可预期性给予限制的一般法所设定的框架里制作。在莱兹看来,这个框架可以通过两类一般规则来创立,一类规则授予必要的权力以制作特定的规则,另一类规则就被授权者如何行使权力规定若干义务。(注:Joseph Raz,The Authority of Law,pp.215-216.)第二,设立合理、严格的适用和解释法律的程序。对于树立法律的权威来讲,最关键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官方尊重法律的政治意愿,而是一些程序性安排。其中,法律解释十分重要。法治要求法官和其他官员在适用法律时要遵循与整个法律制度相符合的解释原则。这里涉及自由裁量权问题。法治并不排斥自由裁量权,因为“没有灵活性地坚守实在法,把法治的美德——恒常性、可预测性、非人格化和自我克制——变得看起来荒唐、拙劣或不人道并不能使死守法律者比破坏法治者更高尚”(注:波斯纳(Richard A.Posner):《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波斯纳认为,自由裁量权并不必然构成对法治的侵犯。他说,我们不会因为有时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来处理疑难案件和行政部门可以不提出何种理由即赦免罪犯,就认为制度“不自由”了。自由国家应该是规则和自由裁量权的混合。不要用“自由”来贴标签。“我们的法律制度是否被称为‘自由的’不应当是重要的。实践中的问题是,我们的制度是否比应该有更多规则和较少裁量权的制度更好一些,或者是比一个有更多裁量权、更多标准和较少规则的制度更好一些。”(同上书,第78页))。但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必须遵循法律,这是法治与政治的一个基本区别(注:波斯纳承认,“在法官遵循(法治)的意义上,法律不同于政治”(Richard A.Posner,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1990,p.153)。)。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建立分权制衡的政府权力结构。正如本文第一部分叙述的中世纪不同政治实体之间的分权制衡对法治的意义所表明的那样,这样的权力结构有一种对法律权威的内在需求,并能够遏制任何一种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避免出现政府的任何一种权力分支(如立法、行政或司法)“自己立法、自己解释、自己执行”的情形。在此意义上,经典的法治观念都把分权制衡作为防止人治的一个关键。(注:例如,1799年《马塞诸塞权利宣言》规定立法、行政和司法分权“以达成法治而非人治”;戴雪说:“与法治形成对照的是这样一种政府制度,它立足于某些有权威的人行使宽泛、专横或随意的强制权力”(Albert.V.Decey,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p.188)。参见Paul R.Verkuil,Separation of Powers,the Rule of Law and Idea of Independence,30 Wm.&Mary Law Review.1987;另参见本文第121页注③。)
9.司法威权
设立司法机构负责在案件中适用法律,并且对案件在法律上的是非曲直做出最终判断和结论,乃是法律制度至关紧要的部分。司法没有权威,法律便没有权威。司法威权包含两个基本要素。第一,法院应该有权通过司法程序审查政府其他部门的行为,以判定其是否合乎法律。如果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不能由独立的法院来验证,就难以使政府机构的运作通过法律并置于法律之下。当然,司法审查只是维护法律权威的一种途径,而且也不无缺陷。立法机关介入执法,如北欧有些国家推行的“议会督察官”制度,也不失为一种尝试。第二,司法独立。如果司法依附于法律以外的权威,便不可能依靠司法来实现法律的统治。司法独立不仅仅是审判独立,它包含一系列关于法官任命方法、法官任期安全、法官薪金标准以及其他服务条件的规则。这些规则旨在保障法官个人免于外部压力,独立于除法律权威以外的一切权威,因此对于保持法治颇为关键。另外,司法独立不仅仅依靠关于司法体系的制度设计,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司法阶层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崛起。(注:关于司法阶层的重要性,参见贺卫方《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载《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
10.司法公正
既然几乎任何法律管辖下的任何事情都要由法院最后做出结论,如果一件事情进入诉讼而法院不能公正地适用法律,那么,法律便失去了意义,劝导人们遵循法律也会徒劳无功。换言之,既然法院要对法律是什么做出结论,那么,只有法官公正地适用法律,才能通过法律来伸张社会正义,当事人也才会受法律的引导。不然的话,人们就只能根据其他的考虑而不是根据法律来猜测法院的决定。培根说,一次不公的判决比多次不公的行为祸害尤烈,因为后者不过弄脏了水流,前者却败坏了水源(注:参见《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有时候,即便立法不公,司法公正也有助于保障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司法公正首先指在适用法律上的公平。这种“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道理在中国古人那里已经说得很明白。如《管子》:“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慎子》:“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缺也”。在现代司法里,适用法律的公平要求形成一个保证获取真相和正确执法的包括审判、听证、证据规则、正当程序在内的制度结构,同时,协调好司法过程中不同权利的冲突,如公平审判权利与新闻自由权利的冲突,公开审判与公共安全的冲突等(注:参见拙文《西方新闻自由探讨——兼论自由理想与法律秩序》,《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确保审判不“因公共喧嚷而有先入之见”(注:John Rawls,ATheory of Justice,p.239.)。其次,法律公正还要求在拥有法律资源方面的公平。对普通人来讲,到法院打官司应该是容易的,这样,个人主张其法定权利的能力便不会因诉讼的长期拖延或过度花费而耗尽。在美国的制度设计里,维护法治原则主要是通过法院。但这种方式也有许多的问题。例如,当事人是否有提起和承受诉讼的意愿和能力(如财力)。美国学者格兰特在70年代发表的一篇被视为法律社会学经典之作的文章,研究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便你在法律上拥有若干包括诉讼权利在内的权利,如果你不拥有或社会没有为你提供可以确保你通过法院来获得救济的法律资源,你的权利便得不到保障(注:Marc Galanter,Why t-he Haves Come Out Ahead:Speculations on the Limits of Legal C-hange,9 Law and Society Review,1974.)。
三、法治的基本价值
法治的规诫十条也好,八条也罢,它们都要通过特定社会里的传统、伦理和制度来获得真实的意义。接下来就该讨论怎样理解和运用这些规诫。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要订立这些规诫?这些规诫的价值何在?进言之,为什么要追求和维护法治?
(一)法治的工具价值
大致说来,有这样两种对法治的不同理解,一种是工具性的,一种是实体性的。按照工具性的理解,法治的价值仅在于保证规则的有效性。换言之,推行法治就是为了科学地制定并有效地实行规则。用流行的汉语语式,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种理解显然是不妥当的。一个纳粹政体想通过规则来实现其令人发指的目标,它也会使命令的制定和实施符合这种意义上的法治要求。如果这样理解法治的话,那么,“在原则上,一个基于否定人权、普遍贫困、种族隔离、性别歧视和宗教迫害的非民主的法律制度就会比任何一种较为开明的西方民主政体的法律制度更符合法治要求”(注:Joseph Raz,The Authority of Law,p.211.)。弗里特曼曾说,“法治简单地指‘公共秩序的存在’。它的意思是通过法律指挥的各种工具和渠道而运行的有组织的政府。在这一意义上,所有现代社会,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自由主义国家,都处在法治下”(注:弗里特曼:《法律与社会变革》,第281页,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66页。)。
这样一种绝对的工具主义法治观只看到法治的外壳,而无视其精神。应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蔑视和践踏人类尊严的暴行已经为这样的法治观敲响了警钟。因为法西斯主义者的确曾以立法多、执法严而标榜法治国,希特勒也是在不无法治传统的德国通过合法程序上台的。这样,如果不能确认和树立某些绝对的、超越的道德价值,如果不能承认在实在法的体系之外还有一个自然法的、道德法的体系,那么,法治便不可能提供一个谋求广泛的、实质正义的制度框架,尤其是不可能通过法律来遏制蔑视和践踏人类尊严的暴行(注:参见Geoffrey de.Walker,The Rule of Law:Foundation of Constitutional Demacracy,1988,p.5。)。在劳伦斯·却伯(Laurence H.Tribe)看来,法治蕴含情感,而不仅仅是一些形式主义的观念。他在《回到法治》一文里针对斯卡里尔法官在哈佛大学1989年度霍尔姆斯演讲发表的捍卫“法治作为规则的法律”的观点,强调“在法的统治与爱的统治之间不该有绝对的冲突”,指出,尽管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因为同情受害人或憎恶加害人而不去破坏或歪曲法律,但是,倘若认为我们的“法律”概念是用直尺和圆规组构的,全无情感和怜悯,则是绝对错误的(注:Laurence H.Tr-ibe,Revisiting the Rule of Law,64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1989,pp.728-730.)。
把法律看做规则,把法治看做规则有效性的向导,这样的理解首先忽略了作为规则遵循者的人。它不仅于实践有害,在理论上也是片面而肤浅的。作为法律制度的一种品德,法治所要求的若干规诫在表面上的确带有工具性,但是倘若细加推究,便不难发现,它们是以若干重要的实体价值为支撑的。也就是说,法治本身在价值上并非全然中立。富勒认为,他所说的以前述八项规诫为内容的法律的“内在之德”,作为“程序自然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立的,例如,法治对避孕的道德问题无能为力。法律可以做出鼓励性规定,也可以做出禁止性规定,但无论哪种规定都不妨害法律内在的完整性。但是,不能认为法律无论采取任何实体目标或价值都不会危害法治。法律的内在之德虽然对宽泛的道德问题可能是中立的,但若以人为视角来看却不可能是中立的。因为人是或者可以成为一个负责任的道德主体,“以不公布的法律或溯及既往的法律来审判人的行为,或命令其为不可能为的行为,便是向人转达对其自决能力的漠视”(注:Lon L.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p.162.)。正是在此意义上,富勒认为纳粹不可能实施法治,即便是法治的形式要件也不可能满足。在法西斯德国,“合法性普遍而剧烈地败坏”(注:Lon L.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p.40.)。比如,法官为了一己之便,或害怕来自“上面”的不悦,在审判中根本不顾法律,甚至不顾纳粹党人自己制定的法律(注: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58页。)。
吾国先贤梁启超也曾激烈批评工具性法治观。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法治主义有两大缺点,一是立法权操于君主之手,“不能正本清源”,故法治实为专制;二是把法律作为尺寸,把人视为可以用尺寸来度量的“布匹土石”,否定人的自由意志,故法治主义实为“物治主义”(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本论,第十六章。)。
不过,揭露工具主义法治观的谬误不是要否定法治的工具品德,不是要否定规则之于法治的意义,不是要否定法治本身的形式主义要求和规则本身的确定性。在波斯纳看来,第一,法治首先是法律秩序的一种管理功能,是一种程序框架,通过这种框架,法律结果更容易识别并用于取得其他政治目的的计算。第二,在维护法律秩序稳定的意义上,法治是一种“公共的善”。法治能够确保法律秩序里的变化不会突然地或大规模地发生,而是要经过一段合理的时间(注:参见Richard A.Pos-ner,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1990,pp.358,154-155。)。因此,应该把法律与政治区别开来。他指出,认为“法律即政治”的人忽视了容易案件的存在,并坚持认为法律若不实现其最过分的形式主义要求就不是法律(注: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中译本,第195-196页。)。莱茨认为,那些以应然的或价值的样式来看待法治的人们要冒落入循环陷阱的危险。他说,“设若法治不过是良法之治,那么,阐释法治的性质就是提出一套完整的社会哲学。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法治这个词汇就会缺乏任何有用的功能。我们无需仅为昭示笃信法治即笃信善良当居优势而皈依法治。”(注:John Raz,The Authority of Law,p.211.)在莱兹看来,法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消极价值。法律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专横权力的危险,而法治则是将法律自身造成的危险最小化的一种设计。同样,法律可能是不稳定的、模糊的、溯及既往的并因此侵害人的自由和尊严,法治则被用来防止这种危险。这样一来,法治在两种意义上是消极价值:第一,遵循法治只是靠防恶而致善;第二,法治所防避的恶乃是只能由法律自身造成的恶。这就像作为一种品德的诚实在狭义上只能解释为不欺诈那样。这样的理解与韩非的法治观倒有几分相像。例如,韩非认为法治的实质是“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注:《韩非子·显学篇》。)。故而“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注:《韩非子·六反篇》。)。不仅如此,莱兹认为,把法治看做法律的一种内在品德是法律的工具性概念的结果。任何工具都有作为工具的道德中立性,这种品性就是效能。对于法律来讲,法治便具有工具品性。在此意义上,法治不是一种道德价值。当然,莱兹并不否认遵循法治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但是,他在批评哈耶克时警告说,承认法治所具有的无可置疑的价值不应该导致对法治重要性的夸张的期待。遵循法治使得法律成为达成某种社会目标的良好工具,但遵循法治本身却非终极目标。“在法治的蔡坛上牺牲过多的社会目标会使得法律贫瘠而空洞”(注:Joseph Raz,The Authority of Law,p.229.以上转述见同书第219-229页。)。富勒在阐释法律的内在之德时似乎认为,在正义问题能够被有意义地提出来之前,按规则统治是必须的(注:参见Lon L.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p.157。)。
(二)人类尊严与自由:法治的核心价值
法治不仅仅意味着法律秩序和相关的操作技术,也不仅仅意味着有更多的社会关系由法律调整。对法治价值的实体性理解着眼于法治本身所包含的道德原则和法治所要达成的社会目标,依此,法治被看做一种培育自由、遏制权势的方法,看做人类作为负责任的道德主体或自由意志主体所从事的一种道德实践。这样的理解可以往前推至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和法律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正义和善德,他把法律的权威看做道德理想的一部分。不过,如何界定和表述法治的实体价值是当代思想者们正在热烈争论的一个领域(注:不过,就具体的理论家及其学说而言,在工具性理解与实体性理解之间划一个绝然的界限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例如,有的西方学者把莱兹、富勒的法治论划为工具性的,把罗尔斯、德沃金、菲尼斯划为实体性的。参见Margaret Jane R-adin,Reconsidering The Rule of Law,69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1989,pp.783-791。有的中国学者把西方法治理论模式分为“自然的”、“合法性的”、“形式正义的”和“全面正义的”,并且把罗尔斯划入“形式正义的”。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14-625页。)。那么,他们是如何论证和表述的呢?
莱兹尽管坦言法治的消极价值,却仍然对法治价值有实体性的把握。他把法治的价值概括为三:第一,法治能够抑制专横的权力。第二,法治使法律自身成为个人计划的一个稳定、可靠的基础,此即哈耶克所说的个人自由。在莱兹看来,自由意味着在许多可能性中做出选择的有效能力,而人们所处环境的可预期性会增进人们的行为能力。不过,这样的自由不同于政治自由。政治自由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禁止某种形式的干涉个人自由的行为,如刑事犯罪;二是限制公共权威的权力,使它对个人自由的干涉最小化,如政府不能限制迁徙自由。法治对个人自由的保护或许是另一种模式。第三,如果法律是尊重人类尊严的,那么就有必要谨循法治。尊重人意味着把人作为有能力计划和规设自己未来的个体来对待,因此,尊重人包括尊重他们的自治,尊重他们控制自己未来的权利。当然,由于自然的或个人天赋与能力的限制,人们对其生活的掌控从来就是有限的,而且,个人生活总是会受到其他人行为的影响,但只有三种干涉才会构成对人的尊严或自治的侵犯,它们是侮辱、奴役和操纵。在此意义上,莱兹指出,“法律可能会以许多方式侵犯人的尊严。遵循法治无论如何也不能保证不发生法律对人的尊严的侵犯。但是,故意漠视法治显然是侵犯人的尊严的。”(注:Joseph Raz,The Auth-ority of Law,pp.221-222.)在莱兹看来,违反法治有两种形式:一是法律不确定,即法律不能使人们预见未来的发展或形成确定的期待(如法律模糊,允许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二是让人们对法律的期待破灭或无望,即鼓励人们依靠现行法律并根据它作计划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表象因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或妨害正当的法律实施而破碎。不确定之恶在于为专横的权力提供机会并限制人们规划其未来的能力,而期待破灭之恶尤大,因为它侵犯了人作为自治主体的尊严。
与莱兹不同,哈耶克、德沃金、罗尔斯、菲尼斯等思想者更多地关注法治对自由主义的直接承诺。哈耶克十分赞赏古罗马思想者西赛罗“为了自由,我们才服从法律”的论断。在他看来,自由是自发社会秩序存在的必要条件,而一般规则则是自由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对一般规则的诉求也就是对法治的诉求。(注:参见邓正来《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9页。)在《自由的构造》一书里,他写道:“为本书首要关注的法律下自由的概念奠基于这样一个论点:当我们服从既定的、不管对谁都适用的一般性抽象规则意义上的法律的时候,我们没有服从他人的意志,并因此是自由的。这是因为,立法者并不知道他的规则将适用的特定案件,同时,适用规则的法官在按照既定的规则体系和案件的特定事实得出结论时是无可选择的,这样,就可以说是法治而不是人治。”(注:F.A.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1960),pp.153-154。译文参见《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90-191页。该译著及前引著均把"conception of freedom under the law"译为“法治下的自由”。这一译法似欠妥当,因为哈耶克在这里所说的自由是存在于法治状态之中的。)
如果说哈耶克突出了法治与自由的密切关系(注:G.C.Roche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要感谢哈耶克的洞见,是他使我们现在认识到了自由与社会组织的密切关系以及自由与法治的密切关系”(转引自邓正来《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研究》,第148页)。),那么,德沃金就强调了法治里的权利价值。他说,实际上有两种极不相同的法治概念,一种是“规则本本”(rule-book)概念。德沃金认为该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狭隘的,因为它没有规制任何可能纳入规则文本的规则的内容。它只是坚持凡纳入文本的规则皆须遵循直至其被变更,而把规则的内容作为实体正义问题,并认为实体正义不属法治理念的一部分。另一种法治概念是“权利”的概念。在他看来,法治的权利概念在不少方面比规则本本概念有雄心,因为它预设公民相互间享有道德权利并承担道德义务,并预设公民享有针对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利。就可操作而言,法治的权利概念坚持这些道德的、政治的权利由实在法认可,以便可以根据公民个人的要求通过法院或其他同样类型的司法设制来实施。因此,这样的法治“是一种按照准确的、公开的个人权利概念来治理的理念。它不像规则本本概念那样在法治与实体正义之间作区分,相反,它要求,作为法律理念的一部分,规则文本里的规则要统摄和实施道德权利”。(注:Dowarkin,A Matter of Principl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11-12.)
罗尔斯把法治看做他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方案的一部分。法治是适用于法律制度的形式正义——“公共规则的恒常的、无偏袒的施用”(注: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235.),它旨在促进自由这个作为公平的正义里的首要价值。那么,罗尔斯又是怎样论证法治之于自由的价值的呢?
罗尔斯构设了一个法律的理性模式,在这个模式里,他提出了关于法律制度的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定义:“法律制度是一种发布给理性的个人以调整其行为并提供社会合作框架的公共规则的强制秩序。”(注: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235.)罗尔斯解释说,从这个概念里可以推出许多关于法治的传统规诫。首先,“法律制度是公共规则的一种强制秩序”一语预设法律是由规则构成的。其次,为了调整行为并因此取得为正义所必须的社会合作,规则必须具有某些与法治相符合的特征:必须做的意味着可能做的;相同情况相同处理,限制司法自由裁量权;“法无规定不为罪”;法律必须以清楚的意思被告知并且被明确地规定;审判必须公平、公开。罗尔斯提出了两个论点来连接这些法治规诫与自由这个基本的实体价值。首先,他论证说,缺乏这些特征将导致令人胆寒的结果。倘若规则是模糊的,相同情况得不到相同处理,或者司法程序无常规,“我们的自由的边界就是不确定的”。当这些边界不确定的时候,“自由就会为对自由之行使的合理恐惧所限制”(注: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26.)。这样一来,处于原始地位的理性个人若要选择一种法律结构来促进他们的最高价值——自由,他们将会由于需要法律后果的可预见性、决定性和确定性而选择法治。罗尔斯为连接法治与自由所推升的又一论点是所谓“霍布斯命题”。在罗尔斯看来,以在自然状态条件下增进自由为宗旨的社会合作规划有着对法治规诫的要求。因为在自然状态下,为了排除自私的个人破坏只要他们一体遵循便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规则,一种强制的主权者便成为必要。“有效的刑罚机制的存在有益于人们相互之间的安全。”(注: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240.在较近的著作里,罗尔斯明确地表述,如果一种自由的政治秩序要一直稳定下去,它就必须奠基于道德共识,而不仅仅是霍布斯的"modus viendi"(John Rawls,The Idea of an Overlapping Consensus,1987,7 Oxford J.Legal Study,pp.1,9-12.)。)所以,即便正义的“理想理论”也要求考虑刑事惩罚作为一种稳定的工具。一旦处在原始状态的理性选择者们确认了能够实施刑事惩罚的强制性主权者的必要性,他们还必须确认遏制这个权贵(利维旦)的必要性。为了控制利维旦,就需要法治。因为,“在法律按照合法性原则而无偏袒、有规则地实施的地方,自由所面临的危险就较少一些”(注: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241.)。
显然,在罗尔斯那里,尽管法治规诫的清单上开列的一般性、一致性、公布于众、可循性等与工具性的概念大致相同,但是,他所提供的正当性证明却很不相同。法治不是基于对行为控制的有效性的要求,而是基于传统自由主义的特定的政治观点。自由是一个核心价值。罗尔斯说:“在其他事情同等时,一种法律命令若更好地履行了法治的规诫,它就会比其他的法律命令更公正地实施。”因为“它将为自由提供更安全的基础并为组织合作规划提供更好的手段”(注: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236.)。正是基于自由原则,传统的工具性的法治规诫被赋予新的意义。以“法律为公众知晓”为例。他说,“如果公民不能够知道法律是什么并且未被给予公平的机会去考虑法律的命令,那么,刑事惩罚就不应该适用于他们”(注: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241.)。在他看来,这是因为惩罚不是基于报复或谴责而是基于自由本身。
菲尼斯把法治理解为人类交往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德性。法治规诫的基本点在于确保受权威支配的人们拥有自我主导的尊严,并免于某种管理方式的侵扰。也因此,法治存在于对正义或公平的要求之中。至于富勒及其批评者提出的专制暴政是否可能通过法治来达到其目的的问题,菲尼斯认为,这样的争论没有弄清这里的“可能”是逻辑的可能性还是历史的可能性。专制暴政没有自足的理由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来约束自己,因为这种自我约束的理性基点是互惠、公平和尊重个人这样一些为专制所敌视的价值。在菲尼斯看来,专制暴政有三类:一是剥削的,即统治者完全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顾社会里其他人的利益;二是意识形态的,即统治者追求他们认为有益于社会的目标,但他们追求的目标采取非理性的方式,而且忽视社会福祉的其他的基本方面;三是前两类的混合,如纳粹政体。这三类政体都不可能在它们的目标里找到任何遵循合法性约束的理性基础,因为它们想要的是确定的结果,而不是帮助个人在社会里建构他们自己。因此,把法治看做像双刃剑那样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效能性工具,是不对的。菲尼斯指出,“法治概念立基于这样的识见: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某种品格(它涉及互惠和程序公正)因其自身的目的而富有价值。法治不只是达致其他社会目标的手段,也不应该轻易地为其他的社会目标做出牺牲。法治不只是“社会控制”或“社会工程项目里的一种‘操作技术’”(注:John Finnis,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p.274.菲尼斯也看到,法治并不能保障公共福祉的每一个方面。因此,对法治局限性的探讨不仅是对用来体现和支持法治的司法方法的探讨,而且是对“法的一般理论”的探讨(同上书,pp.272-275)。)。
上面梳理了几位思想者把人类尊严和自由作为法治的核心价值的主要论点和论证过程。从这个核心价值出发,我们还可以推演出其他的相关价值。例如,法治对于民主的价值。民主并非法治的天然盟友。民主是一种社会计算,如少数服从多数便是一个计算规则,但是,若要在计算过程中遵循既定的原则并保障个人权利,不致出现“多数人的暴政”、“群众专政”或以整体利益剥夺个体利益的情形,就必须严格遵循比较明确的、一般的、客观的、尤其是载有个人权利条款的法律规则(注:参见ALLan C.Hutchinson & Patrick Monahan,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1987。)。在此意义上,没有法治或许可以有民主,但没有法治的民主不仅是残缺的,而且相当危险。
结语:法治的悖论与语境
以上所述仅限于从渊源、规诫和价值的角度勾画一个关于法治的认识框架。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得以把法治理解为一项历史成就和一种法制品德,并且在理解法治的工具效用的同时,认识它对于人类尊严与自由的意义。坦率地讲,这个认识框架可能为了其自身的目的而有意把某些问题简单化,并小心翼翼地避开某些矛盾和歧异。沃尔克曾这样揭示法治的内在矛盾:
一方面,法治表示对法律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的需求,以便人们得以相应地规划和组织他们的安排;但是,另一方面,法治又强调需要法律保有某种灵活性并且能够让自身适应公共观念的变化。一方面,作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推论结果,法治宣称对法律适用的一般性的要求;但是,另一方面,法治又小心翼翼地让平等原则不适用于那些可以或者应该做出合理区别的案件。不仅如此,司法独立被说成是法治的一个本质要素,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想让法官过于独立,以免法治蜕化为司法的暴政。(注:Geoffrey de.Walker,The Rule of Law,Foundation of Constitutional Demacracy,p.42.)
这段话触及了法治的几个悖论,即确定与灵活、稳定与变革、一般与个别、一律平等与差别对待以及司法独立与司法廉正之间的矛盾。当然,法治的内在矛盾不止于此。例如,在规则的治理与自由裁量权之间、个人自由与福利国家规划之间、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法律与情理之间以及法治与民主、人权等价值之间,还有许多的矛盾。这些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出自法律本身的矛盾,如,维持秩序与实现正义的矛盾。在这个矛盾里,秩序本身又存在一种内在紧张关系,它需要变革又需要稳定;正义本身又包含着个人权利与社会共同福利之间的紧张关系。伯尔曼把这类紧张关系视为西方法律传统的固有矛盾,并认为正是不同时期的正义观念与既存秩序之间的紧张为法律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契机(注:参见伯尔漫《法律与革命》导论,第25页。)。其实,这样的情形又岂止于西方?
法治是一门实践的艺术(注:参见Lon L.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pp.91-94。)。从某种意义上讲,法治是一个社会的、实践的概念。因为规则在本质上依赖于社会场合和重复性的人类行为(注:参见L.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G.E.M.Anscombe tr-ans.Rev.ed.1968.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规则的社会概念和规则怀疑论,参见Margaret Jane Radin,Reconsidering The Rule of Law,69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1989,pp.797-801。)。无论是被认为业已建成法治的社会,还是正在走向法治的社会,都会面临一些具体场合下的特殊问题。也就是说,怎样表述法治、怎样建成法治以及怎样操作法治在不同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是有着不尽相同的语式、路径和方法的。无庸讳言,尽管法治在本世纪里已经成为中国的流行话语,但迄今为止,我们在从学理上阐释法治的时候所使用的语言主要是翻译过来的西方语言,我们所援用的原理主要是翻译过来的西方原理。究其原由,一因西方法治先行,经验厚积,且学术经年,易成文化强势;二因法治乃人类共求之物,人类社会共通之理,故先知先述、多知多述者遂居语言优势;三因吾国近世灾难深重,学人难以从容梳理故旧,接应西学,且多患“文化失语症”,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讲述当前发生的与自己相关的事情。问题在于,翻译或许可以勉力做到所谓“信、达、雅”,而且“信、达、雅”的术语、概念、原则或许还可以在业已经过法律移植的新的制度环境里使用无碍,但是,倘若用它们作为工具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或者,来表述一种已经成为历史的不同的法律经验,就会成为一件极易出错的事情。例如,大凡论及中国思想史,都免不了要谈论“法治”、“德治”或“人治”之争。但是,这里的“德治”、“人治”、“法治”究竟指的是什么?如果从法理学角度观察并与现代法治理论相比较,我们或许会发现,通常所谓古人的“法治”、“德治”、“人治”,大都是根据当时思想者或学术流派的某些特征或趋向乃至他们所采用的特定语式,糅合今人的臆念所作的一些标识或归纳。离开了对特定语境的把握,我们很难理解其真实的意思,很难判断它们究竟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今天所说的法治、人治或德治,因此也就很难真正了解这些思想的真实意义和价值。在这里,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知识和语言的地方性,另一方面,则要真正下一番融会贯通的功夫。不然的话,我们的研究就只能是中西之间的一些简单的对照和褒贬(注:这也是本文在关于法治的历史渊源部分未敢轻易涉及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法治在中国的思想资源宜另作论述。关于近些年来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尤其是中西法文化比较研究之流弊参见拙文《批评本该多一些——答谢、反省与商榷》对“西方化”与“本土化”的评论(《中国书评》1996年第10期,第127-131页)。)。或许比把握中国古代的法治语境更为重要的是把握当代中国的法治语境。因为西学东渐以来,“官僚法”与“习惯法”的“短路式的接合”(注:参见季卫东《现代法治国的条件(代译序)》,载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第5页。)以及其后的社会政治的风云激荡使当代中国的法治语境变得极为特殊。中国走向法治的过程的确面临许多与其他国家既共同亦不同的问题(注:关于当代中国法治问题特殊性的不同讨论方式和不同见解,参见蒋立山《中国法治道路讨论》,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3、4期;苏力《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与法治》,载《法学研究》第二十卷第一期;公丕祥《法哲学与法制现代化》第五部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家福、刘海年主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科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李步云《走向法治》,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近二十年来,中国法学界的许多研讨都可以看做依循特定的路径、使用特定的语式来表述或树立法治的规诫和价值的积极尝试。例如,关于法律本质的讨论通过反省“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个命题,在“阶级性与社会性”这一讨论框架里提出了法律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可预期性等问题;法律与政策的关系的讨论不仅强调了法律的稳定性,而且潜在地提出了政府的政策、尤其是执政党的政策能否违反法律的问题;关于法律继承性的讨论通过争论不同阶级本质的法律之间有无继承性,从历史的角度、用特殊的话语触及了法律的普遍性、确定性和稳定性;关于法律本位的讨论提出了法律是“权利本位”还是“义务本位”问题,虽然争论各方所持的关于权利、义务的概念和关于“本位”的定义本身尚待商榷,但这样的讨论提醒人们关注现代法律中的民主、平等、自由等原则,尤其是在讲求依法治国的时候要超越漠视个人权利的古代法家的法治主义;关于法律文化的讨论尽管对于相对客观的、确定的中外历史上的法律给予了许多不客观的、不确定的解释,乃至任意的褒贬,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温“五四”前后的文化思考、进一步传播现代法治概念的重要途径;关于人权的讨论虽然也留有不少缺憾,但它通过张扬道德权利,为确立法治的价值原则、探讨法律运作过程中权利冲突的解决方案开辟了一条路径;关于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的讨论,从市场理性和市场规则的角度为普遍、客观、公开、可预期、稳定以及公正、平等、自由这些法治的规诫和价值提供了迄今为止在我国堪称最全面、最有说服力的正当性证明,尽管这种证成方法未免有些浪漫和粗糙,而且没有、也不可能论涉人的尊严和价值这一法治的核心问题;关于法律与社会的研究则为弄清中国社会里的法律观念、权利意识和法律运作机制,为弄清在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建立法治社会以及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法治社会做出了努力。
值得注意的还有相关语词的变化。“法治”本为汉语固有词汇,但一直不受青睐。1979年的一份中央文件明确使用了“法治”概念(注:法律“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但通常还是用“法制”一词,如“健全法制”,“加强法制”。近几年来,“法治”一词的使用日渐频繁,甚至多于“法制”。比如,以“法治国家”替代“法制国家”。我想,这一语词转换至少表示了两个变化:一是从一般地要求“加强法制”到要求告别人治;二是把法治看做法制的一种品德,并且意识到,这种品德不是所有的法制都具备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
本文写作承蒙学友吴玉章教授、张志铭教授、信春鹰教授、朱景文教授、朱苏力教授、郑强博士先后提供一些宝贵的资料或讨论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王好立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礻加氏
| 课件名称: | 河海大学:行政法学 |
| 课件分类: | 法学 |
| 课件类型: | 教学课件 |
| 文件大小: | 5.69MB |
| 下载次数: | 5 |
| 评论次数: | 4 |
| 用户评分: | 8.3 |
- 10. 河海大学:行政法学:ARICEBU1.GIF
- 11. 河海大学:行政法学:ARICEBU2.GIF
- 12. 河海大学:行政法学:ARICEBU3.GIF
- 13. 河海大学:行政法学:ARICERUL.GIF
- 14. 河海大学:行政法学:CYPRBK.JPG
- 15. 河海大学:行政法学:RICEBK.JPG
- 16. 河海大学:行政法学:公务员的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的划分
- 17. 河海大学:行政法学:关于现代行政程序的再思考
- 18. 河海大学:行政法学:案例分析
- 19. 河海大学:行政法学: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
- 20. 河海大学:行政法学: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 21. 河海大学:行政法学:10515977931
- 22. 河海大学:行政法学:ABSTRBU1.GIF
- 23. 河海大学:行政法学:ABSTRBU2.GIF
- 24. 河海大学:行政法学:ABSTRBU3.GIF
- 25. 河海大学:行政法学:ABSTRRUL.GIF
- 26. 河海大学:行政法学:ACDBULL1.GIF
- 27. 河海大学:行政法学:ACDBULL2.GIF
- 28. 河海大学:行政法学:ACDBULL3.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