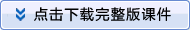中国宪法学向何处去广西大学法学院·魏敦友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矣。——梁启超(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一,页九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2003.)
今日国人谈及中国前途者,什有九心灰意尽,曰,噫,国其殆亡!国其殆亡!吾则以为我国人苟不自亡,他人决无能亡我者。 ——梁启超(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八册,专题之三十二,页二0,北京,中华书局,1989/2003.)
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田汉悼聂耳诗
(见拙文:《初入古滇国杂记》,http://weidunyou.fyfz.cn/blog/weidunyou/index.aspx?blogid=42912.)
宪法学应是现行政治的分析化验师和医师,不应是现行政治的涂脂抹粉者。客观理性的宪法学说、中立的研究立场,是中国民主政治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 ——杜钢建 范忠信(杜钢建 范忠信:《基本权利理论与学术批判态度》,载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页16。)
一我想再一次强调2005年对于当代中国法学/法制的里程碑式的意义,我甚至于认为2005年是这样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它是中国百年“知识引进运动的终结”,是中国人开始自己思考问题从而自已构建自己的生活秩序的开端。(参拙文:《音调未谐的变奏》、《“知识引进运动”的终结》等。http,//weidunyou.fyfz.cn.)
上述命题当然是有待证实的。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命题实出于我对2005年发生在中国法学界的诸多“事件”的感受。对上述命题而言,其中两个事件是值得反复提到的。一个是“邓正来事件”,一个是“巩献田事件”。是年伊始,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邓正来先生就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政法论坛》(2005年第1至4期)连续发表长篇论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正来教授深刻指出中国法学没有自己的理想图景,长期受到“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的宰制,并认为中国法学处在深刻的危机中,中国法学欲走出这个危机,必须结束受西方法律理想图景支配的法学旧时代,从而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章景”的法学新时代。同年8月12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巩献田教授发表质疑《物权法(草案)》的公开信,从多方面对物权法草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批评该草案违宪,从而在全国引起喧然大波,《物权法(草案)》因此没有象许多人所预期的那样进入2006年3月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我将邓正来教授的行为命名为“邓正来教授事件”,将巩献田教授的行为命名为“巩献田教授事件”。
我认为,中国法学/法制要想获得进展,必须将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解读这两个“事件”的内在意义。如果说邓正来教授从法学的层面预见了中国法学/法制的深刻危机,那么可以恰当地说,巩献田教授则在法制实践的层面使这个危机找到了自己全面爆发的突破口。对中国法制/法学的危机需要从历史与哲学的双重角度进行认真地清理,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知性工作。我注意到,巩献田先生公开信发表后,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反应,比较引人注目的,大概是2006年2月25日下午许多民法学家,还有宪法学家,聚集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法学院以研讨“物权法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的名义,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关于“《物权法》草案违宪、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公开信进行全面回应。(见http://legal.people.com.cn/GB/42731/4148610.html.)。十分蹊跷的是,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带给人的印象好象是“众口一词”,然而聪明的中国人心里明白,这要么是预谋,要么是有选择地报道,总之是太不可信了,正象华东政法学院童之伟教授针对此次会议的报道所敏锐指出的那样,“如果有人发表点不同看法,会议的共识可能会更可信些。”(童之伟:《〈物权法(草案)〉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评一封公开信引起的违宪与合宪之争》,注[5],见http://dzl.legaltheory.com.cn/info.asp?id=11248.)在我也感到迷惑不解的时候,我突然在“正来学堂”里面读到了此次会议参加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景文教授的文章《由〈物权法草案〉的争论所想到的》(在“物权法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见http://dzl.legaltheory.com.cn/info.asp?id=11190.),朱景文教授就在这篇文章中谈到了许多与物权法学者的“不同看法”,可惜的是,关于此次会议的报道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印痕!看来,中国学者们玩起政治来,一点也不比政治家们逊色!如果是这样,那么我要求中国人,请记住这一天,2006年2月25日,因为我认为这一天将成为中国法学的“耻辱日”!因为这一天将使中国人对中国法学家们是否具有“知性的诚实”发生深深的怀疑!因此这一天它也应该成为中国法学家们集体的“忏悔日”!不正视这种耻辱,不进行深刻的忏悔,不回归知性的诚实,中国法学没有希望,中国法制没有希望。而更重要的,是我从2006年2月25日这一天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以江平、王利明、杨立新等人为代表的中国民法学以及以许崇德、周叶中、韩大元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宪法学因为自我虚脱而无力面对当今中国现实,基本上已经走到了自己的逻辑终点。虽然它们还将在中国法学场域中存在一段时间甚至于相当长一段时间(必须有新的理论出来才能完全代替它们),但是它们从总体上讲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为了新的法学时代的来临,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清理中国法学/法制的知识系谱及其与政治权力的相互关系。本小文显然不可能完成这一重大任务,也不是为了这一重大任务而来,因为确切地说,本小文的写作机缘只是因为读到了华东政法学院童之伟教授的针对“巩献田教授事件”的大作《〈物权法(草案)〉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评一封公开信引起的违宪与合宪之争》(见http://dzl.legaltheory.com.cn/info.asp?id= 11248.),感到中国宪法学界并不乏深思明辩之士,一时高兴,竟不揣浅陋而作此文向童教授致意,并借此机会清理一下对当代中国宪法学的一些零星看法,而象中国民法学的知识系谱则应该由专门的民法学之才学之士去认真清理的。
二在此次“巩献田教授事件”中,中国宪法学家们的表演令人吃惊。在巩先生质疑《物权法草案》违宪之后,中国“著名的”宪法学家们不去研究到底什么叫违宪、如何检验违宪以及进一步去深入探讨中国宪法学的当代使命,却匆匆忙忙加入到民法学/物权法学者所主导的“《物权法草案》并不违宪”的大合唱中,失去了一个宪法学家对事物的甄别力,从而客观上成了民法学/物权法学者的“侍者”,完全丧失了中国宪法学家的尊严。中国宪法学家在“巩献田教授事件”中的这种表演,在我看来,并不是偶然的,它充分说明中国宪法学已经陷入困境,因此只能在现实的波澜中随波逐流。北京大学法学院徐爱国教授批评中国法理学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自己,因为“国家设定了法学和法理学家,不是让他们做法律具体的政治性的工作,而是需要他们拿出有理论价值的成果,这应该是一个学者的责任”。(徐爱国:《困境与出路:对中国法理学的遐想》,http://dzl.legaltheory.com.cn/info.asp?id= 11098.)我曾经在一篇小文章《中国法理学向何处去》中认可了爱国教授的这一观点(http://weidunyou.fyfz.cn.)。现在我想说的是,在我看来,爱国教授对中国法理学家的这种严厉批评同样适用于中国宪法学家,甚至于更适合于中国宪法学家。
然而,在我对中国宪法学家在“巩献田教授事件”中的表演深感失望的情况之下,我终于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宪法学家出场了,他就是上海华东政法学院的童之伟教授。这位曾经的珞珈(武汉大学)学子,辗转武汉来到上海,从上海交通大学而华东政法学院,著述虽然不多,却巍然屹立而有智者之思,五年前(2001)因从吾兄谢晖教授所主持之“法理文库”中读到其大著《法权与宪政》,尽管觉得其知识学理资源稍感老旧(如运用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来安排法权理论),但其立论扎实,特别是对风靡一时的权利本位论有重大的突破之处,心甚仪之,可惜一直无缘成文以示敬意,甚至今年二月在颠簸的云南西双版纳崎岖山路上海脑里猛然涌现出写写童之伟教授的想法,还连忙将脑海里涌出的一些想法在笔记本上写出一个大概,但回南宁后竟没有再理会。今日得缘,拜读童之伟先生针对“巩献田教授事件”的长文,越发对这位珞珈学长(因本人也在珞珈混过几天故可如此称呼)油然而起敬意,特别是联想到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珞珈许多学人在中国学界失尽颜面的情况下尤其难得,使我生“吾珞珈毕竟有人”的感慨。童之伟教授在《法权与宪政》中深刻指出:“无真知则易盲从”。(童之伟:《法权与宪政》,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页74.)如果用这句话来检验中国宪法学家在“巩献田事件”中的表演,那真是太合适不过的了,或者说,中国宪法学家的表演,正好不幸成了童教授此语的注脚。这也从反面提示我们,中国宪法学的根本出路在于获得宪法学的“真知”。没有对于宪法学的真知,自然就会昨日盲从于政治(学)家的逻辑,今日盲从于民法学家的逻辑,明日盲从于刑法学家的逻辑,总之是看不到在全球化结构之中的当代中国的内在秩序结构,更谈不上完成自己的学术使命了。
三纵观童之伟教授这篇共分为八节并长达近三万字的宏文,照我看,它有三个特点,一是理性冷静的态度,一是客观深入的分析,一是学术自主的追求。如果概括得当,那么我认为童之伟教授实际上为中国宪法学家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循此路径,中国宪法学家庶几可以不辱自己时代之使命。
巩献田先生“公开信”出,物权法草案起草人/民法学者在愤怒中举止失措,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教授等人指责巩先生不懂物权法,不懂就不要说,等学懂了再来评论物权法之类的话,在我看,完全丧失了一个学者最基本的立场。关于这个方面的解读我已在《“巩献田事件”的本质是当代中国法制/法学的危机》(http://weidunyou.fyfz.cn.)一文中作出,兹不具论。总之我想表明的是,在当代中国一个宪政的结构之下,中国人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就国是进行理性的辩论从而达成共识的,但是我们的民法学家竟似乎忘记了这一点,更可悲的是,我们的宪法学家似乎也忘记了这一点,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韩大元教授等人以宪法学家名义无原则的捧场,完全丧失了理性的立场。童之伟教授的这篇宏文首先表明的就是这样一个理性冷静的态度,照理说,本来这样一个理性冷静的态度是对于学者来讲是一般的要求,不幸它在当代中国竟成了一个高的要求,就象我们的中央台经常表扬那些为老百姓作出了一些贡献的官员令人不免感到有些荒唐一样,因为对老百姓作出贡献这是一个官员最起码的要求,不过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完全用不着表扬的,因为在这种表扬里面,从理论上看,它实际上预设着这样一个立场,仿佛不作贡献不履行自己的职责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不是太荒唐了吗?!然而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所以童教授的这种立场就自然显得十分可贵了。童先生的理性冷静的立场在我看来贯穿在整个文本中,但突出地体现在第一、二两节。第一节的标题就是“理性看待《草案》违宪与合宪之争,。童先生在这一节指出:“法律是什么?它形式上是分配法权即法定之权的规则,实际上是分配利益的规则,归根结底是分配财产的规则。物权法是国家基本的法律,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财产关系,因而它的制定和修改,直接关系到社会广泛的财产利益、财产权利的归属及其运用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真正应该是广大公民的事情,法学家、民法学家所能作的,只能是从技术上、形式上把依据宪法形成的、大多数公民所能接受的分配规则记录好,而不应是试图决定其实质内容。《草案》修改和完善过程中出现了尖锐的意见对立,表明该草案起草过程背后有不同社会阶层在进行激烈的法权博弈,法学家只不过是他们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代言人。”(童之伟:《〈物权法(草案)〉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评一封公开信引起的违宪与合宪之争》,http,//dzl.legaltheory.com.cn/info.asp?id=11248.下引此文不再注明。)
童先生的这种立场恢复了法律的政治本质,打破了那种以为法律可以游历于政治之外的“法律中立的神话”,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对当下世界结构中为人们视而不见的极其隐蔽的推行某种社会秩序或政治秩序的过程或机制进行揭示和批判”。(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页 23.)这样看来,我们的民法学/特权法学家试图阻止人们的批判看来是不现实的。童先生说得好:“对同一个学术问题,有不同意见才正常,没有不同意见是反常的。众口一词,千夫指向一个人或一种观点,那不太像学术研讨。学术研究不必搞意见一致、舆论一律。学者们不妨冷静地想一想,既然大家观点完全一致,还开研讨会做什么呢?”这就是理性冷静的态度。正是基于这种理性冷静的立场,童先生在第二节对巩先生的公开信作出了深入的理性分析,指出了巩先生的两个缺失。第一个缺失是“没搞清已经由宪法序言肯定了的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马列书本中的和过去脱离我国实际追求的虚幻的、以‘一大二公’”、‘大锅饭’等做法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第二个缺失是”忽视了中国已基本进入了市场经济社会、宪法肯定了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事实。两种基本经济制度不同的社会都搞市场经济,当然会有一些相同的规律性的东西要遵循,其中一个重要的规律性的东西就是平等“。
除此之外,童先生还指出了巩先生其他一些方面的错误认识,比如认为巩先生的公开信“关于公有物权比私有物权更根本的判断颠倒了社会生活的真实关系”,“公开信批评在现实生活中公共财产疏于保护,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等情况,但这种现象不会是平等保护造成的,恰恰相反,这些确实存在的现象倒是实践中没有真正做到平等保护的结果”。在这种理性分析的基础上,童先生得出的结论是:“看不出《草案》有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问题。”(第二节的标题)
四但是在我看来,童先生这篇宏文最精彩之处是后面六节。我将第三、四、五这三节看成是一个单元,将第六、七、八这三节看成另一个单元。我将前一个单元视之为客观深入分析的典范,后一个单元视之为学术自主追求的典范。
“巩献田事件”的要害是物权法草案是否违宪之争,而是否违宪的要害则是物权是平等保护还是区别保护。认为物权法草案没有违宪的学者其理由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很显然,这种论证方法是回避问题而不是面对问题。真正面对问题的态度是要从宪法本身找依据,而不是在宪法之外来找,因为确定是否违宪只能从宪法的文本方面去找根据而不是相反。因此这样一来,物权法起草者们/物权法学者们/宪法学者们就违背了最基本的学术规范。那么从宪法找依据如何呢?童先生对我国现行宪法进行深入的客观分析,特别是对宪法第6条、第7条、第12条、第13条进行分析后,指出:“我们就可发现有关条款在语言上很直观地显示了几点区别:1.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受保护但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试想,2004年修宪,有那么多人主张修正案的条款写成‘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修宪机关为什么坚持不写上‘神圣’二字?有那么多人主张既然私有财产前不冠以神圣的顶戴,那就把公共财产的神圣顶戴拿下来,结果拿下来了没有?为什么没拿?如果不是文义上有原则差别人们为什么要求比照公共财产在私有财产前加上‘神圣’字眼?如果没有原则差别修宪机关为什么不按‘要神圣都神圣,要不神圣都不神圣’的主张修改宪法有关条文?2.公有财产前有‘社会主义’的定语,这表明宪法将这种财产的地位和命运与社会主义的地位和命运联系了起来,而且没有‘依法’二字,表明对它的保护是无条件的;私有财产没有这种宪法地位和现实地位,自然也没有享受这种宪法待遇。此外,私有财产还在逻辑上被区分为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表明保护是有条件的。3.国家得‘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对国有财产的保值增值承担有特别的义务,对其他主体财产没有这种义务。《草案》贯彻平等保护原则在文义和逻辑上都与宪法有关条款冲突,这点再明显不过了,只要有中学生语文水平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能看清。”童先生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在宪法眼中财产权从而物权是区别保护不是平等保护”。(第三节标题)
童先生在第四节进一步分析了“《草案》忽视了确立平等保护原则的宪法依据,。(第四节的标题)“对于包括物权在内的不同主体的财产权,《草案》从专家草拟建议稿时开始,就是主张对不同主体的物权平等保护的,基本上没有注意甚至是有意回避了宪法的要求。”比如童先生指出:梁慧星教授领导的物权法研究课题组1995年提出基本思路、1999年完成定稿的草案建议稿第4条就是把各种物权权利主体平等看待的,并且在说明理由时没有提到宪法有关条款。梁教授在说明理由时讲得很清楚:“本条对于一切民事主体的物权权利给予平等保护,作为基本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在财产法的领域里彻底否定旧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并真正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财产法的基本规则”,“以前的物权权利制度建立了国家物权权利优先的原则,基于这一原则,过去的物权权利制度对其他主体的物权权利作了相当大的限制,甚至是歧视性的规定;因此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精神,对中国物权权利制度进行更新,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产关系的自身规律,建立完全适应形势发展需求的新的物权权利制度。”梁教授很清楚,平等保护很难找到直接的宪法依据,甚至是违反宪法有关条款和精神的,所以他为平等保护找的依据不是宪法,而是“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市场经济的财产关系的自身规律”。当然,市场经济也是宪法肯定了的,但他仅从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它所包含的“规律”中找根据,所找到的根据只能是间接地推导出来的、很难确证的东西,不会是直接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梁教授所要“彻底否定”的“旧的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内容,实际上就存在于他说这个话时正在实施的宪法中!又比如童先生指出:学者们非常清楚,社会上和法学界都有不少人依据宪法的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条款坚持社会主义国家传统上都认同的公有财产特别保护论,为了打消这方面的疑问,王利明教授对此论给予了批驳。他说,“此种观点认为,宪法规定,‘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意味着对公有财产实行特殊保护……所以物权法应当对公有财产实行特殊保护。我认为这完全是对宪法的误解。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都已经明确规定了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但宪法也规定了合法的个人财产受法律保护。”在援引了宪法第11条的规定后,王教授说,“强调保护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是并举的,绝对不能割裂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而对宪法的规定断章取义……实行平等保护是完全符合宪法的。”童先生认为,王教授在这里只是提出了一个论点、论断,没有证据,也没有论证,特殊保护论者不可能心服。
在指出物权法学者回避宪法的事实情况之下,童先生力求回到宪法文本进行探讨问题,他指出“任何一项打破传统新确立的法律所贯彻的原则是合宪还是违宪,总难免有争议。通常,利害关系人往往会尽可能按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做解释,其他人的理解和解释也往往难免受自己价值观的影响。不过,二百多年来,一些实行成文宪法制度的法治国家的违宪审查机关还是形成了一些被普遍认可的解释宪法的方法或套路。我们可以参照这些方法和套路来对《草案》贯彻平等保护原则是否合宪做些评论。”童先生细致地考察了七种宪法解释的方法,认为无论哪一种解释都不可能得出国家财产与私有财产在物权上享有平等保护的地位,因此,“《草案》贯彻平等保护原则确有违宪嫌疑”。(第五节标题)并指出“《草案》要清清白白地走出宪法之门,必须启动适当的宪法程序为其‘摆渡’或让其‘过桥’。”我认为,到此为止,童之伟教授完全证成了“目前的这个物权法草案是违宪的”这个命题。令我感叹万分的是,巩先生利用政治的武器证明的东西,在童先生这里在宪法学理上得到了精细的证明。
五在我看来,童之伟教授这篇宏文,如果说前述理性冷静的态度是其立论的基础,客观深入的分析是其立论的方法,那么,学术自主性追求则是其立论的目标。
童先生在宪法学上的学术自主性追求体现在第六、七、八三节之中。童先生呼吁,“要修改好《草案》须先修正民法与宪法关系的认识偏颇”。(第六节标题)童先生痛切地指出:“在我国,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等原因,违宪的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文件从来没有遭遇过违宪宣告,所以各个部门法学者以及法官对宪法并不特别重视,对宪法学通常也少有认真研读者。我亲见不少很有成就的部门法学者和级别很高的法官对作为民事权利的人身权、财产权与作为宪法权利的人身权、财产权的联系与区别之类的宪法学领域的问题不清楚。当然,这首先是宪法学的失败,因为历来的宪法学教材也几乎都没讲清这些知识,甚至大多完全没提到这类原理性问题。讨论《草案》是否违宪的过程表明,不少比这些知识复杂得多的重大学理问题在学者之间缺乏基本共识。学术研究水准直接影响立法水准。要修改好《草案》,需要参与其事的各方人士实事求是地理解物权法与宪法的关系,在一些较重要的认识问题上取得基本共识。”童先生严厉批评了人们囿于公法与私法二分的偏见,认为宪法是公法,只管公权力,宪法没有必要管私法的事,物权法是私法,那么宪法你不要管。童先生深刻指出,正是在这种对宪法的误识之下,“有关学者表达的宪法观与《草案》处理与宪法关系的做法是贯彻着相同指导思想的,那就是要让民法与宪法这部‘公法’尽可能区隔开,最好一点关系也没有。这种将宪法看作公法,试图将民法与宪法分开的做法,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际上是行不通或有害的。但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在起草《草案》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起草者采取了明显违反常规的做法:第一,该草案不像其他基本法律那样写上‘公法依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该草案也不像其他法律通常所做的那样,将相关方面的宪法条文或其中关键规则、原则(如宪法第12条和第13条)写进草案,这显然是起草者表示不认同它们是物权法应遵循的原则的结果。”其实,在童先生看来,这种观念严重地阻碍了人们对宪法的认识,宪法不是公法,而是根本法,它是一切法律的最终根据,宪法是一国的根本法,如果一定要区别公法与私法,那么宪法就是既包括公法规范(包括原则、规则和概念)又包括私法规范的根本法,在分类上“根本法”应该是一个与公法、私法并列的单独的类别。
除了这样一个将宪法视为根本法而超出公法与私法之上的基本共识之外,童先生还认为我们要修改好《草案》,民法学者与宪法和其他部门法学者还应该达成这样一些共识:第一,我们不能用目的的正当性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不一定合宪,两者不可以混为一谈;而且,宪法确认的原则、规则很多,立法不能违反其中任何一条。第二,民法是具体宪法架构下的具体的民法。第三,实现物权平等保护的价值追求与进行合宪性操作应该统一起来。第四,处理好公民和国家间关系的关键是在总体上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也即实现所谓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平衡,不可盲目偏于一端。第五,不应以任何借口模糊违宪合宪界线或回避违宪合宪判断。
在达成上述共识的前提下,童之伟教授认为,我们就可以真正建立起一个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法律体系,检验这个法律体系是否真正是一个符合宪法的法律体系的标准是“宪法有关条文间存在抵牾,最好正式释宪。”(第七节标题)然而在近三十年的中国法制进程之中,人们将宪法束之高阁,将生活中对于宪法的违背熟视无睹,戏称为“良性违宪”,如郝铁川等人竟对“良性违宪”现象给予肯定的评价,试图从学理上证成之,(童之伟:《法权与宪政》,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页598.)这种违背宪法的情况在今天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宪法墨守成规,死板教条,人们既可能通过重新制宪来完成厘定新生活秩序的诉求,也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来适应现实生活,比如今天中国的现实已远远不是三十年前所可比拟的了,巩先生的错误则是还生活在三十年前的中国,面对这样一个新的生活现实,我们也不能无视宪法的权威,在没有制宪的前提之下,应充分运用宪法解释的手段完成在宪法框架之下生活秩序,比如童先生指出:“宪法解释应基于新论据宣示平等保护是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第八节标题)“那种认为民法应对国有财产实行特殊保护、认为《草案》应按这种精神对不同主体的物权实行区别保护的主张,虽有宪法关于不同主体的财产地位不同的有关条款做依据,但却有悖于宪法关于实行市场经济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国不顾市场经济的规律,将区别保护原则贯彻到物权法中,几乎可以肯定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按必要和演进解释的进路对宪法做与时俱进的解释,排除掉物权进而财产权按不同身份区别保护这个选项,是非常必要的。”“对不同主体的财产实行平等保护,是我国现阶段走富民强国的市场经济道路之所必不可少的法律选择,宪法解释应当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解释宪法的有关条款,将对不同主体的财产实行平等保护宣示为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让它不仅适用于民事法,也适用于包括刑事法、行政法在内的所有法律部门。宪法解释事实上会具有低于宪法但高于所有其他法律的效力,这是不可避免的。”“宪法解释应当事实求是地说明如下关键理由:法律对不同主体的财产实行平等保护是以国家、集体在财产占有方面事实上占据了优越的宪法地位为前提的,是以国家、集体事实上占有或垄断了社会的全部财产中的基础性部分为前提的;这种平等是全局不平等格局下的局部平等,是宪法上不平等前提下的法律上的平等,是实质不平等条件下的形式平等。真实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宪法解释还可以说明,只要处置得当,对不同主体的财产实行平等保护不仅不会动摇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还会改善和加强这种地位。” 这样一来,则可以达成双赢的结果,而最关键的是,宪法的权威得到了捍卫。而捍卫宪法的权威是宪法家的天职,宪法学家在根本上说就是宪法的守护神。
我本非法学出身,没有师传,偶入法池,随意浏览,而属意法理与宪政。在研习宪法的这五六年时间里,我认为在当今中国,童之伟教授是中国宪法的真正卫士,是中国宪法学的真正守护人。《法权与宪政》是童教授最重要的著作,他对法权理论的建构,他对权利本位说的有力批判,尤其是对曾经在中国盛极一时的,良性违宪”理论的激烈批判,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次我通过研读童教授的又一篇宏文,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印象。杜钢建、范忠信两位学者非常深刻地指出:“宪法学应是现行政治的分析化验师和医师,不应是现行政治的涂脂抹粉者。客观理性的宪法学说、中立的研究立场,是中国民主政治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杜钢建 范忠信:《基本权利理论与学术批判态度》,载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页16.)据此判断,我认为,以许崇德、周叶中、韩大元等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宪法学总的来说其知识系谱源自于西方17、18世纪的自然法学,再加上当下政治正确的陈词滥调,因此处在西方知识权力与当今政治权力的双重掌控之下,在根本上“属于现行政治的涂脂抹粉者”,而童之伟教授所开启的法权宪法学由于将权力置于宪法的关注之下并对权力的入微的分析则庶几可以看成是属于“现行政治的分析化验师和医师”。童之伟教授好象不是中国主流法学家,那么,童之伟教授的宪法学思想应该属于未来中国的。
六吾国不幸,近百年的宪政转折至今依然付之阙如。因读范忠信教授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于梁启超先生文大好之。遂购得《饮冰室合集》十二巨册,昼夜攻读,大有崭获。范忠信教授说:“在宪法学方面,梁启超更是宪法学在中国的开山鼻祖,有无可争辩的创始人地位。”(范忠信:《认识法学家梁启超》,载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页10.)又说,“在作钦犯、斗志、政治家的颠沛奔波的坎坷生涯中把自己培养成法学学术权威人物,近代史上除梁先生以外更无第二人。”(范忠信:《认识法学家梁启超》,载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页13.)证以我读之《饮冰室合集》,信然矣。有李泽厚者,一面说,梁启超“是应该大书特书的肯定人物”,但另一面又说梁启超“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宣传家”。(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页385.)证以我读之《饮冰室合集》,不然矣。窃以为李氏读梁氏文必不过什一。梁氏之文,理性清明,文彩灿烂,而于宪政、共和、专制、民主诸词之辩入微,远远过于当今诸子之论。当今诸子,混淆宪政与民主,忘却共和与专制,胡言人权与法治,其病久矣。德人研究哲学,常有回到康德之说,而私心以为,当今中国宪政之研究,倡回到梁启超如何?诸君不回,吾将独回矣。梁启超先生高过当今宪法学人岂止万倍。
吾好历史,而历史予我喜,也予我忧也。由梁启超先生文,寻百年宪政中国史,禁不住而发百年之忧。所忧者何?
一百年前,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这帮头脑冬烘的僵老官僚在欧美日本游逛了九个月后,返回国门时竟连宪政的名词都讲不清楚。“公款旅游”了九个月,仍向皇上交不了差,怎么办?情急之中,他们只得暗中托人转请被朝廷明令通缉的“宪政专家”梁启超帮忙。梁启超凭自己丰厚的学养,代五大臣起草了一份《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的长篇报告,五大臣以自己的名义上奏朝廷。(范忠信:《认识法学家梁启超》,载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页6-7.)我将五大臣偷运梁启超的宪政思想为“五大臣事件”。
一百年后,2005年,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最新一轮“十大中青年法学家”称号获得者周叶中教授与其弟子戴激涛女士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正在兴高采烈之时,不幸被曾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师而专志共和理论的王天成先生指为剽窃,责为“博盗”(王天成:《究竟是博导,还是“博盗”?——评武汉大学教授周叶中等的剽窃问题》,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7157&type=1001)。举国舆论一时哗然。周先生坚不承认,认为自己严守学术规范,之所以不加注/删注是因为王天成的政治背景,实指王天成有“政治问题”。针对周叶中教授的此种辩解,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奋而撰文,严斥其非,并将此一事件命名为“周叶中教授事件”。(贺卫方:《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7341&type=1000)。一个堂堂的“宪法学家”,一个经常以“帝师”炫耀人前的人,就算你所说是真,但你竟要靠偷运有政冶问题的王天成的共和思想来立论,岂非大谬!与前述五大臣偷运当时有政治问题的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比较起来,不知诸位学子作何感想?吾不忍心视之矣,吾不忍心视之矣。吾以为“五大臣事件”、“周叶中教授事件”为过去之百年吾中华宪政史之奇耻大辱也!为吾国宪法学家之奇耻大辱也!斯耻斯辱之甚,无有过之。建议每一位中国宪政学人每日念此两“事件”,如此则吾国宪政或有生机矣,吾国宪法学或有生机矣,吾国宪法学家再百年后或可免斯耻免斯辱矣。
宪政中国何处去?中国宪法何处去?中国宪法学家何处去?
吾文将尽,时近午夜,明月在天,南国寂寥。“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李白)心念吾中华的法制/法学或正处在一个临界点上,在这样一个临界点上,它特别要求中国的宪法学家做到这样一点,也就是要象童之伟教授那样:认真对待宪法,做宪法的守护神;认真对待宪法学,追求宪法学独立于西方知识权力与当今政治权力的学术自主性。
这也许就是中国宪法学的去向?
今日国人谈及中国前途者,什有九心灰意尽,曰,噫,国其殆亡!国其殆亡!吾则以为我国人苟不自亡,他人决无能亡我者。 ——梁启超(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八册,专题之三十二,页二0,北京,中华书局,1989/2003.)
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田汉悼聂耳诗
(见拙文:《初入古滇国杂记》,http://weidunyou.fyfz.cn/blog/weidunyou/index.aspx?blogid=42912.)
宪法学应是现行政治的分析化验师和医师,不应是现行政治的涂脂抹粉者。客观理性的宪法学说、中立的研究立场,是中国民主政治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 ——杜钢建 范忠信(杜钢建 范忠信:《基本权利理论与学术批判态度》,载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页16。)
一我想再一次强调2005年对于当代中国法学/法制的里程碑式的意义,我甚至于认为2005年是这样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它是中国百年“知识引进运动的终结”,是中国人开始自己思考问题从而自已构建自己的生活秩序的开端。(参拙文:《音调未谐的变奏》、《“知识引进运动”的终结》等。http,//weidunyou.fyfz.cn.)
上述命题当然是有待证实的。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命题实出于我对2005年发生在中国法学界的诸多“事件”的感受。对上述命题而言,其中两个事件是值得反复提到的。一个是“邓正来事件”,一个是“巩献田事件”。是年伊始,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邓正来先生就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政法论坛》(2005年第1至4期)连续发表长篇论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正来教授深刻指出中国法学没有自己的理想图景,长期受到“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的宰制,并认为中国法学处在深刻的危机中,中国法学欲走出这个危机,必须结束受西方法律理想图景支配的法学旧时代,从而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章景”的法学新时代。同年8月12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巩献田教授发表质疑《物权法(草案)》的公开信,从多方面对物权法草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批评该草案违宪,从而在全国引起喧然大波,《物权法(草案)》因此没有象许多人所预期的那样进入2006年3月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我将邓正来教授的行为命名为“邓正来教授事件”,将巩献田教授的行为命名为“巩献田教授事件”。
我认为,中国法学/法制要想获得进展,必须将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解读这两个“事件”的内在意义。如果说邓正来教授从法学的层面预见了中国法学/法制的深刻危机,那么可以恰当地说,巩献田教授则在法制实践的层面使这个危机找到了自己全面爆发的突破口。对中国法制/法学的危机需要从历史与哲学的双重角度进行认真地清理,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知性工作。我注意到,巩献田先生公开信发表后,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反应,比较引人注目的,大概是2006年2月25日下午许多民法学家,还有宪法学家,聚集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法学院以研讨“物权法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的名义,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关于“《物权法》草案违宪、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公开信进行全面回应。(见http://legal.people.com.cn/GB/42731/4148610.html.)。十分蹊跷的是,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带给人的印象好象是“众口一词”,然而聪明的中国人心里明白,这要么是预谋,要么是有选择地报道,总之是太不可信了,正象华东政法学院童之伟教授针对此次会议的报道所敏锐指出的那样,“如果有人发表点不同看法,会议的共识可能会更可信些。”(童之伟:《〈物权法(草案)〉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评一封公开信引起的违宪与合宪之争》,注[5],见http://dzl.legaltheory.com.cn/info.asp?id=11248.)在我也感到迷惑不解的时候,我突然在“正来学堂”里面读到了此次会议参加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景文教授的文章《由〈物权法草案〉的争论所想到的》(在“物权法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见http://dzl.legaltheory.com.cn/info.asp?id=11190.),朱景文教授就在这篇文章中谈到了许多与物权法学者的“不同看法”,可惜的是,关于此次会议的报道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印痕!看来,中国学者们玩起政治来,一点也不比政治家们逊色!如果是这样,那么我要求中国人,请记住这一天,2006年2月25日,因为我认为这一天将成为中国法学的“耻辱日”!因为这一天将使中国人对中国法学家们是否具有“知性的诚实”发生深深的怀疑!因此这一天它也应该成为中国法学家们集体的“忏悔日”!不正视这种耻辱,不进行深刻的忏悔,不回归知性的诚实,中国法学没有希望,中国法制没有希望。而更重要的,是我从2006年2月25日这一天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以江平、王利明、杨立新等人为代表的中国民法学以及以许崇德、周叶中、韩大元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宪法学因为自我虚脱而无力面对当今中国现实,基本上已经走到了自己的逻辑终点。虽然它们还将在中国法学场域中存在一段时间甚至于相当长一段时间(必须有新的理论出来才能完全代替它们),但是它们从总体上讲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为了新的法学时代的来临,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清理中国法学/法制的知识系谱及其与政治权力的相互关系。本小文显然不可能完成这一重大任务,也不是为了这一重大任务而来,因为确切地说,本小文的写作机缘只是因为读到了华东政法学院童之伟教授的针对“巩献田教授事件”的大作《〈物权法(草案)〉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评一封公开信引起的违宪与合宪之争》(见http://dzl.legaltheory.com.cn/info.asp?id= 11248.),感到中国宪法学界并不乏深思明辩之士,一时高兴,竟不揣浅陋而作此文向童教授致意,并借此机会清理一下对当代中国宪法学的一些零星看法,而象中国民法学的知识系谱则应该由专门的民法学之才学之士去认真清理的。
二在此次“巩献田教授事件”中,中国宪法学家们的表演令人吃惊。在巩先生质疑《物权法草案》违宪之后,中国“著名的”宪法学家们不去研究到底什么叫违宪、如何检验违宪以及进一步去深入探讨中国宪法学的当代使命,却匆匆忙忙加入到民法学/物权法学者所主导的“《物权法草案》并不违宪”的大合唱中,失去了一个宪法学家对事物的甄别力,从而客观上成了民法学/物权法学者的“侍者”,完全丧失了中国宪法学家的尊严。中国宪法学家在“巩献田教授事件”中的这种表演,在我看来,并不是偶然的,它充分说明中国宪法学已经陷入困境,因此只能在现实的波澜中随波逐流。北京大学法学院徐爱国教授批评中国法理学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自己,因为“国家设定了法学和法理学家,不是让他们做法律具体的政治性的工作,而是需要他们拿出有理论价值的成果,这应该是一个学者的责任”。(徐爱国:《困境与出路:对中国法理学的遐想》,http://dzl.legaltheory.com.cn/info.asp?id= 11098.)我曾经在一篇小文章《中国法理学向何处去》中认可了爱国教授的这一观点(http://weidunyou.fyfz.cn.)。现在我想说的是,在我看来,爱国教授对中国法理学家的这种严厉批评同样适用于中国宪法学家,甚至于更适合于中国宪法学家。
然而,在我对中国宪法学家在“巩献田教授事件”中的表演深感失望的情况之下,我终于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宪法学家出场了,他就是上海华东政法学院的童之伟教授。这位曾经的珞珈(武汉大学)学子,辗转武汉来到上海,从上海交通大学而华东政法学院,著述虽然不多,却巍然屹立而有智者之思,五年前(2001)因从吾兄谢晖教授所主持之“法理文库”中读到其大著《法权与宪政》,尽管觉得其知识学理资源稍感老旧(如运用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来安排法权理论),但其立论扎实,特别是对风靡一时的权利本位论有重大的突破之处,心甚仪之,可惜一直无缘成文以示敬意,甚至今年二月在颠簸的云南西双版纳崎岖山路上海脑里猛然涌现出写写童之伟教授的想法,还连忙将脑海里涌出的一些想法在笔记本上写出一个大概,但回南宁后竟没有再理会。今日得缘,拜读童之伟先生针对“巩献田教授事件”的长文,越发对这位珞珈学长(因本人也在珞珈混过几天故可如此称呼)油然而起敬意,特别是联想到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珞珈许多学人在中国学界失尽颜面的情况下尤其难得,使我生“吾珞珈毕竟有人”的感慨。童之伟教授在《法权与宪政》中深刻指出:“无真知则易盲从”。(童之伟:《法权与宪政》,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页74.)如果用这句话来检验中国宪法学家在“巩献田事件”中的表演,那真是太合适不过的了,或者说,中国宪法学家的表演,正好不幸成了童教授此语的注脚。这也从反面提示我们,中国宪法学的根本出路在于获得宪法学的“真知”。没有对于宪法学的真知,自然就会昨日盲从于政治(学)家的逻辑,今日盲从于民法学家的逻辑,明日盲从于刑法学家的逻辑,总之是看不到在全球化结构之中的当代中国的内在秩序结构,更谈不上完成自己的学术使命了。
三纵观童之伟教授这篇共分为八节并长达近三万字的宏文,照我看,它有三个特点,一是理性冷静的态度,一是客观深入的分析,一是学术自主的追求。如果概括得当,那么我认为童之伟教授实际上为中国宪法学家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循此路径,中国宪法学家庶几可以不辱自己时代之使命。
巩献田先生“公开信”出,物权法草案起草人/民法学者在愤怒中举止失措,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教授等人指责巩先生不懂物权法,不懂就不要说,等学懂了再来评论物权法之类的话,在我看,完全丧失了一个学者最基本的立场。关于这个方面的解读我已在《“巩献田事件”的本质是当代中国法制/法学的危机》(http://weidunyou.fyfz.cn.)一文中作出,兹不具论。总之我想表明的是,在当代中国一个宪政的结构之下,中国人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就国是进行理性的辩论从而达成共识的,但是我们的民法学家竟似乎忘记了这一点,更可悲的是,我们的宪法学家似乎也忘记了这一点,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韩大元教授等人以宪法学家名义无原则的捧场,完全丧失了理性的立场。童之伟教授的这篇宏文首先表明的就是这样一个理性冷静的态度,照理说,本来这样一个理性冷静的态度是对于学者来讲是一般的要求,不幸它在当代中国竟成了一个高的要求,就象我们的中央台经常表扬那些为老百姓作出了一些贡献的官员令人不免感到有些荒唐一样,因为对老百姓作出贡献这是一个官员最起码的要求,不过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完全用不着表扬的,因为在这种表扬里面,从理论上看,它实际上预设着这样一个立场,仿佛不作贡献不履行自己的职责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不是太荒唐了吗?!然而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所以童教授的这种立场就自然显得十分可贵了。童先生的理性冷静的立场在我看来贯穿在整个文本中,但突出地体现在第一、二两节。第一节的标题就是“理性看待《草案》违宪与合宪之争,。童先生在这一节指出:“法律是什么?它形式上是分配法权即法定之权的规则,实际上是分配利益的规则,归根结底是分配财产的规则。物权法是国家基本的法律,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财产关系,因而它的制定和修改,直接关系到社会广泛的财产利益、财产权利的归属及其运用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真正应该是广大公民的事情,法学家、民法学家所能作的,只能是从技术上、形式上把依据宪法形成的、大多数公民所能接受的分配规则记录好,而不应是试图决定其实质内容。《草案》修改和完善过程中出现了尖锐的意见对立,表明该草案起草过程背后有不同社会阶层在进行激烈的法权博弈,法学家只不过是他们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代言人。”(童之伟:《〈物权法(草案)〉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评一封公开信引起的违宪与合宪之争》,http,//dzl.legaltheory.com.cn/info.asp?id=11248.下引此文不再注明。)
童先生的这种立场恢复了法律的政治本质,打破了那种以为法律可以游历于政治之外的“法律中立的神话”,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对当下世界结构中为人们视而不见的极其隐蔽的推行某种社会秩序或政治秩序的过程或机制进行揭示和批判”。(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页 23.)这样看来,我们的民法学/特权法学家试图阻止人们的批判看来是不现实的。童先生说得好:“对同一个学术问题,有不同意见才正常,没有不同意见是反常的。众口一词,千夫指向一个人或一种观点,那不太像学术研讨。学术研究不必搞意见一致、舆论一律。学者们不妨冷静地想一想,既然大家观点完全一致,还开研讨会做什么呢?”这就是理性冷静的态度。正是基于这种理性冷静的立场,童先生在第二节对巩先生的公开信作出了深入的理性分析,指出了巩先生的两个缺失。第一个缺失是“没搞清已经由宪法序言肯定了的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马列书本中的和过去脱离我国实际追求的虚幻的、以‘一大二公’”、‘大锅饭’等做法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第二个缺失是”忽视了中国已基本进入了市场经济社会、宪法肯定了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事实。两种基本经济制度不同的社会都搞市场经济,当然会有一些相同的规律性的东西要遵循,其中一个重要的规律性的东西就是平等“。
除此之外,童先生还指出了巩先生其他一些方面的错误认识,比如认为巩先生的公开信“关于公有物权比私有物权更根本的判断颠倒了社会生活的真实关系”,“公开信批评在现实生活中公共财产疏于保护,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等情况,但这种现象不会是平等保护造成的,恰恰相反,这些确实存在的现象倒是实践中没有真正做到平等保护的结果”。在这种理性分析的基础上,童先生得出的结论是:“看不出《草案》有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问题。”(第二节的标题)
四但是在我看来,童先生这篇宏文最精彩之处是后面六节。我将第三、四、五这三节看成是一个单元,将第六、七、八这三节看成另一个单元。我将前一个单元视之为客观深入分析的典范,后一个单元视之为学术自主追求的典范。
“巩献田事件”的要害是物权法草案是否违宪之争,而是否违宪的要害则是物权是平等保护还是区别保护。认为物权法草案没有违宪的学者其理由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很显然,这种论证方法是回避问题而不是面对问题。真正面对问题的态度是要从宪法本身找依据,而不是在宪法之外来找,因为确定是否违宪只能从宪法的文本方面去找根据而不是相反。因此这样一来,物权法起草者们/物权法学者们/宪法学者们就违背了最基本的学术规范。那么从宪法找依据如何呢?童先生对我国现行宪法进行深入的客观分析,特别是对宪法第6条、第7条、第12条、第13条进行分析后,指出:“我们就可发现有关条款在语言上很直观地显示了几点区别:1.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受保护但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试想,2004年修宪,有那么多人主张修正案的条款写成‘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修宪机关为什么坚持不写上‘神圣’二字?有那么多人主张既然私有财产前不冠以神圣的顶戴,那就把公共财产的神圣顶戴拿下来,结果拿下来了没有?为什么没拿?如果不是文义上有原则差别人们为什么要求比照公共财产在私有财产前加上‘神圣’字眼?如果没有原则差别修宪机关为什么不按‘要神圣都神圣,要不神圣都不神圣’的主张修改宪法有关条文?2.公有财产前有‘社会主义’的定语,这表明宪法将这种财产的地位和命运与社会主义的地位和命运联系了起来,而且没有‘依法’二字,表明对它的保护是无条件的;私有财产没有这种宪法地位和现实地位,自然也没有享受这种宪法待遇。此外,私有财产还在逻辑上被区分为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表明保护是有条件的。3.国家得‘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对国有财产的保值增值承担有特别的义务,对其他主体财产没有这种义务。《草案》贯彻平等保护原则在文义和逻辑上都与宪法有关条款冲突,这点再明显不过了,只要有中学生语文水平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能看清。”童先生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在宪法眼中财产权从而物权是区别保护不是平等保护”。(第三节标题)
童先生在第四节进一步分析了“《草案》忽视了确立平等保护原则的宪法依据,。(第四节的标题)“对于包括物权在内的不同主体的财产权,《草案》从专家草拟建议稿时开始,就是主张对不同主体的物权平等保护的,基本上没有注意甚至是有意回避了宪法的要求。”比如童先生指出:梁慧星教授领导的物权法研究课题组1995年提出基本思路、1999年完成定稿的草案建议稿第4条就是把各种物权权利主体平等看待的,并且在说明理由时没有提到宪法有关条款。梁教授在说明理由时讲得很清楚:“本条对于一切民事主体的物权权利给予平等保护,作为基本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在财产法的领域里彻底否定旧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并真正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财产法的基本规则”,“以前的物权权利制度建立了国家物权权利优先的原则,基于这一原则,过去的物权权利制度对其他主体的物权权利作了相当大的限制,甚至是歧视性的规定;因此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精神,对中国物权权利制度进行更新,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产关系的自身规律,建立完全适应形势发展需求的新的物权权利制度。”梁教授很清楚,平等保护很难找到直接的宪法依据,甚至是违反宪法有关条款和精神的,所以他为平等保护找的依据不是宪法,而是“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市场经济的财产关系的自身规律”。当然,市场经济也是宪法肯定了的,但他仅从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它所包含的“规律”中找根据,所找到的根据只能是间接地推导出来的、很难确证的东西,不会是直接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梁教授所要“彻底否定”的“旧的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内容,实际上就存在于他说这个话时正在实施的宪法中!又比如童先生指出:学者们非常清楚,社会上和法学界都有不少人依据宪法的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条款坚持社会主义国家传统上都认同的公有财产特别保护论,为了打消这方面的疑问,王利明教授对此论给予了批驳。他说,“此种观点认为,宪法规定,‘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意味着对公有财产实行特殊保护……所以物权法应当对公有财产实行特殊保护。我认为这完全是对宪法的误解。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都已经明确规定了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但宪法也规定了合法的个人财产受法律保护。”在援引了宪法第11条的规定后,王教授说,“强调保护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是并举的,绝对不能割裂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而对宪法的规定断章取义……实行平等保护是完全符合宪法的。”童先生认为,王教授在这里只是提出了一个论点、论断,没有证据,也没有论证,特殊保护论者不可能心服。
在指出物权法学者回避宪法的事实情况之下,童先生力求回到宪法文本进行探讨问题,他指出“任何一项打破传统新确立的法律所贯彻的原则是合宪还是违宪,总难免有争议。通常,利害关系人往往会尽可能按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做解释,其他人的理解和解释也往往难免受自己价值观的影响。不过,二百多年来,一些实行成文宪法制度的法治国家的违宪审查机关还是形成了一些被普遍认可的解释宪法的方法或套路。我们可以参照这些方法和套路来对《草案》贯彻平等保护原则是否合宪做些评论。”童先生细致地考察了七种宪法解释的方法,认为无论哪一种解释都不可能得出国家财产与私有财产在物权上享有平等保护的地位,因此,“《草案》贯彻平等保护原则确有违宪嫌疑”。(第五节标题)并指出“《草案》要清清白白地走出宪法之门,必须启动适当的宪法程序为其‘摆渡’或让其‘过桥’。”我认为,到此为止,童之伟教授完全证成了“目前的这个物权法草案是违宪的”这个命题。令我感叹万分的是,巩先生利用政治的武器证明的东西,在童先生这里在宪法学理上得到了精细的证明。
五在我看来,童之伟教授这篇宏文,如果说前述理性冷静的态度是其立论的基础,客观深入的分析是其立论的方法,那么,学术自主性追求则是其立论的目标。
童先生在宪法学上的学术自主性追求体现在第六、七、八三节之中。童先生呼吁,“要修改好《草案》须先修正民法与宪法关系的认识偏颇”。(第六节标题)童先生痛切地指出:“在我国,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等原因,违宪的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文件从来没有遭遇过违宪宣告,所以各个部门法学者以及法官对宪法并不特别重视,对宪法学通常也少有认真研读者。我亲见不少很有成就的部门法学者和级别很高的法官对作为民事权利的人身权、财产权与作为宪法权利的人身权、财产权的联系与区别之类的宪法学领域的问题不清楚。当然,这首先是宪法学的失败,因为历来的宪法学教材也几乎都没讲清这些知识,甚至大多完全没提到这类原理性问题。讨论《草案》是否违宪的过程表明,不少比这些知识复杂得多的重大学理问题在学者之间缺乏基本共识。学术研究水准直接影响立法水准。要修改好《草案》,需要参与其事的各方人士实事求是地理解物权法与宪法的关系,在一些较重要的认识问题上取得基本共识。”童先生严厉批评了人们囿于公法与私法二分的偏见,认为宪法是公法,只管公权力,宪法没有必要管私法的事,物权法是私法,那么宪法你不要管。童先生深刻指出,正是在这种对宪法的误识之下,“有关学者表达的宪法观与《草案》处理与宪法关系的做法是贯彻着相同指导思想的,那就是要让民法与宪法这部‘公法’尽可能区隔开,最好一点关系也没有。这种将宪法看作公法,试图将民法与宪法分开的做法,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际上是行不通或有害的。但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在起草《草案》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起草者采取了明显违反常规的做法:第一,该草案不像其他基本法律那样写上‘公法依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该草案也不像其他法律通常所做的那样,将相关方面的宪法条文或其中关键规则、原则(如宪法第12条和第13条)写进草案,这显然是起草者表示不认同它们是物权法应遵循的原则的结果。”其实,在童先生看来,这种观念严重地阻碍了人们对宪法的认识,宪法不是公法,而是根本法,它是一切法律的最终根据,宪法是一国的根本法,如果一定要区别公法与私法,那么宪法就是既包括公法规范(包括原则、规则和概念)又包括私法规范的根本法,在分类上“根本法”应该是一个与公法、私法并列的单独的类别。
除了这样一个将宪法视为根本法而超出公法与私法之上的基本共识之外,童先生还认为我们要修改好《草案》,民法学者与宪法和其他部门法学者还应该达成这样一些共识:第一,我们不能用目的的正当性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不一定合宪,两者不可以混为一谈;而且,宪法确认的原则、规则很多,立法不能违反其中任何一条。第二,民法是具体宪法架构下的具体的民法。第三,实现物权平等保护的价值追求与进行合宪性操作应该统一起来。第四,处理好公民和国家间关系的关键是在总体上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也即实现所谓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平衡,不可盲目偏于一端。第五,不应以任何借口模糊违宪合宪界线或回避违宪合宪判断。
在达成上述共识的前提下,童之伟教授认为,我们就可以真正建立起一个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法律体系,检验这个法律体系是否真正是一个符合宪法的法律体系的标准是“宪法有关条文间存在抵牾,最好正式释宪。”(第七节标题)然而在近三十年的中国法制进程之中,人们将宪法束之高阁,将生活中对于宪法的违背熟视无睹,戏称为“良性违宪”,如郝铁川等人竟对“良性违宪”现象给予肯定的评价,试图从学理上证成之,(童之伟:《法权与宪政》,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页598.)这种违背宪法的情况在今天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宪法墨守成规,死板教条,人们既可能通过重新制宪来完成厘定新生活秩序的诉求,也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来适应现实生活,比如今天中国的现实已远远不是三十年前所可比拟的了,巩先生的错误则是还生活在三十年前的中国,面对这样一个新的生活现实,我们也不能无视宪法的权威,在没有制宪的前提之下,应充分运用宪法解释的手段完成在宪法框架之下生活秩序,比如童先生指出:“宪法解释应基于新论据宣示平等保护是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第八节标题)“那种认为民法应对国有财产实行特殊保护、认为《草案》应按这种精神对不同主体的物权实行区别保护的主张,虽有宪法关于不同主体的财产地位不同的有关条款做依据,但却有悖于宪法关于实行市场经济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国不顾市场经济的规律,将区别保护原则贯彻到物权法中,几乎可以肯定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按必要和演进解释的进路对宪法做与时俱进的解释,排除掉物权进而财产权按不同身份区别保护这个选项,是非常必要的。”“对不同主体的财产实行平等保护,是我国现阶段走富民强国的市场经济道路之所必不可少的法律选择,宪法解释应当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解释宪法的有关条款,将对不同主体的财产实行平等保护宣示为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让它不仅适用于民事法,也适用于包括刑事法、行政法在内的所有法律部门。宪法解释事实上会具有低于宪法但高于所有其他法律的效力,这是不可避免的。”“宪法解释应当事实求是地说明如下关键理由:法律对不同主体的财产实行平等保护是以国家、集体在财产占有方面事实上占据了优越的宪法地位为前提的,是以国家、集体事实上占有或垄断了社会的全部财产中的基础性部分为前提的;这种平等是全局不平等格局下的局部平等,是宪法上不平等前提下的法律上的平等,是实质不平等条件下的形式平等。真实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宪法解释还可以说明,只要处置得当,对不同主体的财产实行平等保护不仅不会动摇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还会改善和加强这种地位。” 这样一来,则可以达成双赢的结果,而最关键的是,宪法的权威得到了捍卫。而捍卫宪法的权威是宪法家的天职,宪法学家在根本上说就是宪法的守护神。
我本非法学出身,没有师传,偶入法池,随意浏览,而属意法理与宪政。在研习宪法的这五六年时间里,我认为在当今中国,童之伟教授是中国宪法的真正卫士,是中国宪法学的真正守护人。《法权与宪政》是童教授最重要的著作,他对法权理论的建构,他对权利本位说的有力批判,尤其是对曾经在中国盛极一时的,良性违宪”理论的激烈批判,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次我通过研读童教授的又一篇宏文,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印象。杜钢建、范忠信两位学者非常深刻地指出:“宪法学应是现行政治的分析化验师和医师,不应是现行政治的涂脂抹粉者。客观理性的宪法学说、中立的研究立场,是中国民主政治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杜钢建 范忠信:《基本权利理论与学术批判态度》,载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页16.)据此判断,我认为,以许崇德、周叶中、韩大元等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宪法学总的来说其知识系谱源自于西方17、18世纪的自然法学,再加上当下政治正确的陈词滥调,因此处在西方知识权力与当今政治权力的双重掌控之下,在根本上“属于现行政治的涂脂抹粉者”,而童之伟教授所开启的法权宪法学由于将权力置于宪法的关注之下并对权力的入微的分析则庶几可以看成是属于“现行政治的分析化验师和医师”。童之伟教授好象不是中国主流法学家,那么,童之伟教授的宪法学思想应该属于未来中国的。
六吾国不幸,近百年的宪政转折至今依然付之阙如。因读范忠信教授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于梁启超先生文大好之。遂购得《饮冰室合集》十二巨册,昼夜攻读,大有崭获。范忠信教授说:“在宪法学方面,梁启超更是宪法学在中国的开山鼻祖,有无可争辩的创始人地位。”(范忠信:《认识法学家梁启超》,载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页10.)又说,“在作钦犯、斗志、政治家的颠沛奔波的坎坷生涯中把自己培养成法学学术权威人物,近代史上除梁先生以外更无第二人。”(范忠信:《认识法学家梁启超》,载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页13.)证以我读之《饮冰室合集》,信然矣。有李泽厚者,一面说,梁启超“是应该大书特书的肯定人物”,但另一面又说梁启超“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宣传家”。(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页385.)证以我读之《饮冰室合集》,不然矣。窃以为李氏读梁氏文必不过什一。梁氏之文,理性清明,文彩灿烂,而于宪政、共和、专制、民主诸词之辩入微,远远过于当今诸子之论。当今诸子,混淆宪政与民主,忘却共和与专制,胡言人权与法治,其病久矣。德人研究哲学,常有回到康德之说,而私心以为,当今中国宪政之研究,倡回到梁启超如何?诸君不回,吾将独回矣。梁启超先生高过当今宪法学人岂止万倍。
吾好历史,而历史予我喜,也予我忧也。由梁启超先生文,寻百年宪政中国史,禁不住而发百年之忧。所忧者何?
一百年前,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这帮头脑冬烘的僵老官僚在欧美日本游逛了九个月后,返回国门时竟连宪政的名词都讲不清楚。“公款旅游”了九个月,仍向皇上交不了差,怎么办?情急之中,他们只得暗中托人转请被朝廷明令通缉的“宪政专家”梁启超帮忙。梁启超凭自己丰厚的学养,代五大臣起草了一份《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的长篇报告,五大臣以自己的名义上奏朝廷。(范忠信:《认识法学家梁启超》,载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页6-7.)我将五大臣偷运梁启超的宪政思想为“五大臣事件”。
一百年后,2005年,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最新一轮“十大中青年法学家”称号获得者周叶中教授与其弟子戴激涛女士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正在兴高采烈之时,不幸被曾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师而专志共和理论的王天成先生指为剽窃,责为“博盗”(王天成:《究竟是博导,还是“博盗”?——评武汉大学教授周叶中等的剽窃问题》,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7157&type=1001)。举国舆论一时哗然。周先生坚不承认,认为自己严守学术规范,之所以不加注/删注是因为王天成的政治背景,实指王天成有“政治问题”。针对周叶中教授的此种辩解,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奋而撰文,严斥其非,并将此一事件命名为“周叶中教授事件”。(贺卫方:《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7341&type=1000)。一个堂堂的“宪法学家”,一个经常以“帝师”炫耀人前的人,就算你所说是真,但你竟要靠偷运有政冶问题的王天成的共和思想来立论,岂非大谬!与前述五大臣偷运当时有政治问题的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比较起来,不知诸位学子作何感想?吾不忍心视之矣,吾不忍心视之矣。吾以为“五大臣事件”、“周叶中教授事件”为过去之百年吾中华宪政史之奇耻大辱也!为吾国宪法学家之奇耻大辱也!斯耻斯辱之甚,无有过之。建议每一位中国宪政学人每日念此两“事件”,如此则吾国宪政或有生机矣,吾国宪法学或有生机矣,吾国宪法学家再百年后或可免斯耻免斯辱矣。
宪政中国何处去?中国宪法何处去?中国宪法学家何处去?
吾文将尽,时近午夜,明月在天,南国寂寥。“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李白)心念吾中华的法制/法学或正处在一个临界点上,在这样一个临界点上,它特别要求中国的宪法学家做到这样一点,也就是要象童之伟教授那样:认真对待宪法,做宪法的守护神;认真对待宪法学,追求宪法学独立于西方知识权力与当今政治权力的学术自主性。
这也许就是中国宪法学的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