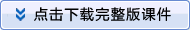输出与回归:法学名词在中日之间
王健
[原文分上、中、下三期分别刊于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24日、1月28日和2月4日的法治时代B2版上。]
主持人提示:考察西方法律语词传入中国的路径及方式,对于我们了解中西法律文化的性质和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诚如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所言:“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观察,一个民族对另一个异文化语词的翻译和接受的过程,可以视为一种文化的移入。”
王健教授的《输出与回归:法学名词在中日之间》一文,通过考察中、日之间法学语词互相借鉴的历史轨迹,澄清了法学界的一些理论误区,揭示出了中西方之间法律文化的一些异同,力图为中国法找到一条更适合自己的、既能超越传统又能摆脱西方个别经验的发展之路,意义可谓重大。今人常常以为,目前我们习见习用的一套法言法语大多于本世纪初期来自东瀛岛国的日本,然而事实并不如此简单,有的甚至相反。本文就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先从语言学界关于近代汉语语源问题上的讨论说起。
1950年代,随着文字改革和语言规范化运动的开展,关于现代汉语中的学术用语和外来语问题,特别是近代日语对汉语的影响等问题,曾引起过中国语言学家的一场热烈讨论;讨论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两种不尽相同的说法,或可说是对立的倾向。
其中一种颇有影响的看法断言,现代汉语中有许多借用日本的语词,这些词大都是明治维新以后,由于日本人翻译西文书籍陆续创造出来的。从历史上来说,它们不仅在我们国人的心目中被认为是“新名词”;就是在日本国内也同样被认为是近百年来产生的“新语”。这种观点以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刘正琰和王立达为代表。高、刘二人合著了《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在所列“汉语外来词所表现的外来事物及概念一览表”里面,作者指出其中属于外来法律类的总共39个语词全部来自日语,没有一个来自该表列出的其他9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包括俄语、德语、意大利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王立达则以新名词、新知识一类词典为例,指出其中所收的词汇“几乎有一半是借自日语的”。
已有学者对他们各自所列出的来自日本的现代汉语词汇作了综合,笔者仅检阅其中有关法律类的语词请另见表。
这些词在今天法律人的言说中占有怎样的地位不言自明,而令人惊讶的是,按照这个表,如此众多而又基本的法律词汇竟然全部都是源自日本的外来语!对此,当时就有人表示不能完全接受这种看法,因为它过分夸大了现代汉语中源于日本的外来语的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讨论似乎只是发生在语言学界的内部,对于从根本上直接涉及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在当时和以后似乎都没有产生什么多大的影响,至少就法学界而言,情形就是如此;因为除了学者偶尔涉及的个别法律语词外,法学界从来就没有对近现代法律用语问题做过专门认真地清理和检讨。可是尽管如此,一个时时可以感觉得到,但又都说不大准、模模糊糊的印象是,我们目前所使用的许多(注意这是一个模糊词)法律名词、术语是来自日本的。而有关于“权利”——这是一个在本文中常常被提起的例子——的近代语源的种种说法,正是反映上述问题的一个典型例证。
关于近现代汉语里的“权利”一词及其相关词语的来源,法学界以往大都认为它(们)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从日本流入到中文里的。明确提出这种说法的书证,至少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位优秀的民法学家梅仲协(1900年—1971年)的民法著作,作者在书中关于权利的专章里指出,
按现代法律学上所谓“权利”一语,系欧陆学者所创设,日本从而移译之。清季变法,“权利”二字,复自东瀛,输入中土,数十年来,习为口头禅。
此说在法学界长期相沿,至今仍频见于大陆、台湾和海外的一些法学论著。如郭道晖于1995年发表的《论法定权利与权利立法》一文中说,
中国法律上“权利”一词始见于清末之立宪和民国之立法。它是由日本传入。日文又是从德文Recht译为“权力利益”,略作“权利”。
同年台湾学者李复甸在其《权利辨正》一文里,依据日本平凡社《世界大百科字典》(1988年)第九卷“权利”词条中的解释,亦说,
……时下之权利出于东洋之译词,(原文此处有注)殆无争议。国人率而沿用,约定而俗成,如今已成为日常口语。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陈添辉在《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中国法制之变化——以民法之制定及施行为例》一文中,引用日本学者Z?Kitagawa的说法写到,
日本尚属中华法系时,亦无权利的观念。留学荷兰Leyden 大学的日本法学者Dr?M?Tsuda,回到日本后,于明治维新那一年,即1868年出版一本书,叫《西方公法学说理论》,因无相当用语来表达权利的观念,于是他在本书首先创造“权利”之用语。在日本社会,权利的观念,曾长期停留在白纸黑字的具文阶段,未为当事人主张。
由于笔者尚未查找到陈文所征引的原著,故无法知晓Z?Kitagawa何以如此持论的依据。不过,此论在日本并不独见。早在1904年N?Hozumi教授的一篇讲演中就有这样的主张,
日本从来没有权利的概念,直到Ken-ri(权利)一词出现,而Ken-ri一词的直接含义是power-interest(权力和利益)。该词的始作俑者是Tsuda博士,Tsuda博士曾在荷兰Leyden大学读书,1868年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论西方的公法》,在这篇文章里,他采用了Ken-ri(权利)一词。
显然,以上两段文字中,前者几乎是后者的翻版,他们都认为,日文之汉字“权利”,系由日本留学荷兰莱顿大学的法学博士津田真道(M?Tsuda)于1868年首先创行的一个用语。
除此之外,也有人指出,日语中的“权利”一词始见于1866年J?S?Mill著作的一个译本;提出这一事例类似情形的还有Pittau。
总之,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无论法学界抑或语言学界,也无论是大陆、台湾甚至日本,按照一种说法,“权利”是来自日本的一个汉语外来词。
然而与此论相左者一直大有人在。日本著名语言学家大木夫見文彦(1847年—1928年)在他所著《箕作麟祥君传》一书里,曾详细地描述了明治初年法学家箕作麟祥(1846年—1897年)为了翻译法国法律而苦心设造法律新名词的情形,其中就涉及到“权利”等词语的翻译问题。兹将这段文字抄录如下,
这是《法兰西法典》首次被引入日本,法理学也尚未发展。箕作麟祥对这些都并无所知;而且也没有带注释的书籍,没有词典,没有教师;克服这些理解上的困难对他是很沉重的负担。每次提到的概念在那时的日本还是完全不知道的,这成了大问题,因为不存在相对的译语。甚至当他请问汉学家时,没有一个人知道该怎样回答;如果他创造一个新词,倘若不是人们已知的汉字的组合,又可能不被接受。像“right”和“obligation”这样的词,他承袭了中国《万国公法》的翻译,译作“权利”和“义务”;至于像“movables”和“immovbles”这样的法律术语,他费尽心思地创造了像“动产”(d?san)和“不动产”(fud?san)这样的新词。
这段文字很可能是后来各种关于日本近代的“权利”等词来源于中国早期汉文译本说法的最早的依据。其中值得注意的关键一点,就是作者所依据的丁韪良的《万国公法》汉译本问题。井上哲次郎及其他日本学者即根据同样的理由断言,“权利”一语并非日本人所创译,这个译语是从中国传入的;因为在明治以前,中国学术界即已使用“权利”这个译语了。至于西周,他仅译出了“权”或“权义”,并未用过“权利”二字,所以,“权利”二字实创始于丁韪良。
与前引N?Hozumi、Z?Kitagawa等日本学者的说法对照来看,尽管近代意义上的“权利”一词究为日本人所创行,抑或借自中国的成语,日本学者的看法即是两出,但是依照大木夫見文彦提供的史实所表明的看法最终得到了国际汉学界的普遍接受,并已成为一个日益强化的趋势。
美国学者马里乌斯?詹森(Marius B?Jansen)于1970年代就指出,西方国际法书籍的早期中文译本中所包含的某些重要的汉字词组,如“权利”(right)、“主权”(sovereignty)这样一些相近的字眼,逐渐流入了日本人的“现代”思想中,并在19世纪末在日本广泛流传。尽管这些术语和后来大量涌进中国语言里的日本词语比较起来数量有限,但他特别提醒人们注意,说这是“中国较早与西方接触而使日本获得的一个最后的,也是很少被人提到的好处……”(按:此处着重为笔者所加)
1993年,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发表了他对于近现代汉语外来语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他批评研究现代汉语词汇的一些学者,尤其是高铭凯、王立达和实藤惠秀,“通常一味强调后面这段过程(按:指19世纪末期),对于那些进入汉语的日语新词,他们以为是借自日语的。而事实是,这类词汇中有好多是由中国传至日本的,几十年后才又回到了中国”。在他所指的情形中,就包括了“权利”一词。
我国则自高、刘、王的论著发表后不久,郑奠即发表了一篇回应的文章——《谈现代汉语中的“日语词汇”》(1958年),旨在缩小由前述作者过分夸大了的现代汉语中属于日语词汇的范围。郑采取历史的和客观的立场,强调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互动过程对于促进汉语词汇发展的重要作用。这篇言简意赅的文章实际上提出了本应值得注意的思路和线索,但后来它似乎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以至这一问题长期未能得到澄清。
观上列种种说法,笔者深感这个问题其实本不该如此复杂。从上述一些说法涉及的种种历史资料当中,我们不难推断出汉语“权利”一词的近代渊源,当然也包括其他的法律语词。可是,丁韪良1864年的《万国公法》汉译本明明摆在那里,而非要说权利等词语创自日本。个中原因,除了对自己去今不远的历史茫然无知外,我们还能再说些什么呢?探索近代汉语法律语词的来源无疑要掌握充分的、必要的文献史料。但从上面的例子来看,问题还并不仅仅是史料的占有,而首先是观念上的问题,即我们如何对待历史。这涉及到中国和日本各自摄取西学的过程,和两者基于同文的(“汉字文化圈”)文化交流的互动关系。要深入地理解这些词语的意义及其演变,我们就应当深入到这些语词创制和使用的时代环境当中,揭开长期遮蔽我们视线的那些观念上的障碍,最终来判别出它们的来龙去脉。而那个障碍,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往往强调中国法律的近代化深受日本影响,而对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是否曾对日本发生过作用一类的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
本文所涉及法学名词列表如下,
人权 公证人 引渡 主权 公诉 出庭
代理 民主 民法 自由 共和 有价证券
刑法 仲裁 投票 判决 法人 法定
法医学 法则 法律 法科 法学 法庭
社团 社团法人 免除 治外法权 制裁 取缔
拘留 所得税 所有权 政府 政策 政党
政治家 信托 特权 财团法人 时效 动产
假释 国际 国际公法 最惠国 传票 债务
债权 领土 领空 领海 宪法 总理
证券 警察 议会 辩护士 权利
就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关系看,日本自古即形成了模仿中国法制的传统。一般认为,早在奈良朝时代,日本即开始输入汉学,继受中国法,此后日本乃有成形法。当时日本的律令完全模仿中国,其体裁和内容皆与唐律相似;自篇目名称、次序、条文之分配,以至文章语句,殆无不完全与之相同。正如日本学者所评价,
就法律文化来说,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最明显的也是在唐代。唐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在当时世界上是先进、文明的国家,其封建法制为各国统治者所羡慕。唐代的长安城也因此成了国际性的大都市。唐代的法律,被称为中国封建法典之楷模,曾随着络绎不绝的使者和留学生传播四方,日本也不例外。
10世纪以后,武家政治重实用而轻虚文,另外武家之中没有能用汉字起草法规的学者,于是除了惯用的法律术语外,放弃从来法制的律、令、格、式等纯汉文体,概用武家上下均能了解的通用的汉字日本文(文字虽用汉字而文章则为日本文)为法令的文体。可是即便如此,当时的“缙绅之士,皆以汉文为高尚而尊之,以日本文为卑贱而远之”。德川幕府时代(17世纪以后)的法令用汉字混以平假名(草书字母)书写。
至明治(1868年)以后,法律文体随政体的“王政复古”而复于古。由于维新政府的执政者大部分为汉学出身,如江藤新平、大木乔任两司法大臣,及编纂刑律之水本成美,起草军法之西周等皆为汉学之硕儒,此外大小官吏也多出身于汉学,因此他们写下的法令及公文书,都倾向于汉文体。例如,明治元年(1868年)拟订的《暂行刑律》和三年(1870年)公布之《新律纲领》,即模仿明清律的体裁编纂。明治六年颁布的《改定律例》的文体亦仿照《新律纲领》,与之同为汉文体。维新政府初期的法令均用汉文体,因此法律用语废除了“御触书”、“御书付”、“御定目”等旧名称,而用“法令”、“布告”、“布达”、“达”、“条例”等名称,不说“公事”而说“诉讼”;不说“役人”而说“官吏”。又如明治四年颁布了西周为兵部起草的《海陆军刑律》,西周精通汉文,又曾留学荷兰,因此他起草的刑律,内容实质上虽采用西方各国军律,但其形式则采用中国律。各编标题都用“律”字,如“谋叛律”、“奔敌律”、“战时逃亡律”、“凶暴劫掠律”、“盗贼律”之类,又用“凡”字作各条之起句,其文体全为中国律。不过由于纯粹的汉文体已经不能适应日本近代化发展的需要,这时的法律用语混入了片假名(楷书字母)。
因此,日本法律发达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中国文字在日本传播和演变的历史。汉字一直是书写日本法律不可缺少的一种工具。“日本的汉字都是从中国一点一画地学过来的。所以倘使某字的写法在中国加多了一画时,日本也跟着增加一画;减少了一画,日本也跟着减少一画。对于成语,日本人亦墨守中国的成规。”只是到了明治时代(1868年—1911年)以后,日本在汉字字型上遵循一律向中国看齐的原则,方才开始动摇。
再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关系上看。16世纪以后,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两者都长期经历了接触或摄取西学的过程。但应当有所区别的是,中日两国在接触西学的途径和方式上有其各自的特点。
一般来讲,近代西方殖民者在东亚进行文化扩张和意图攻取的目标,主要集中在中国。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忽略日本或东亚的其他国家,也与中国人是否愿意接纳西学的态度或政策无关。他们认为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传统等方面,中国的地位都要比日本更重要。中国是东方诸国的大宗,一旦“中华归主”,作为处于主体文化边缘地位的藩属,如日本,自会率从。而这种意识的出现,始于葡萄牙人沙勿略。
沙勿略是最早东来的耶稣会传教士。他起先即在日本传教,其间当他与有学识的日本人、特别是僧人讨论时,对方总要问他“汝教如独为真教,缘何中国不知有之?”沙氏惊讶“日本人对其比邻大国之文学哲理深致敬佩,盖此为日本全部文化之本也”。由于这样的问题和作答不止一次,于是他开始思考,最后得出了“使日本归依之善法,莫若传播福音于中国”的结论。在他去世的那一年(1552年)记述到,“中国乃一可以广事传播耶稣基督教理之国。若将基督教理输入其地,将为破坏日本诸教派之一大根据点”。沙勿略决意进入中国传教的愿望虽然未能实现,但却为他的后继者们留下了这条重要的经验,并长期影响着西人对东方进行文化传播的目标取向。
19世纪初期东来的新教传教士,一开始就把精力主要用在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著述和编译有关西方知识的中文读物上面。他们在中国——初为南洋,继而东南沿海——所从事的西学汉译工作,或者反过来说,中国在接触西方知识的语言条件方面的水平,是要高于日本的。
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和禁书制度。几乎所有与西方文明的接触,都只能通过长崎一港与中国和荷兰的有限的贸易活动进行的。当时日本人获取西学知识的渠道因而只有两条:一是从中国传入的西书中文译本当中间接获得;另外就是所谓的兰学。“兰学”是泛指关于荷兰的学问。虽然它在后来发展为内容更为丰富的“洋学”,并将中国系统的西方学术也纳入它的名下,但在开国前,它是以翻译和研究荷兰文的西医知识为核心内容的,加之洋书进口的严格控制,所以兰学对于日本人了解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作用十分有限。
中国向日本输出的汉译西书则是日本人获取西方各种知识的主要来源。1850年代,“不仅中国新出版的书籍被立即带回日本,即使尚未出版的,也时常传述消息,使日本学者急切盼待”。据日本学者的统计,仅从1840年至1855年的16年间,中国商船就运载了3407种45481部书籍到达日本。其中就有《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等介绍世界知识的最新书籍。也就是说,19世纪初期新教传教士编写的载有丰富的西方政法知识信息的中文西书,经此途径完全流入到了日本。日本人将这些收购来的汉译西学书籍以翻刻重版,或训点后印刷出版的方式,加以学习和利用,时间上则紧随中国的原刊本出版之后。
丁韪良的《万国公法》,正是明治维新前后翻刻汉译政法类书籍次数最多、印量最大而且反应速度最快的书籍之一。
,万国公法》于1864年底在北京出版后不久,就出现了开成所的翻刻本六册,只在人名、地名旁边加上了日文字母的读音。该书在日本除了庆应元年(1865年)、四年(1868年),明治四年(1871年)、八年(1875年)、十四年(1881年)、十九年(1886年)的翻刻本外,还有堤士志的《万国公法释义》(四册,1868年京都)、瓜生寅根据英文原文校译的《交道起源》(又名《万国公法全书》,1868年)、重野安绎译述的《和译万国公法》(1870年鹿儿岛藩)以及高谷龙州注解、中村正直批阅的《万国公法蠡管》(1876年东京府)等各种不同形式的译、注本出版。总之,明治初期《万国公法》的各种节译、全译的日译本多达数十种。明治五年(1872年)日本公布新学制时,《万国公法》还被指定为教科书。《万国公法》在日本如此受欢迎,与“万国交际之时尤为需要”的情势分不开的。明治政府成立后,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挽回主权为目标,故这个译本当时被奉为与西方列强进行交涉的权威经典,甚至还流传着“长剑不如短剑,短刀不如手枪,手枪不如《万国公法》”的说法,以致出现了“识者争读此书”,视之为当时“最流行之学问”的局面。
除了《万国公法》,当时传入日本的中译西方法学书籍还有《星轺指掌》(原刊于1876年,1879年柳泽信大的训点本)、《公法会通》(原刊于1880年,1881年岸田吟香的训点本翻刻出版)、《法国律例》(原刊于1882年,司法省训点本1883年印行)等等。它们都是由京师同文馆才出版不久的。
中译本在日本大受欢迎的原因,除了由于本国尚未具备直接翻译能力,中译本是吸收西洋文化的一条便捷途径,可省学习外语之劳以外,再就是中译本有阅读技术上的便利条件——这些书是日本知识阶层大多熟悉的汉字。在一些人看来,这种中译本还是克服翻译荷兰文化重重障碍的先决条件。直到1871年日本的一条普通学则还规定,
环海各国,皆我同井四邻也。……且初学者,未通其语言,未习其文学,故宜先就汉人所译之书而加研习,以得其略。
当时日本人对中译西书依赖和相信之深可见一斑;而这种借助翻刻西书中译本输入西学的做法,也一直持续到大约1880年代末。
既然早在1868年明治维新前后几十年间,《万国公法》等中译本就已经在日本广为传播,成为正处于学习西方知识热潮中的日本人十分熟悉的读物,因此,箕作麟祥、津田真道等这些从事西法译介工作开路先锋的人,在创制近代法律词汇时就不会不受到这些中国译本的影响。在经过苦苦的思索和反复地推敲之后,将那些在中译本里已经出现,而且也是刚刚被赋予了新意的词汇——如“权利”——直接拿过来,去克服他们正在试图逾越的语言难关,是完全可能的。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是中日两国同在西方的巨大压力下为实现近代化而竞争的关键时期。与中国对西学反应态度迟缓适成对照的是,日本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崛起,至1880年代末,随着出洋学生的陆续回国、聘请外教造就的人才逐步开始任事,日本摆脱中译本而径自输入和吸收西洋文化的条件逐渐成熟,开始告别传统中国文化,所谓“脱亚入欧”。中日两国传统的文化关系自此显示出逆转之势。
随着日本推行近代化的成功经验开始引起中国人的注意,经过日本化了的西方制度和知识也开始影响中国。不过这一切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1894至1895年间的中日战争有助于我们确定这种转变的性质,但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来讲,日本西化以后的文化之影响中国,大约始于十多年前,即自1870年代末以后——从出使大臣的观察和记述,到维新运动思想家与清廷大员同声鼓吹学习和效法日本,再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呈现出阶段性的不同途径的输入日本近代制度文化的特征。
中文著作里最早观察并记录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制度变化的,是清政府派遣日本的出使大臣、那些为了开阔眼界游历外洋的官员以及受地方官府资助的考察人士或自费出游的知识分子。这是日本法律词汇和新概念进入中国语文的一条最初的途径。
在首任出使日本公使何如璋(1877年赴任)的《使东述略》,以及1887年派赴外洋游历的兵部郎中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馀记》(1887年)、刑部主事顾厚琨的《日本新政考》(1888年)等书籍当中,都不同程度地记录了日本自维新以后靡然以泰西为式的制度、器物、语言、文字的新情况,而且内容越来越详细。例如《日本新政考》一书特辟《刑罚考》一目,反映了明治后日本的法制与司法状况。
然而无论从内容之详备,还是与后来所发生影响的关系上看,黄遵宪(1877年作为参赞出使日本)于1887年写成的《日本国志》,都可称得上是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这部巨著按照中国史书编纂体例的传统,列《刑法志》为其一志。其最有价值者,乃将明治十三年(1880年)公布的《治罪法》(即“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又称旧刑法)全部翻译,并加以自己的注解。可以说,黄遵宪当时已是最权威的日本近代法律专家。
将这两部法律的日文原本与《刑法志》里的中译本进行对照,可以发现,原文中除夹杂以个别的假名之外,条文里的名词几乎全部使用汉字。中译本《刑法志》除了将原文里面凡是有假名的名词或术语里的假名予以删除,并按照中国人的表述习惯对一些字词重新加以调整外,余者则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例如《治罪法》里面的“犯罪ノ搜查起诉及ヒ豫审”、“告诉及ヒ告发”、“捡察官ノ起诉”、“民事原告人ノ起诉”、“被告人ノ讯问及ヒ对质”、“再审ノ诉”、“裁判管辖ヌ定ムルノ诉”,转变为中译文,便是“犯罪搜查起诉及豫审”、“告诉及告发”、“检察官起诉”、“民事原告人起诉”、“被告人推问及对质”、“再审之诉”、“定裁判所管之诉”;其他大量不带假名者,则完全照抄,如“违警罪裁判所”、“大审院”、“高等法院”、“搜查”、“现行犯罪”、“起诉”、“令状”、“证据”、“保释”、“特赦”等是。
旧《刑法》里的情形亦然。旧《刑法》里面有许多表示罪名的复合结构的名词带有假名。当翻译成中文时,通常是先将这些假名一概删去,然后将这些名词最前面的表示宾格的字词后置,并保留原词最后面的“罪”字的位置不变,即告成之。例如“国事ン关スル罪”——“关国事罪”、“官吏ノ职务ヌ行フヌ妨害スル罪”——“妨害官吏职务罪”、“往来通信ヌ妨害スル罪”——“妨害通行音信罪”、“货币ヌ伪造スル罪”——“伪造货币罪”、“私印私书ヌ伪造スル罪”——“伪造私印私书罪”、“公选ノ投票ヌ伪造スル罪”——“伪造公选投票罪”、“商业及ヒ农工ノ业ヌ妨害スル罪”——“妨害商业及农工业罪”、“财产ン对スル罪”——“对人财产之罪”,等等。
中译本对于日文原本的语言转换如此简便易行,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刑事立法技术上采取汉文体有直接的关系。穗积陈重指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的立法分刑法、宪法和民商法三种系统。这三种系统的文体各殊,用语有异。与宪法系统之庄重森严、民商法系统之平易通俗不同,刑法系统采取汉文体。它以纯用汉文之中古“律”为远祖,并以维新后混以假名的汉文体的《暂行刑律》和《新律纲领》为现时刑事法之始祖,其特性遗传于其以后之刑事法律。基于这种传统的理由,所以当编纂明治十三年(1880年)所发布之《刑法》及《治罪法》之际,专设一名非法学家之汉文大家来担任法典编纂委员。
作为改革传统法律的起点,日本的《治罪法》和《刑法》又都是在翻译和仿照法国法的基础上制定的。时代所趋,新法不得不创造新词以表达新的概念。新词虽仍借助固有的汉字复合而成,但这些互相连属构成的新词的意思却往往无法从原字的意思中推出。正因此,译文当中随处都有对法律新词概念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罪法》和旧《刑法》当中实已包含了许多被日语化了的新的法律概念。换言之,黄氏著《刑法志》一篇,已在开始向中国输入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概念了。
黄遵宪撰写之时,日本的民商等法典尚未颁布实施,加之1882年黄被调离日本,另就他任,故关于此类法律语词,《刑法志》一文尚无从道及。
甲午战争后,国人受到一大刺激。自此,学习西学的途径和目标更趋明确和具体,这就是以日本为途径,以日本为榜样。
1895年张之洞发表了他的名著《劝学篇》,广为刊布,风行海内外。这篇被称为“留学日本宣言书”的小册子,大力鼓动应多译西国有用之书,并广派出洋游学之人。他权衡了东西洋的各种因素,指出无论从哪方面来讲,游学日本和翻译日本书籍都是迅速达到富强的最有效捷径。他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而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理由之一是“东文近中文,易通晓”。在他看来,“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他知道欲求精备的西学应赴西洋,但在眼下,惟以日本最佳。此外,他还提出了译书的三项具体措施,其一是各省多设译书局;其二是出使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译之(晚清修律时许多外国法典的获取,正是这样的途径来源);其三是利用上海的商业和文化条件,鼓励民间广译西书,其销流必广(这成为清末翻译西书的一条最重要渠道)。
总之,他的观点就是“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
受黄遵宪和马建忠等人的启发,梁启超也发表了他对于翻译外国书籍的激进的观点。1896年,在他的第一部政论性著作《变法通议》里面,专列“论译书”一节,指陈过去译书之得失,并倡言当今译书之重要与方法,提醒人们注意以日本作为学习西学的好处。他的结论是,
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译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计日文之易成,约有数端,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扞格之音,二也。文法舒阔,三也。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也。汉文居十六七,五也,故黄君公度,谓可不学而能,苟能强记,半岁无不尽通者,以此视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
1899年,梁在《清议报》发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进一步鼓吹学习日文的好处,
学英文者经五六年始成,其初学成也尚多窒碍,犹未必能读其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之书也。而学日本文者,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日本之学,已尽为我有矣。
显然,在主张游学日本和翻译日文书籍这一点上,梁的看法与张之洞的上述观点如出一辙,而且更加乐观。在19世纪末各种思想风云激荡的年月,作为一位出色的鼓动家,同时也是实践者,梁启超拼命通过这种便捷的语言条件吸取新的思想和知识,为日语化的西方思想文化概念的介绍和传播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而如此倡导学习日文并翻译日本书籍,这为后来留日学生大量从日本吸收西学制造了舆论。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官员和学者大力提倡学习日本的言论中,不仅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的色彩,同时也暗含着对于过去几十年里所推行现代化措施的失望和对以往成绩的低估。而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西学引进方面已有的积累最终被抛弃了。
另外,日本方面对华政策上的变化,即在“清国保全论”的旗号下,为积极招徕中国人留学日本而采取的种种措施,也是促成文化关系逆转的一方面因素,进而使日本化的西方政治法律概念的传入中国成为可能。
无疑,清末法律制度的变革几乎是仿照日本模式而来的。来华日本法律顾问、特别是留日法科学生对于日本法律语词和概念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贡献莫大;中国近现代的一套法律话语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但这并不等于说,经此途径而来的所有的法律词语就一定是由日本人创制的。马西尼关于大量文献的语词统计分析研究表明,在现代汉语里,通常被视为来自日语的汉字中,其实约有五分之一早在19世纪后半叶的汉语文献中就已经有了。
那么为什么有些词语被认为是创自日本的呢?
实际上,某一词语何以获得它的新意,和这个词语又何以得到广泛流行和为人们接受,有时并不是一回事。对此加以适当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误认为像“权利”以及其他一些的政法词语都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这个问题。
前文我们已经讨论过,“权”或“权利”等词早在1864年即已大量出现在国际法译本当中,但是直到十多年以后丁韪良还要对它作出特别说明,可见当时人们对这些词语的陌生和不理解。更何况当时阅读公法著作的人毕竟只是数量极为有限的上层官僚,因此这类词语影响所及之范围自然有限。这也反映了当时清政府和处于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新概念的不敏不察,反应迟钝,以至最终国人要为思想观念的近代化而感谢日本。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此其一。
其二,上面已经提到,甲午战争之后朝野对洋务运动普遍地、严厉地指责,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忽视了以往几十年里在输入西学方面的成就。一种抛弃过去已有的积累,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激情从人们的内心深处迅速升腾,并且很快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了过去一向看不起的“蕞尔小国”日本。这种风向的转变在公共心理上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由此,与“洋务”时代只有少数人接触“公法”的情形已经完全不同,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在日本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法律和其他社会科学知识,在头脑中灌注了大量西方的自由、平等、民权、法制的名词和概念。作为立宪共和时代的主角,他们回国后又大都成了变法改制的思想鼓动家和实践家,他们的话语遂成为社会变革时代的主流话语。随着负载着西方思想、观念、理论和学说的日本式的语词以及表述方式的普遍流行,一个“东洋化”的近代世界的概念被缔造出来,这是后来人们往往以为中国近代的法政名词、术语和概念皆自日本而来的最重要原因。
王健
[原文分上、中、下三期分别刊于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24日、1月28日和2月4日的法治时代B2版上。]
主持人提示:考察西方法律语词传入中国的路径及方式,对于我们了解中西法律文化的性质和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诚如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所言:“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观察,一个民族对另一个异文化语词的翻译和接受的过程,可以视为一种文化的移入。”
王健教授的《输出与回归:法学名词在中日之间》一文,通过考察中、日之间法学语词互相借鉴的历史轨迹,澄清了法学界的一些理论误区,揭示出了中西方之间法律文化的一些异同,力图为中国法找到一条更适合自己的、既能超越传统又能摆脱西方个别经验的发展之路,意义可谓重大。今人常常以为,目前我们习见习用的一套法言法语大多于本世纪初期来自东瀛岛国的日本,然而事实并不如此简单,有的甚至相反。本文就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先从语言学界关于近代汉语语源问题上的讨论说起。
1950年代,随着文字改革和语言规范化运动的开展,关于现代汉语中的学术用语和外来语问题,特别是近代日语对汉语的影响等问题,曾引起过中国语言学家的一场热烈讨论;讨论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两种不尽相同的说法,或可说是对立的倾向。
其中一种颇有影响的看法断言,现代汉语中有许多借用日本的语词,这些词大都是明治维新以后,由于日本人翻译西文书籍陆续创造出来的。从历史上来说,它们不仅在我们国人的心目中被认为是“新名词”;就是在日本国内也同样被认为是近百年来产生的“新语”。这种观点以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刘正琰和王立达为代表。高、刘二人合著了《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在所列“汉语外来词所表现的外来事物及概念一览表”里面,作者指出其中属于外来法律类的总共39个语词全部来自日语,没有一个来自该表列出的其他9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包括俄语、德语、意大利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王立达则以新名词、新知识一类词典为例,指出其中所收的词汇“几乎有一半是借自日语的”。
已有学者对他们各自所列出的来自日本的现代汉语词汇作了综合,笔者仅检阅其中有关法律类的语词请另见表。
这些词在今天法律人的言说中占有怎样的地位不言自明,而令人惊讶的是,按照这个表,如此众多而又基本的法律词汇竟然全部都是源自日本的外来语!对此,当时就有人表示不能完全接受这种看法,因为它过分夸大了现代汉语中源于日本的外来语的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讨论似乎只是发生在语言学界的内部,对于从根本上直接涉及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在当时和以后似乎都没有产生什么多大的影响,至少就法学界而言,情形就是如此;因为除了学者偶尔涉及的个别法律语词外,法学界从来就没有对近现代法律用语问题做过专门认真地清理和检讨。可是尽管如此,一个时时可以感觉得到,但又都说不大准、模模糊糊的印象是,我们目前所使用的许多(注意这是一个模糊词)法律名词、术语是来自日本的。而有关于“权利”——这是一个在本文中常常被提起的例子——的近代语源的种种说法,正是反映上述问题的一个典型例证。
关于近现代汉语里的“权利”一词及其相关词语的来源,法学界以往大都认为它(们)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从日本流入到中文里的。明确提出这种说法的书证,至少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位优秀的民法学家梅仲协(1900年—1971年)的民法著作,作者在书中关于权利的专章里指出,
按现代法律学上所谓“权利”一语,系欧陆学者所创设,日本从而移译之。清季变法,“权利”二字,复自东瀛,输入中土,数十年来,习为口头禅。
此说在法学界长期相沿,至今仍频见于大陆、台湾和海外的一些法学论著。如郭道晖于1995年发表的《论法定权利与权利立法》一文中说,
中国法律上“权利”一词始见于清末之立宪和民国之立法。它是由日本传入。日文又是从德文Recht译为“权力利益”,略作“权利”。
同年台湾学者李复甸在其《权利辨正》一文里,依据日本平凡社《世界大百科字典》(1988年)第九卷“权利”词条中的解释,亦说,
……时下之权利出于东洋之译词,(原文此处有注)殆无争议。国人率而沿用,约定而俗成,如今已成为日常口语。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陈添辉在《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中国法制之变化——以民法之制定及施行为例》一文中,引用日本学者Z?Kitagawa的说法写到,
日本尚属中华法系时,亦无权利的观念。留学荷兰Leyden 大学的日本法学者Dr?M?Tsuda,回到日本后,于明治维新那一年,即1868年出版一本书,叫《西方公法学说理论》,因无相当用语来表达权利的观念,于是他在本书首先创造“权利”之用语。在日本社会,权利的观念,曾长期停留在白纸黑字的具文阶段,未为当事人主张。
由于笔者尚未查找到陈文所征引的原著,故无法知晓Z?Kitagawa何以如此持论的依据。不过,此论在日本并不独见。早在1904年N?Hozumi教授的一篇讲演中就有这样的主张,
日本从来没有权利的概念,直到Ken-ri(权利)一词出现,而Ken-ri一词的直接含义是power-interest(权力和利益)。该词的始作俑者是Tsuda博士,Tsuda博士曾在荷兰Leyden大学读书,1868年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论西方的公法》,在这篇文章里,他采用了Ken-ri(权利)一词。
显然,以上两段文字中,前者几乎是后者的翻版,他们都认为,日文之汉字“权利”,系由日本留学荷兰莱顿大学的法学博士津田真道(M?Tsuda)于1868年首先创行的一个用语。
除此之外,也有人指出,日语中的“权利”一词始见于1866年J?S?Mill著作的一个译本;提出这一事例类似情形的还有Pittau。
总之,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无论法学界抑或语言学界,也无论是大陆、台湾甚至日本,按照一种说法,“权利”是来自日本的一个汉语外来词。
然而与此论相左者一直大有人在。日本著名语言学家大木夫見文彦(1847年—1928年)在他所著《箕作麟祥君传》一书里,曾详细地描述了明治初年法学家箕作麟祥(1846年—1897年)为了翻译法国法律而苦心设造法律新名词的情形,其中就涉及到“权利”等词语的翻译问题。兹将这段文字抄录如下,
这是《法兰西法典》首次被引入日本,法理学也尚未发展。箕作麟祥对这些都并无所知;而且也没有带注释的书籍,没有词典,没有教师;克服这些理解上的困难对他是很沉重的负担。每次提到的概念在那时的日本还是完全不知道的,这成了大问题,因为不存在相对的译语。甚至当他请问汉学家时,没有一个人知道该怎样回答;如果他创造一个新词,倘若不是人们已知的汉字的组合,又可能不被接受。像“right”和“obligation”这样的词,他承袭了中国《万国公法》的翻译,译作“权利”和“义务”;至于像“movables”和“immovbles”这样的法律术语,他费尽心思地创造了像“动产”(d?san)和“不动产”(fud?san)这样的新词。
这段文字很可能是后来各种关于日本近代的“权利”等词来源于中国早期汉文译本说法的最早的依据。其中值得注意的关键一点,就是作者所依据的丁韪良的《万国公法》汉译本问题。井上哲次郎及其他日本学者即根据同样的理由断言,“权利”一语并非日本人所创译,这个译语是从中国传入的;因为在明治以前,中国学术界即已使用“权利”这个译语了。至于西周,他仅译出了“权”或“权义”,并未用过“权利”二字,所以,“权利”二字实创始于丁韪良。
与前引N?Hozumi、Z?Kitagawa等日本学者的说法对照来看,尽管近代意义上的“权利”一词究为日本人所创行,抑或借自中国的成语,日本学者的看法即是两出,但是依照大木夫見文彦提供的史实所表明的看法最终得到了国际汉学界的普遍接受,并已成为一个日益强化的趋势。
美国学者马里乌斯?詹森(Marius B?Jansen)于1970年代就指出,西方国际法书籍的早期中文译本中所包含的某些重要的汉字词组,如“权利”(right)、“主权”(sovereignty)这样一些相近的字眼,逐渐流入了日本人的“现代”思想中,并在19世纪末在日本广泛流传。尽管这些术语和后来大量涌进中国语言里的日本词语比较起来数量有限,但他特别提醒人们注意,说这是“中国较早与西方接触而使日本获得的一个最后的,也是很少被人提到的好处……”(按:此处着重为笔者所加)
1993年,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发表了他对于近现代汉语外来语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他批评研究现代汉语词汇的一些学者,尤其是高铭凯、王立达和实藤惠秀,“通常一味强调后面这段过程(按:指19世纪末期),对于那些进入汉语的日语新词,他们以为是借自日语的。而事实是,这类词汇中有好多是由中国传至日本的,几十年后才又回到了中国”。在他所指的情形中,就包括了“权利”一词。
我国则自高、刘、王的论著发表后不久,郑奠即发表了一篇回应的文章——《谈现代汉语中的“日语词汇”》(1958年),旨在缩小由前述作者过分夸大了的现代汉语中属于日语词汇的范围。郑采取历史的和客观的立场,强调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互动过程对于促进汉语词汇发展的重要作用。这篇言简意赅的文章实际上提出了本应值得注意的思路和线索,但后来它似乎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以至这一问题长期未能得到澄清。
观上列种种说法,笔者深感这个问题其实本不该如此复杂。从上述一些说法涉及的种种历史资料当中,我们不难推断出汉语“权利”一词的近代渊源,当然也包括其他的法律语词。可是,丁韪良1864年的《万国公法》汉译本明明摆在那里,而非要说权利等词语创自日本。个中原因,除了对自己去今不远的历史茫然无知外,我们还能再说些什么呢?探索近代汉语法律语词的来源无疑要掌握充分的、必要的文献史料。但从上面的例子来看,问题还并不仅仅是史料的占有,而首先是观念上的问题,即我们如何对待历史。这涉及到中国和日本各自摄取西学的过程,和两者基于同文的(“汉字文化圈”)文化交流的互动关系。要深入地理解这些词语的意义及其演变,我们就应当深入到这些语词创制和使用的时代环境当中,揭开长期遮蔽我们视线的那些观念上的障碍,最终来判别出它们的来龙去脉。而那个障碍,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往往强调中国法律的近代化深受日本影响,而对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是否曾对日本发生过作用一类的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
本文所涉及法学名词列表如下,
人权 公证人 引渡 主权 公诉 出庭
代理 民主 民法 自由 共和 有价证券
刑法 仲裁 投票 判决 法人 法定
法医学 法则 法律 法科 法学 法庭
社团 社团法人 免除 治外法权 制裁 取缔
拘留 所得税 所有权 政府 政策 政党
政治家 信托 特权 财团法人 时效 动产
假释 国际 国际公法 最惠国 传票 债务
债权 领土 领空 领海 宪法 总理
证券 警察 议会 辩护士 权利
就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关系看,日本自古即形成了模仿中国法制的传统。一般认为,早在奈良朝时代,日本即开始输入汉学,继受中国法,此后日本乃有成形法。当时日本的律令完全模仿中国,其体裁和内容皆与唐律相似;自篇目名称、次序、条文之分配,以至文章语句,殆无不完全与之相同。正如日本学者所评价,
就法律文化来说,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最明显的也是在唐代。唐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在当时世界上是先进、文明的国家,其封建法制为各国统治者所羡慕。唐代的长安城也因此成了国际性的大都市。唐代的法律,被称为中国封建法典之楷模,曾随着络绎不绝的使者和留学生传播四方,日本也不例外。
10世纪以后,武家政治重实用而轻虚文,另外武家之中没有能用汉字起草法规的学者,于是除了惯用的法律术语外,放弃从来法制的律、令、格、式等纯汉文体,概用武家上下均能了解的通用的汉字日本文(文字虽用汉字而文章则为日本文)为法令的文体。可是即便如此,当时的“缙绅之士,皆以汉文为高尚而尊之,以日本文为卑贱而远之”。德川幕府时代(17世纪以后)的法令用汉字混以平假名(草书字母)书写。
至明治(1868年)以后,法律文体随政体的“王政复古”而复于古。由于维新政府的执政者大部分为汉学出身,如江藤新平、大木乔任两司法大臣,及编纂刑律之水本成美,起草军法之西周等皆为汉学之硕儒,此外大小官吏也多出身于汉学,因此他们写下的法令及公文书,都倾向于汉文体。例如,明治元年(1868年)拟订的《暂行刑律》和三年(1870年)公布之《新律纲领》,即模仿明清律的体裁编纂。明治六年颁布的《改定律例》的文体亦仿照《新律纲领》,与之同为汉文体。维新政府初期的法令均用汉文体,因此法律用语废除了“御触书”、“御书付”、“御定目”等旧名称,而用“法令”、“布告”、“布达”、“达”、“条例”等名称,不说“公事”而说“诉讼”;不说“役人”而说“官吏”。又如明治四年颁布了西周为兵部起草的《海陆军刑律》,西周精通汉文,又曾留学荷兰,因此他起草的刑律,内容实质上虽采用西方各国军律,但其形式则采用中国律。各编标题都用“律”字,如“谋叛律”、“奔敌律”、“战时逃亡律”、“凶暴劫掠律”、“盗贼律”之类,又用“凡”字作各条之起句,其文体全为中国律。不过由于纯粹的汉文体已经不能适应日本近代化发展的需要,这时的法律用语混入了片假名(楷书字母)。
因此,日本法律发达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中国文字在日本传播和演变的历史。汉字一直是书写日本法律不可缺少的一种工具。“日本的汉字都是从中国一点一画地学过来的。所以倘使某字的写法在中国加多了一画时,日本也跟着增加一画;减少了一画,日本也跟着减少一画。对于成语,日本人亦墨守中国的成规。”只是到了明治时代(1868年—1911年)以后,日本在汉字字型上遵循一律向中国看齐的原则,方才开始动摇。
再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关系上看。16世纪以后,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两者都长期经历了接触或摄取西学的过程。但应当有所区别的是,中日两国在接触西学的途径和方式上有其各自的特点。
一般来讲,近代西方殖民者在东亚进行文化扩张和意图攻取的目标,主要集中在中国。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忽略日本或东亚的其他国家,也与中国人是否愿意接纳西学的态度或政策无关。他们认为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传统等方面,中国的地位都要比日本更重要。中国是东方诸国的大宗,一旦“中华归主”,作为处于主体文化边缘地位的藩属,如日本,自会率从。而这种意识的出现,始于葡萄牙人沙勿略。
沙勿略是最早东来的耶稣会传教士。他起先即在日本传教,其间当他与有学识的日本人、特别是僧人讨论时,对方总要问他“汝教如独为真教,缘何中国不知有之?”沙氏惊讶“日本人对其比邻大国之文学哲理深致敬佩,盖此为日本全部文化之本也”。由于这样的问题和作答不止一次,于是他开始思考,最后得出了“使日本归依之善法,莫若传播福音于中国”的结论。在他去世的那一年(1552年)记述到,“中国乃一可以广事传播耶稣基督教理之国。若将基督教理输入其地,将为破坏日本诸教派之一大根据点”。沙勿略决意进入中国传教的愿望虽然未能实现,但却为他的后继者们留下了这条重要的经验,并长期影响着西人对东方进行文化传播的目标取向。
19世纪初期东来的新教传教士,一开始就把精力主要用在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著述和编译有关西方知识的中文读物上面。他们在中国——初为南洋,继而东南沿海——所从事的西学汉译工作,或者反过来说,中国在接触西方知识的语言条件方面的水平,是要高于日本的。
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和禁书制度。几乎所有与西方文明的接触,都只能通过长崎一港与中国和荷兰的有限的贸易活动进行的。当时日本人获取西学知识的渠道因而只有两条:一是从中国传入的西书中文译本当中间接获得;另外就是所谓的兰学。“兰学”是泛指关于荷兰的学问。虽然它在后来发展为内容更为丰富的“洋学”,并将中国系统的西方学术也纳入它的名下,但在开国前,它是以翻译和研究荷兰文的西医知识为核心内容的,加之洋书进口的严格控制,所以兰学对于日本人了解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作用十分有限。
中国向日本输出的汉译西书则是日本人获取西方各种知识的主要来源。1850年代,“不仅中国新出版的书籍被立即带回日本,即使尚未出版的,也时常传述消息,使日本学者急切盼待”。据日本学者的统计,仅从1840年至1855年的16年间,中国商船就运载了3407种45481部书籍到达日本。其中就有《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等介绍世界知识的最新书籍。也就是说,19世纪初期新教传教士编写的载有丰富的西方政法知识信息的中文西书,经此途径完全流入到了日本。日本人将这些收购来的汉译西学书籍以翻刻重版,或训点后印刷出版的方式,加以学习和利用,时间上则紧随中国的原刊本出版之后。
丁韪良的《万国公法》,正是明治维新前后翻刻汉译政法类书籍次数最多、印量最大而且反应速度最快的书籍之一。
,万国公法》于1864年底在北京出版后不久,就出现了开成所的翻刻本六册,只在人名、地名旁边加上了日文字母的读音。该书在日本除了庆应元年(1865年)、四年(1868年),明治四年(1871年)、八年(1875年)、十四年(1881年)、十九年(1886年)的翻刻本外,还有堤士志的《万国公法释义》(四册,1868年京都)、瓜生寅根据英文原文校译的《交道起源》(又名《万国公法全书》,1868年)、重野安绎译述的《和译万国公法》(1870年鹿儿岛藩)以及高谷龙州注解、中村正直批阅的《万国公法蠡管》(1876年东京府)等各种不同形式的译、注本出版。总之,明治初期《万国公法》的各种节译、全译的日译本多达数十种。明治五年(1872年)日本公布新学制时,《万国公法》还被指定为教科书。《万国公法》在日本如此受欢迎,与“万国交际之时尤为需要”的情势分不开的。明治政府成立后,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挽回主权为目标,故这个译本当时被奉为与西方列强进行交涉的权威经典,甚至还流传着“长剑不如短剑,短刀不如手枪,手枪不如《万国公法》”的说法,以致出现了“识者争读此书”,视之为当时“最流行之学问”的局面。
除了《万国公法》,当时传入日本的中译西方法学书籍还有《星轺指掌》(原刊于1876年,1879年柳泽信大的训点本)、《公法会通》(原刊于1880年,1881年岸田吟香的训点本翻刻出版)、《法国律例》(原刊于1882年,司法省训点本1883年印行)等等。它们都是由京师同文馆才出版不久的。
中译本在日本大受欢迎的原因,除了由于本国尚未具备直接翻译能力,中译本是吸收西洋文化的一条便捷途径,可省学习外语之劳以外,再就是中译本有阅读技术上的便利条件——这些书是日本知识阶层大多熟悉的汉字。在一些人看来,这种中译本还是克服翻译荷兰文化重重障碍的先决条件。直到1871年日本的一条普通学则还规定,
环海各国,皆我同井四邻也。……且初学者,未通其语言,未习其文学,故宜先就汉人所译之书而加研习,以得其略。
当时日本人对中译西书依赖和相信之深可见一斑;而这种借助翻刻西书中译本输入西学的做法,也一直持续到大约1880年代末。
既然早在1868年明治维新前后几十年间,《万国公法》等中译本就已经在日本广为传播,成为正处于学习西方知识热潮中的日本人十分熟悉的读物,因此,箕作麟祥、津田真道等这些从事西法译介工作开路先锋的人,在创制近代法律词汇时就不会不受到这些中国译本的影响。在经过苦苦的思索和反复地推敲之后,将那些在中译本里已经出现,而且也是刚刚被赋予了新意的词汇——如“权利”——直接拿过来,去克服他们正在试图逾越的语言难关,是完全可能的。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是中日两国同在西方的巨大压力下为实现近代化而竞争的关键时期。与中国对西学反应态度迟缓适成对照的是,日本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崛起,至1880年代末,随着出洋学生的陆续回国、聘请外教造就的人才逐步开始任事,日本摆脱中译本而径自输入和吸收西洋文化的条件逐渐成熟,开始告别传统中国文化,所谓“脱亚入欧”。中日两国传统的文化关系自此显示出逆转之势。
随着日本推行近代化的成功经验开始引起中国人的注意,经过日本化了的西方制度和知识也开始影响中国。不过这一切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1894至1895年间的中日战争有助于我们确定这种转变的性质,但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来讲,日本西化以后的文化之影响中国,大约始于十多年前,即自1870年代末以后——从出使大臣的观察和记述,到维新运动思想家与清廷大员同声鼓吹学习和效法日本,再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呈现出阶段性的不同途径的输入日本近代制度文化的特征。
中文著作里最早观察并记录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制度变化的,是清政府派遣日本的出使大臣、那些为了开阔眼界游历外洋的官员以及受地方官府资助的考察人士或自费出游的知识分子。这是日本法律词汇和新概念进入中国语文的一条最初的途径。
在首任出使日本公使何如璋(1877年赴任)的《使东述略》,以及1887年派赴外洋游历的兵部郎中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馀记》(1887年)、刑部主事顾厚琨的《日本新政考》(1888年)等书籍当中,都不同程度地记录了日本自维新以后靡然以泰西为式的制度、器物、语言、文字的新情况,而且内容越来越详细。例如《日本新政考》一书特辟《刑罚考》一目,反映了明治后日本的法制与司法状况。
然而无论从内容之详备,还是与后来所发生影响的关系上看,黄遵宪(1877年作为参赞出使日本)于1887年写成的《日本国志》,都可称得上是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这部巨著按照中国史书编纂体例的传统,列《刑法志》为其一志。其最有价值者,乃将明治十三年(1880年)公布的《治罪法》(即“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又称旧刑法)全部翻译,并加以自己的注解。可以说,黄遵宪当时已是最权威的日本近代法律专家。
将这两部法律的日文原本与《刑法志》里的中译本进行对照,可以发现,原文中除夹杂以个别的假名之外,条文里的名词几乎全部使用汉字。中译本《刑法志》除了将原文里面凡是有假名的名词或术语里的假名予以删除,并按照中国人的表述习惯对一些字词重新加以调整外,余者则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例如《治罪法》里面的“犯罪ノ搜查起诉及ヒ豫审”、“告诉及ヒ告发”、“捡察官ノ起诉”、“民事原告人ノ起诉”、“被告人ノ讯问及ヒ对质”、“再审ノ诉”、“裁判管辖ヌ定ムルノ诉”,转变为中译文,便是“犯罪搜查起诉及豫审”、“告诉及告发”、“检察官起诉”、“民事原告人起诉”、“被告人推问及对质”、“再审之诉”、“定裁判所管之诉”;其他大量不带假名者,则完全照抄,如“违警罪裁判所”、“大审院”、“高等法院”、“搜查”、“现行犯罪”、“起诉”、“令状”、“证据”、“保释”、“特赦”等是。
旧《刑法》里的情形亦然。旧《刑法》里面有许多表示罪名的复合结构的名词带有假名。当翻译成中文时,通常是先将这些假名一概删去,然后将这些名词最前面的表示宾格的字词后置,并保留原词最后面的“罪”字的位置不变,即告成之。例如“国事ン关スル罪”——“关国事罪”、“官吏ノ职务ヌ行フヌ妨害スル罪”——“妨害官吏职务罪”、“往来通信ヌ妨害スル罪”——“妨害通行音信罪”、“货币ヌ伪造スル罪”——“伪造货币罪”、“私印私书ヌ伪造スル罪”——“伪造私印私书罪”、“公选ノ投票ヌ伪造スル罪”——“伪造公选投票罪”、“商业及ヒ农工ノ业ヌ妨害スル罪”——“妨害商业及农工业罪”、“财产ン对スル罪”——“对人财产之罪”,等等。
中译本对于日文原本的语言转换如此简便易行,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刑事立法技术上采取汉文体有直接的关系。穗积陈重指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的立法分刑法、宪法和民商法三种系统。这三种系统的文体各殊,用语有异。与宪法系统之庄重森严、民商法系统之平易通俗不同,刑法系统采取汉文体。它以纯用汉文之中古“律”为远祖,并以维新后混以假名的汉文体的《暂行刑律》和《新律纲领》为现时刑事法之始祖,其特性遗传于其以后之刑事法律。基于这种传统的理由,所以当编纂明治十三年(1880年)所发布之《刑法》及《治罪法》之际,专设一名非法学家之汉文大家来担任法典编纂委员。
作为改革传统法律的起点,日本的《治罪法》和《刑法》又都是在翻译和仿照法国法的基础上制定的。时代所趋,新法不得不创造新词以表达新的概念。新词虽仍借助固有的汉字复合而成,但这些互相连属构成的新词的意思却往往无法从原字的意思中推出。正因此,译文当中随处都有对法律新词概念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罪法》和旧《刑法》当中实已包含了许多被日语化了的新的法律概念。换言之,黄氏著《刑法志》一篇,已在开始向中国输入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概念了。
黄遵宪撰写之时,日本的民商等法典尚未颁布实施,加之1882年黄被调离日本,另就他任,故关于此类法律语词,《刑法志》一文尚无从道及。
甲午战争后,国人受到一大刺激。自此,学习西学的途径和目标更趋明确和具体,这就是以日本为途径,以日本为榜样。
1895年张之洞发表了他的名著《劝学篇》,广为刊布,风行海内外。这篇被称为“留学日本宣言书”的小册子,大力鼓动应多译西国有用之书,并广派出洋游学之人。他权衡了东西洋的各种因素,指出无论从哪方面来讲,游学日本和翻译日本书籍都是迅速达到富强的最有效捷径。他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而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理由之一是“东文近中文,易通晓”。在他看来,“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他知道欲求精备的西学应赴西洋,但在眼下,惟以日本最佳。此外,他还提出了译书的三项具体措施,其一是各省多设译书局;其二是出使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译之(晚清修律时许多外国法典的获取,正是这样的途径来源);其三是利用上海的商业和文化条件,鼓励民间广译西书,其销流必广(这成为清末翻译西书的一条最重要渠道)。
总之,他的观点就是“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
受黄遵宪和马建忠等人的启发,梁启超也发表了他对于翻译外国书籍的激进的观点。1896年,在他的第一部政论性著作《变法通议》里面,专列“论译书”一节,指陈过去译书之得失,并倡言当今译书之重要与方法,提醒人们注意以日本作为学习西学的好处。他的结论是,
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译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计日文之易成,约有数端,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扞格之音,二也。文法舒阔,三也。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也。汉文居十六七,五也,故黄君公度,谓可不学而能,苟能强记,半岁无不尽通者,以此视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
1899年,梁在《清议报》发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进一步鼓吹学习日文的好处,
学英文者经五六年始成,其初学成也尚多窒碍,犹未必能读其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之书也。而学日本文者,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日本之学,已尽为我有矣。
显然,在主张游学日本和翻译日文书籍这一点上,梁的看法与张之洞的上述观点如出一辙,而且更加乐观。在19世纪末各种思想风云激荡的年月,作为一位出色的鼓动家,同时也是实践者,梁启超拼命通过这种便捷的语言条件吸取新的思想和知识,为日语化的西方思想文化概念的介绍和传播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而如此倡导学习日文并翻译日本书籍,这为后来留日学生大量从日本吸收西学制造了舆论。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官员和学者大力提倡学习日本的言论中,不仅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的色彩,同时也暗含着对于过去几十年里所推行现代化措施的失望和对以往成绩的低估。而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西学引进方面已有的积累最终被抛弃了。
另外,日本方面对华政策上的变化,即在“清国保全论”的旗号下,为积极招徕中国人留学日本而采取的种种措施,也是促成文化关系逆转的一方面因素,进而使日本化的西方政治法律概念的传入中国成为可能。
无疑,清末法律制度的变革几乎是仿照日本模式而来的。来华日本法律顾问、特别是留日法科学生对于日本法律语词和概念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贡献莫大;中国近现代的一套法律话语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但这并不等于说,经此途径而来的所有的法律词语就一定是由日本人创制的。马西尼关于大量文献的语词统计分析研究表明,在现代汉语里,通常被视为来自日语的汉字中,其实约有五分之一早在19世纪后半叶的汉语文献中就已经有了。
那么为什么有些词语被认为是创自日本的呢?
实际上,某一词语何以获得它的新意,和这个词语又何以得到广泛流行和为人们接受,有时并不是一回事。对此加以适当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误认为像“权利”以及其他一些的政法词语都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这个问题。
前文我们已经讨论过,“权”或“权利”等词早在1864年即已大量出现在国际法译本当中,但是直到十多年以后丁韪良还要对它作出特别说明,可见当时人们对这些词语的陌生和不理解。更何况当时阅读公法著作的人毕竟只是数量极为有限的上层官僚,因此这类词语影响所及之范围自然有限。这也反映了当时清政府和处于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新概念的不敏不察,反应迟钝,以至最终国人要为思想观念的近代化而感谢日本。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此其一。
其二,上面已经提到,甲午战争之后朝野对洋务运动普遍地、严厉地指责,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忽视了以往几十年里在输入西学方面的成就。一种抛弃过去已有的积累,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激情从人们的内心深处迅速升腾,并且很快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了过去一向看不起的“蕞尔小国”日本。这种风向的转变在公共心理上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由此,与“洋务”时代只有少数人接触“公法”的情形已经完全不同,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在日本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法律和其他社会科学知识,在头脑中灌注了大量西方的自由、平等、民权、法制的名词和概念。作为立宪共和时代的主角,他们回国后又大都成了变法改制的思想鼓动家和实践家,他们的话语遂成为社会变革时代的主流话语。随着负载着西方思想、观念、理论和学说的日本式的语词以及表述方式的普遍流行,一个“东洋化”的近代世界的概念被缔造出来,这是后来人们往往以为中国近代的法政名词、术语和概念皆自日本而来的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