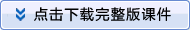话说“民法”
高 尚
人民法院报2006-04-10
“民法”一词我国古已有之。据有关文献记载:“民法之称,见于尚书孔传”,但在该词语出现后的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既没有部门法意义上的“民法”,更不存在私权观念上的“民法”。检视中华法系的历代律典,充其量只存在调整户婚田宅钱债等民事生活内容的零星法条,并不存在现代法学和部门法意义上“民法”。
现代意义上“民法”一词源自罗马法,它在观念形态上蕴涵着保护私权和对民众自治的承认,最终直指对“正义”价值目标的追求;在形式理性上,它强调一种协调一致的逻辑性,是由特定的基本概念、术语和规范而组成的一种法典化的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民法”最早是在19世纪末才在中国初现端倪的,20世纪初则频繁地出现在学术界的著述和官方的典籍档案之中了。
中文文献中最早使用现代意义“民法”一词的,见于1887年黄遵宪所著的《日本国志》一书,其中有云:“私诉以赔偿归还赃物为主,照依民法听被害者自便。”十余年后,康有为为鼓吹变法,曾数次提到要修订民法。1897年,在中国的知识界普遍地对西方系统的法学知识和法律体系极为陌生的情形下,梁启超认真地对待包含了“民律”在内共有六部法典的《法国律例》一书,并将《法国律例》列入他所主持的湖南时务学堂《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中,与学生共同研讨。通过对“民律”的研究,梁启超已不再在概念上将“民律”与“民法”并列而论,对近现代意义上的部门法划分,已有了较准确的理解与把握,对现代意义上的“民法”一词,至少在概念上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术语表达上也是准确的。
如果说,至19世纪末,梁启超还主要地是从概念和术语上把握、论及现代意义的“民法”的话,那么,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则开始体系化地、具体地向国内介绍和引入日本民法、日本民法学、日本民法学著作。留日学生于1900年12月创办了以“研究实学”、“重视责任”为宗旨的《译书汇编》杂志,1901年7月出版的第七期的《译书汇编》上,登载了日本学者樋山广业的《现行法制大意》一文,该文不但对现代民法学体系作了系统介绍,而且,私法类下分两章,第一章为民法,“民法”下辖人及法人、物、物权、债权、亲族、相续六节,各节下又分有细目,较为详尽地介绍了西方的民法结构体例和基本内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毕业于美国芝加哥伊利拿大学法科的胡贻榖于1902年翻译了英国人甘格士所著《History?of?Socialism》一书,并将其中文译名定为《泰西民法志》,这是我国学术界正式引入的第一部西方民法学专著,该书在内容上介绍了罗马法的历史,法国、英国等西欧民法内容、立法旨意、活动及法学家的学说等。由此,民法学的传播在中国全面展开。1903年在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法政辞书中,开始对民法和民法学中的重要概念逐条解释,其中认为“规定私人之相互关系者,谓之民法”。此后,《法兰西民法正文》则让中国法政学界真正地接触和面对大陆法系最具代表性的、差不多也是当时最新的民法典原文。
如果说,19世纪末,极少数的知识精英引入了西方“民法”概念的话,那么,20世纪初的头10年里,中国的法政学术界则以飞一般的速度从理论体系到法典本身“恶补”现代“民法”一课,并呼吁制定中国自己的民法典。
所有上述的努力,基本地都还局限于民间的或学术的立场。官方对待现代“民法”的认识和态度,在1902年没有先兆地突然间明朗起来。1901年清政府的上谕诏书和封疆大吏的条陈奏张中,均无只言片语涉及“民法”,但1902年在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联名保举沈家本主持修订法律的奏议中,明确论及现代意义上的民法问题:“近来日本法律学分门别类,考究亦精,而民法一门,最为西人所叹服。……亦可由出使日本大臣,访求该国法律博士,取其专精民法、刑法者各一人,一并延请来华,协同编译。”这一奏折中,两次出现“民法”一词。同年,在由张百熙拟订、并由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大学堂章程》(但这个章程实际上没有能够执行)中,清政府对京师大学堂速成科仕学馆各学年课程作了明确安排,规定第三学年在“政治学”科目下开设“国法、民法、商法”三门课程,这是清政府的官方文件中又一次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法”一词。可以说,清政府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在语词上以及法学学科体系的课程设置上,接受了西方意义的“民法”之说。1907年,清政府的官僚阶层就是否要制定民律、具体由哪个部门来制定、西方民法的竟源考流、中国传统典章中的民法资源、民商分立抑或民商合一等问题,以及民事习惯的调查等等,展开讨论、争论或落实具体的措施。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20世纪初的10年里,当民间和学者频繁地引进、介绍、翻译西方的民法概念、民法理论、呼吁编订民法典、并熟练地运用“民法”一词之际,清政府却在语词上向传统倒退,弃“民法”不用,改用“民律”,清政府民政部最后奏请编订的是“民律”,清政府批示修订的也是“民律”。这不单纯是一个名词上的变化,它凸现出中国固有法观念强大的惯性,凸现出社会转型时期深刻的新旧法观念的冲突,也折射出20世纪初中国法律制度变革的迂回复杂而又艰难曲折的一面。由此,再次导致“民律”与“民法”并用的现象,并持续了将近三十年。这一时期,《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律草案》都以“民律”命名,而本来在观念上已接受了西方“民法”理论的学术界,受官方的影响,各种民法学教材中也多有“民律”与“民法”交替使用的情形。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会议作出决议:“一切法律概须由政治会议议决。凡经政治会议议决之法律概称曰某‘法’。”这样,一方面一揽子解决了各部门法在法名上的称谓问题,另一方面也杜绝了“民律”、“民法”混用的现象。
高 尚
人民法院报2006-04-10
“民法”一词我国古已有之。据有关文献记载:“民法之称,见于尚书孔传”,但在该词语出现后的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既没有部门法意义上的“民法”,更不存在私权观念上的“民法”。检视中华法系的历代律典,充其量只存在调整户婚田宅钱债等民事生活内容的零星法条,并不存在现代法学和部门法意义上“民法”。
现代意义上“民法”一词源自罗马法,它在观念形态上蕴涵着保护私权和对民众自治的承认,最终直指对“正义”价值目标的追求;在形式理性上,它强调一种协调一致的逻辑性,是由特定的基本概念、术语和规范而组成的一种法典化的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民法”最早是在19世纪末才在中国初现端倪的,20世纪初则频繁地出现在学术界的著述和官方的典籍档案之中了。
中文文献中最早使用现代意义“民法”一词的,见于1887年黄遵宪所著的《日本国志》一书,其中有云:“私诉以赔偿归还赃物为主,照依民法听被害者自便。”十余年后,康有为为鼓吹变法,曾数次提到要修订民法。1897年,在中国的知识界普遍地对西方系统的法学知识和法律体系极为陌生的情形下,梁启超认真地对待包含了“民律”在内共有六部法典的《法国律例》一书,并将《法国律例》列入他所主持的湖南时务学堂《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中,与学生共同研讨。通过对“民律”的研究,梁启超已不再在概念上将“民律”与“民法”并列而论,对近现代意义上的部门法划分,已有了较准确的理解与把握,对现代意义上的“民法”一词,至少在概念上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术语表达上也是准确的。
如果说,至19世纪末,梁启超还主要地是从概念和术语上把握、论及现代意义的“民法”的话,那么,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则开始体系化地、具体地向国内介绍和引入日本民法、日本民法学、日本民法学著作。留日学生于1900年12月创办了以“研究实学”、“重视责任”为宗旨的《译书汇编》杂志,1901年7月出版的第七期的《译书汇编》上,登载了日本学者樋山广业的《现行法制大意》一文,该文不但对现代民法学体系作了系统介绍,而且,私法类下分两章,第一章为民法,“民法”下辖人及法人、物、物权、债权、亲族、相续六节,各节下又分有细目,较为详尽地介绍了西方的民法结构体例和基本内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毕业于美国芝加哥伊利拿大学法科的胡贻榖于1902年翻译了英国人甘格士所著《History?of?Socialism》一书,并将其中文译名定为《泰西民法志》,这是我国学术界正式引入的第一部西方民法学专著,该书在内容上介绍了罗马法的历史,法国、英国等西欧民法内容、立法旨意、活动及法学家的学说等。由此,民法学的传播在中国全面展开。1903年在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法政辞书中,开始对民法和民法学中的重要概念逐条解释,其中认为“规定私人之相互关系者,谓之民法”。此后,《法兰西民法正文》则让中国法政学界真正地接触和面对大陆法系最具代表性的、差不多也是当时最新的民法典原文。
如果说,19世纪末,极少数的知识精英引入了西方“民法”概念的话,那么,20世纪初的头10年里,中国的法政学术界则以飞一般的速度从理论体系到法典本身“恶补”现代“民法”一课,并呼吁制定中国自己的民法典。
所有上述的努力,基本地都还局限于民间的或学术的立场。官方对待现代“民法”的认识和态度,在1902年没有先兆地突然间明朗起来。1901年清政府的上谕诏书和封疆大吏的条陈奏张中,均无只言片语涉及“民法”,但1902年在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联名保举沈家本主持修订法律的奏议中,明确论及现代意义上的民法问题:“近来日本法律学分门别类,考究亦精,而民法一门,最为西人所叹服。……亦可由出使日本大臣,访求该国法律博士,取其专精民法、刑法者各一人,一并延请来华,协同编译。”这一奏折中,两次出现“民法”一词。同年,在由张百熙拟订、并由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大学堂章程》(但这个章程实际上没有能够执行)中,清政府对京师大学堂速成科仕学馆各学年课程作了明确安排,规定第三学年在“政治学”科目下开设“国法、民法、商法”三门课程,这是清政府的官方文件中又一次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法”一词。可以说,清政府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在语词上以及法学学科体系的课程设置上,接受了西方意义的“民法”之说。1907年,清政府的官僚阶层就是否要制定民律、具体由哪个部门来制定、西方民法的竟源考流、中国传统典章中的民法资源、民商分立抑或民商合一等问题,以及民事习惯的调查等等,展开讨论、争论或落实具体的措施。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20世纪初的10年里,当民间和学者频繁地引进、介绍、翻译西方的民法概念、民法理论、呼吁编订民法典、并熟练地运用“民法”一词之际,清政府却在语词上向传统倒退,弃“民法”不用,改用“民律”,清政府民政部最后奏请编订的是“民律”,清政府批示修订的也是“民律”。这不单纯是一个名词上的变化,它凸现出中国固有法观念强大的惯性,凸现出社会转型时期深刻的新旧法观念的冲突,也折射出20世纪初中国法律制度变革的迂回复杂而又艰难曲折的一面。由此,再次导致“民律”与“民法”并用的现象,并持续了将近三十年。这一时期,《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律草案》都以“民律”命名,而本来在观念上已接受了西方“民法”理论的学术界,受官方的影响,各种民法学教材中也多有“民律”与“民法”交替使用的情形。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会议作出决议:“一切法律概须由政治会议议决。凡经政治会议议决之法律概称曰某‘法’。”这样,一方面一揽子解决了各部门法在法名上的称谓问题,另一方面也杜绝了“民律”、“民法”混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