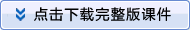果戈理(1809-1852)
果戈理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自然派的奠基人。当果戈理以《钦差大臣》和《死魂灵》而享誉文坛之时,一批青年作家纷纷仿效之,一时间形成了以《祖国纪事》和《现代人》杂志为阵地的“果戈理学派”,而敌对派则把他们污蔑为歪曲现实的“自然派”。别林斯基接过这一称号,系统阐述了“自然派”的创作特征和它与解放运动的密切关系。在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的共同推动下,掀起了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高潮。
一、生平和创作:
果戈理1809年3月19日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德县索罗庆采镇一个地主家庭。其父酷爱戏剧,且善创作,对果戈理走上文学道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果戈理12岁就读于涅仁高级中学。在此深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迷恋普希金,雷列耶夫的自由诗,对专制、农奴制的不满亦由此滋生。19岁时,果戈理独自到彼得堡谋生。他当小公务员,一度穷困潦倒。这为他日后写小人物奠定了生活基础。
果戈理是在普希金和别林斯基的影响下走上文学道路的,并以此为终身职业。他的早期创作是属于浪漫主义的。他的成名作《狄康卡近乡夜话》(一、二部,1831-32),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这部作品包括八部中短篇小说,以生动幽默的笔触描写了乌克兰人民的生活和习俗,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1835年,小说集《密尔格拉德》和《小品集》问世,标志着果戈理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此后他又把《小品集》中的《涅瓦大街》、《肖像》和《狂人日记》三篇小说与后来创作的《鼻子》、《马车》、《外套》等作品合成一集,取名为《彼得堡故事集》。
在《密尔格拉德》和《彼得堡故事集》中,果戈理主要塑造了两类现实主义的人物形象,
即旧式地主和小人物形象。《旧式地主》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弗洛维奇争吵的故事》,都是写旧式地主的,他含着泪,写出了当代地主们“动物性的、丑恶的、谑画的生活的全部庸俗和卑污”。《密尔格拉德》中的历史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也写得十分出色。这篇小说以十七世纪乌克兰带有传奇性的民族英雄布尔巴为主人公,描写他与波兰侵略者的浴血斗争,以豪放的笔调表现了他坚强的意志和为国献身的崇高精神,突出了爱国主义的主题。
写小人物形象的作品有《狂人日记》和《外套》。其中《外套》最为著名,主人公叫巴施马奇金,意为“鞋”,象征了主人公屈辱的社会地位。小说的故事很简单,在寒冷的冬天里,巴施马奇金的破外套已无法御寒,因此为做一件新外套而费尽心机,当新外套到手后,又意外地被强盗抢去。巴施马奇金求告无门,被长官训斥一顿之后,一命呜呼。死去的巴施马奇金阴魂不散,常在涅瓦大桥上游荡,扒下达官贵人的外套以示报复。这篇小说不仅写出了处于官僚等级制度最底层的小人物们生活的穷困,更主要的是写出了他们精神的扭曲。在官僚等级制度下的重压下,他们丧失了起码的自尊和应有的创造力,成了奴性十足的可怜虫和麻木无用的抄写匠。
与小人物形象的创始者普希金所写的《驿站长》相比,《外套》把小人物生活的场景从荒远的驿站搬到了彼得堡,从而更突出了小人物在官僚制度下的底层地位;在对小人物精神世界的描写上,《外套》作了更为充分的展示和深入的挖掘,从而让读者不仅同情他们的不幸,也为他们的不争而痛惜,鲁迅先生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恰好可以作为人们对巴施马奇金感受的注脚;在表现手法上更体现了果戈理本人的特色。作者用喜剧手法来写悲剧,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包含了喜剧的因素,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会因一系列喜剧化的细节掩面而笑,但读完全篇却不禁要为主人公悲惨的遭遇洒下一掬同情的泪水,从而读者在悲喜交集的阅读过程中获得更丰富的审美感受。
果戈理对黑暗现实的有力批判和尖锐讽刺招致了反动阵营的攻击。这时,别林斯基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为果戈理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对他的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把这两部作品称作是“现实的诗”,认为它们足以使果戈理“站在普希金所遗下的位置上面”,成为“文坛的盟主,诗人的魁首”。
果戈理自幼酷爱戏剧,三十年代中期他终于以一部讽刺喜剧《钦差大臣》(1836)为自己在俄国戏剧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钦差大臣》讲的是一个错认钦差的故事。京城小官吏赫列斯达可夫被某市的官员当作了微服私访的钦差,从而引出了一系列喜剧性情节。作者借错认钦差这一偶然事件,目的在于把一切俄国的坏东西收集在一起,一下子把这一切嘲笑个够。因此,在剧中我们看到的是曾经骗过三个省长的市长;用自然疗法对待病人的慈善院长;极尽特务之职、陷害进步教师的督学;分不清真假状子的法官;私拆信件的邮政局长;欺压百姓“随便用拳头揍人”的警察署长。错认钦差虽是偶然事件,但其中却包含着必然性,即各级官僚的恶行败德导致他们害怕受到正义的处罚,因此在惶惑之中才会认假为真,从而反映了俄国官场腐败的普遍性,使作品具有了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
,钦差大臣》是俄国现实主义戏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即把以往无思想深度的笑剧和传奇剧发展为了具有深刻社会内容的政治讽刺剧,从而使俄国戏剧在当时的世界剧坛占有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作者充分发挥了喜剧特有的笑的功能,虽然满台都是反面人物,但观众正义的笑声就是对专制社会的官僚制度最无情的批判,就如剧中的市长所说的“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
尖锐犀利的讽刺喜剧激怒了专制统治者,果戈理遭到了恶意的攻击和诽谤,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果戈理避居罗马,潜心创作他构思已久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终于在1841年脱稿,并于次年出版。
,死魂灵》第一部的出版受到进步文学阵营的高度评价,认为它是俄国“文坛上划时代的巨著”,是一部“高出于俄国过去以及现在一切作品之上的”,“既是民族的,同时又是高度艺术的作品”,它“巩固了新学派的胜利,断然解决了我们时代的文学问题”。同时,这部杰作也遭到了反动阵营更猛烈的攻击,他们把果戈理称为“俄国的敌人”,要“把他戴上镣铐送到西伯利亚去。”
果戈理并非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对地主的惋惜和同情,以及对封建家长制的美化,加之他侨居国外之后,与斯拉夫派关系密切,远离进步阵营和祖国现实,导致他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与反动阵营的斗争中,步步退让,最后甚至站到了维护专制农奴制的立场上。在《〈死魂灵〉第一部第二版序文》(1946)中,他说这部作品“有许多不确之处”,“混入许多错误和妄断,致使这书的每一页上,无不应加若干修改”,并承诺要在《死魂灵》的第二部里写出“好的人物和性格”。1847年出版的《与友人书简选》更是果戈理思想的大倒退,他甚至为沙皇的反动统治寻找理论根据,提倡宗教感情、道德修养和封建复古。别林斯基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写了公开信《给果戈理的一封信》(1847),对他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指出,人民可以宽恕作家写一部拙劣的书,但不能宽恕作家写一本有毒素的书。
1842以后,果戈理按照既定的创作计划,投入了《死魂灵》第二部的创作,但因为严重背离俄国现实,连他自己都怀疑其真实性,虽一再改写和重写,终不能令自己满意,1845年,他把写出的初稿付之一炬。后来他又写了第二稿,但第二稿也被他在临终前全烧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二卷的一些断简残篇,是根据清理果戈理遗物时在五个笔记本里发现的草稿整理而成的。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力图写出理想化的地主官吏形象,并试图调和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幻想地主与农民亲密合作、共同富裕,为俄国社会指明出路。其中所写的地主们在勤奋地经营庄园,发家致富,好官吏在教导农奴主们发家致富以后应如何关心国家、有益社会;乞乞可夫虽然还在犯罪,但他的良心却在感到不安,甚至会哭哭啼啼;而总督则是一个愤世嫉俗、对官场腐败恨之入骨的正义之人,他虽然意识到他手下没有好官员,但还是教导他们要为官清廉,一心奉公。对腐朽没落的官僚地主阶级的刻意美化,无疑背离了作家曾遵循的现实主义原则。在此,他的政治立场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之间产生了极大的矛盾,而他烧掉书稿也就是必然的,这也证明了,果戈理“作为思想家会误入歧途,但作为艺术家,他始终是忠于自己的”。(陈殿兴《死魂灵》译本序)
果戈理的结局是悲剧性的,这悲剧虽有主观的原因,但根本原因却在于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的:“差不多在每个俄罗斯作家的面前我们都可以对旧俄国宣布最严厉的、革命的诅咒,因为他们不是被它杀害,便是被它引上了错误的道路。”果戈理正是属于后者。
果戈理的创作虽然因其与进步力量的背离而大打折扣,但纵观他的全部创作,其功绩是巨大的,这表现在:首先,在果戈理之前,还没有哪一位作家对俄国的专制、农奴制及其官僚制度进行了如此深刻而全面的揭露与批判,他的笔触从破败的乡村到灰暗的城市,从小公务员蜗居的斗室到官僚们争逐的官场,点染出一个个没落地主的形象,勾画出官僚们丑恶的灵魂。其次,在小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果戈理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他在俄国官僚制度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写出了小人物生活的贫寒和他们灵魂的扭曲,并极大地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批后来者,难怪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外套》情有独钟,认为“我们都是来自《外套》”。再次,果戈理作品的突出特色是“含泪的微笑”,《外套》表面的幽默掩盖不住作者内心的苦痛,而《死魂灵》在对地主们尖刻的讽刺之中,也隐约可见作者的泪痕悲色。
二、《死魂灵》第一部
,死魂灵》第一部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第一部具有高度思想艺术水平的长篇小说。在叙事方法上作者没有采取平铺直叙的方式,而是故意给我们制造了一个悬念,即从乞乞可夫来到N市写起,遍访社会名流,并初步介绍了书中的一些重要人物,而乞乞可夫的来历却没有交待,而是留在了结尾第十一章揭开谜底。除了开篇和结尾这两章之外,小说的其余章节分成了两大部分,即第二至第六章乞乞可夫分别到五个地主家购买死魂灵,从而充分地展示了俄国地主的生活状态,刻画了五个性格鲜明的地主形象;第七章至第十章写乞乞可夫回到N市办过户手续,在此,乞乞可夫的神秘行径引起了众人的猜疑,以致舆论哗然,乞乞可夫不得不溜之大吉。在这一部分,作者用了较大篇幅来反映外省社会的生活,揭露了官僚集团的腐败和上流社会的庸俗。
乞乞可夫是俄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从小地主、小官吏过渡到新兴资产者的典型。他既精于官场应付和与地主打交道的世故伎俩,又有资产阶级投机钻营、圆滑奸诈的特点。他从父亲那里接受的是只认金钱不讲道德,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家教,即“要博得你的上司的欢心”;还要“省钱,积钱,钱是永远不会抛弃你的,只要有钱,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什么都办得到”。他初入仕途,曾一度得手。为了得到科长的职位,他以前所未有的“克己和忍耐”,对上司百般献媚,并追求上司的麻脸女儿,然而一旦职位到手,即把上司和未婚妻弃置一边。为了得到税务局里的一个重要职位,他装出少有的“正直和廉洁”,终得上司赏识而得遂心愿,并利用职权,走私贩私,大发横财,但东窗事发,功亏一篑。但他从不认输,跌倒了再爬起来,开始“新的尝试”。于是他又到法院去当了代书人,在办理农奴抵押业务之时,受到启发,想到趁新的人口调查到来之前,买进死农奴,再到救济局去抵押,转眼就可以发大财。于是,他就奔赴乡村,把他的计划付诸实施。
在购买死魂灵的过程中,乞乞可夫的圆滑和奸诈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在愚蠢的玛尼罗夫面前,他可以变得比玛尼罗夫还文雅,而对科罗皤契加则是软硬兼施,与无赖罗士特莱夫相处他则小心谨慎,对梭巴开维支他则硬碰硬,直来直去,而对泼留希金这样一个吝啬鬼,他只需装得比对方还傻,情愿负担死农奴的人头税,以致泼留希金对他感激涕泠。
在乞乞可夫身上,既有地主贵族剥削、寄生、欺压人民的特征,又有资产阶级投机钻营、圆滑狡诈、唯利是图的特征。作为资产者,乞乞可夫的意义不仅仅在俄国。别林斯基说,乞乞可夫之流活动在不同的国家里,只不过穿着别的衣服罢了,“在法国和英国,他们不买进死魂灵,而是在自由的议会选举中收买活魂灵!整个差别只在文化上,却不在本质上。”
乞乞可夫拜访的第一个地主是玛尼洛夫。他热情、好客,重友谊、爱学问,常常沉浸在幻想之中,且懒惰成性。一本书看了两年才翻到十四页。他虽广有财产,但却疏于管理,庄园里满目荒芜。玛尼洛夫曾与乞乞科夫在宴会上有一面之交,但当他见到乞乞科夫的时候,却像见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长时间地与其握手。乞乞科夫也逢场作戏,看着彼此泪光闪闪的眼睛。当乞乞科夫表明来意,要买死魂灵,玛尼洛夫出于“友谊”,如数奉送,但直到乞乞科夫已经走了,他也没搞清乞乞科夫为什么要买死魂灵。
乞乞科夫本要去拜访梭巴开维支,但在去梭巴开维支家的路上,顺便到了女地主科罗皤契加的家,他看到这个女地主的家颇为寒酸,因此就开门见山,道明来意,并说他收购了她的死魂灵可使她免交人头税。女地主既感兴趣又怕上当,但最终还是以15卢布的价格卖给了乞乞科夫18个死魂灵。
接着,他又遇到了罗士特莱夫。来到罗士特莱夫的家,看到的是各式各样的狗,罗士特莱夫在狗们中间完全像家庭里的父亲一样。乞乞科夫对罗士特莱夫说要买死魂灵,而罗士特莱夫则硬要乞乞科夫说明买死魂灵的用途,并非要乞乞科夫陪他赌钱、下棋。乞乞科夫被缠得无法脱身,只好放弃了做买卖的念头,趁法院院长来找罗士特莱夫的机会,偷偷溜走了。
乞乞科夫终于来到了梭巴开维支的家,相见之下,乞乞科夫仿佛看到了一头中等大小的熊。这只“熊”贪图口腹之欲,行为粗野,对待农奴十分残忍,但又工于心计,做事精明。当乞乞科夫稍表来意,梭巴开维支即心领神会,竟然每个死魂灵要价100卢布,最后的成效价是两个半卢布一个。
乞乞科夫最后拜访的地主叫泼留希金,他拥有近千个农奴,但极为贪婪吝啬。他的衣着像个叫花子,常把碎布、铁钉之类的破烂捡回他的“仓库”里。仓库里的东西都已发霉变质,散发出阵阵异味。这样的人当然不愿为死去的农奴付人头税,因此当乞乞科夫表示愿购买死魂灵时,他感激不尽,竟破天荒地招待了乞乞科夫一次。
泼留希金与西欧文学中常见的高利贷者形象不同,高利贷者聚敛的财富主要是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而泼留希金聚敛的则主要是实物形式的财产,他把它们长期存放在仓库里,任其腐烂变质,使他的财产时时都在贬值。这表明他在聚财的同时又在浪费财产。从泼留希金形同乞丐的外表和霉气冲天的仓房,作者一再向我们表明地主阶段才是真正的死魂灵,作为统治阶级,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阶级基础,他们已经腐朽不堪了,那么这个制度的末日也已经不远了。
在谈到这本书的写作特点时,果戈理说过:“人们在分析我的某些方面时有许多说法,可是对我的主要特点并没有抓住。这个特点只有普希金一人抓到了。他总是对我说,还没有一个作家有这种才华——能把生活中的庸俗现象显示得这样鲜明,能把庸俗人的庸俗生活这样有力地勾画出来,使一切容易滑过的琐事显著地呈现在大家眼前……这个特点在全书中表现得更加有力。并不是因为它揭露了俄国的什么伤疤或病痛,也不是因为它描绘了邪恶逞凶、善良受苦这样一些震撼人心的画面而使俄国感到惊恐,在俄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丝毫不是。我的主人公们根本不是恶棍;对他们中间的任何人,我只须增加一条优点,读者就会容忍他们。可是他们的庸俗加到一起却使读者感到惊恐。”(转引自陈殿兴《死魂灵》译者序)
在这段话里,果戈理认为自己的特点是“能把庸俗人的庸俗生活有力地勾画出来,使一切容易滑过的琐事显著地呈现在大家眼前”。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是夸张。谈到夸张,人们容易把它与浪漫主义联系起来,但浪漫主义的夸张往往是带有主观幻想性质的,而果戈理的夸张则是在尊重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把生活中的事件或人物某些可笑的方面加以放大,使其更为显著而已。这样就有了玛尼罗夫的握手时间之长足令朋友厌烦,罗士特莱夫的与狗为伍,梭巴开维支的由内到外都堪似狗熊,泼留希金的与叫化子别无二致。
讽刺是《死魂灵》的突出特点,鲁迅称其为“含泪的笑”,是“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按照果戈理自己的说法是,“由分明的笑,和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来历览一切壮大活动的人生。”,笑”,也就是讽刺,本是喜剧常用的表现手法,但在《死魂灵》中,这笑却常常受到果戈理不分明的泪的侵蚀,也就和他的世界观挂上了钩,含泪的笑恰当地表达了作者的世界观与艺术表现之间的矛盾性。分明的笑,即以夸张的手法,典型化的细节,个性化的肖像描写等,突出人物外表和内心的矛盾,刻划人物的性格;不分明的泪则是作者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对地主的无聊和堕落,表示同情和哀惋,并对理想的地主社会充满幻想。鲁迅先生说:《死魂灵》“一共写了五个地主,讽刺固多,实则除了一个老太婆和吝啬鬼泼留希金外,都各有可爱之处。”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死魂灵》所引发的笑是健康的,有益的,且绝不会有泪;在我们的时代已很难找到果戈理的同道,不会再有人陪着他黯然神伤,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健康的笑,在被笑的一方面是悲哀,所以果戈理的‘含泪的笑’,倘传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读者的脸上,也就成为健康;这是《死魂灵》的伟大之处,也正是作者的悲哀之处。”
用典型化的环境描写来烘托人物的性格。如玛尼罗夫满布灰尘的家和破败的田园与他的懒惰成性;罗士特莱夫的狗舍与他的狗性;梭巴开维支家粗壮的家具与他的熊性;泼留希金发霉的仓库和无光的土屋与他的贪婪和吝啬。人物和环境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表明果戈理深得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