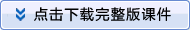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作家。他虽然对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对人性的丑恶、可怖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但他对宗教的狂热鼓吹,对人生的绝望态度都曾引起激烈的争议。但无论来自哪个方面的评价,都对其艺术天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高尔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是无可辩驳的,就描绘的能力而言,他的才华也许只有莎士比亚可以与之并列,……”他不仅以现实主义的精细笔法描绘了俄国城市贫民的生活,同时更注重对人的心灵特别是人的深层意识的挖掘,而在小说的叙事方式上创用“复调小说”更使他在同时代作家中独树一帜,并对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生平与创作:
1821年11月1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莫斯科,其父为贫民医院医生,薄有田产,后取得贵族身份。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住医院附近,为贫穷、疾病所包围,使他对当时平民以至贫民的生活多有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幼患有癫痫病,为顽疾所困,他的心灵以及创作都受到了直接的影响。
1837年,他遵父命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但生活贫苦,有时口袋里连饮一口茶的钱都没有。他因爱好文学而致学业成绩不佳。六年后到工程局绘图处工作,但一年后即辞职而专事文学创作。
四十年代的俄国文坛正是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大行其道的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其影响,以一部书信体的中篇小说《穷人》(1846)荣登文坛,涅克拉索夫惊呼“新的果戈理出现了”,并将此作收入他所编的自然派作品集《彼得堡文集》第二集。这部作品奠定了陀氏作为自然派重要作家的地位。
,穷人》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但却是对俄国文学中写小人物传统的继承和开拓。他不仅继承了普希金、果戈理对小人物悲惨生活和精神屈辱的描写,而且写出了小人物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微弱的反抗。这部小说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深度,得益于作家所采用的书信体形式。作为身处官僚等级制度底层的男主人公杰符什金,在公开场合,当着上司的面,他是不敢表示出丝毫的不满的,这不满只能藏在心里,诉诸笔端,对他心爱的人诉说。从这些发自心底的言说中,读者窥见了小人物心灵的一角,这是在普希金和果戈理的小说中都未得到充分表现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小人物的爱情悲剧写得极为动人。杰符什金是一个干了三十年抄写工作的小公务员,瓦莲卡是身遭不幸、几乎沦落风尘的年轻姑娘。身处底层的命运使两个小人物同病相怜,处事谨慎的杰符什金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爱着瓦莲卡,他怕招惹是非,不敢和她稍有亲近,只能在礼拜天作弥撒时或者在瓦莲卡撩开窗帘的刹那一睹她的芳容。小公务员虽然生活贫苦,但必须有外套和皮靴来维持起码的体面,然而,为了接济贫困中的瓦莲卡,他竟要卖掉外套,其牺牲精神足令世人感动。
因为处身于社会的底层,杰符什金性情敏感,十分看重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他不认为自己是别人的累赘,因为“这口面包是我自己的,它是我劳动挣来的,是合法的”;他不认为自己天生卑贱,也不认为抄抄写写是卑贱的工作,觉得自己“也有一颗与别人一样的心”,“我有良心和思想”;他以自己在工作而自豪,“因为我在工作,我在流汗嘛”。从这些言语中透露出小人物的“自尊”和他们要做“人”的强烈意识,他们虽然贫穷,但“贫非罪”。
杰符什金的反抗只是停留在他自己的意识中,至多是讲给瓦莲卡听的,所以他的反抗仍然是微弱的,是“跪着造反”。而且他无力承受任何重大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只能任凭命运的捉弄。所以当他心爱的瓦莲卡被迫嫁给地主贝科夫时,他发出了悲惨的哀号。
,穷人》的成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对小人物内心世界中的软弱与反抗都作了充分的揭示,因此预示了他未来的一个创作方向,即对人的心灵奥秘的揭示。果然,在他的下一部作品《双重人格--高略德金先生的奇遇》(1846)中,他就对主人公极化的内心世界作了更进一步的揭示。高略德金本是一个性格懦弱、胆小怕事的小公务员,失业的恐惧使他处事谨慎,唯恐一不小心又落入穷困潦倒的境地。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他也不是没有想过靠不道德的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但他却没有勇气这样做。此时,一个与他相貌相同的小高略德金出现在他的幻想里,这是一个不讲道德,不择手段,巧取豪夺的人,主人公对他既恐惧又向往,在道德与非道德之间高略德金终未找到出路,因此而导致疯狂。
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写过《女房东》(1847)、《白夜》(1848)等中篇小说,其中浓重的幻想色彩和对人物病态心理和人格分裂的描写,显示出作家创作上的独特之处,其主观倾向与神秘色彩导致别林斯基等人对他的批评,并最终导致双方的分裂。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文学不应该局限于具体的社会使命,而应更重视想象和幻想,他把他的现实主义称为“幻想的现实主义”。此时,他与别林斯基等激进民主派的分歧还停留在文学观念上,他仍然醉心于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赞成社会改革,解放农奴,为此,他参加了进步学生团体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在一次集会活动中与小组成员一起被捕,加给他的罪名是在会上朗读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为此他被削去贵族身份,判处死刑,只是在临刑前才由尼古拉一世下旨改判为四年苦役加期满后在边疆服兵役。这样,自1849年被捕至1859年回到彼得堡,他中断文学创作达十年之久。
这段生活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抛弃了从前的思想信仰,从《圣经》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认为只有基督教的博爱忍从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正确途径。这一思想是他在此后的作品中所竭力宣扬的,也是他与进步的民主主义者论战的立足点。对他的创作来讲,这十年使他的生活阅历更为丰富,素材积累更为丰厚,对人性的思考也更为深入。而苦役和兵役生活对健康的损害也使他的癫痫病日益频繁发作,这也多少给他的作品涂上了一层神经质的色彩。
六十年代初期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创作了长篇小说《死屋手记》(1861-62),书中假借一贵族流放犯之口,讲述了狱中十年的见闻。书中描写了狱中酷吏用惨无人道的刑罚折磨犯人的描写,从而对专权社会提出了强烈的控诉,尤其是作者认为陷身于牢狱的人本可能是一个杰出的个性,但却被白白地牺牲了。同时,作品也充分展示了人性之恶,如狱吏热列比亚特尼科夫的变态施虐狂;“像人一般大的蜘蛛”、兽性十足、专以虐杀儿童为乐的逃后卡津;贪恋肉体快乐的贵族青年A等。作者借这些形象强调了“恶”是人性中固有的东西,认为“刽子手的特性存在于每个现代人的胚胎之中”。这一观念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中的瓦尔科夫斯基身上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和哥哥先后病逝,此前他曾与哥哥共同经营杂志,杂志停刊之后,欠债颇多。陀思妥耶夫斯基担负起了抚养哥哥的妻儿之责,此时债主乘人之危,上门逼债,无奈,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得将全集版权出卖。出版商泰罗夫斯基又限他半年内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进行《罪与罚》的创作,无暇写另外的作品。他铤而走险,到赌场中一试身手,然而输得一塌糊涂。此番经历激起了他的灵感,遂请了速记员安娜,用二十六天完成了长篇小说《赌徒》。1867年他与安娜结婚,避居国外,但赌性不改。1871年回国,债主们又纷纷登门,多亏安娜与之周旋,陀思妥耶夫斯基得以全力投入创作,先后写出了《白痴》(1868)、《群魔》(1871)、《少年》(1874)、《卡拉玛佐夫兄弟》(1880)等小说。
二.重要长篇小说
,罪与罚》是一部给作者带来世界性声誉的作品。小说的素材来自当时《时代》杂志连载的一个案例,一位法国青年拉谢尼耶夫因杀害了一个老年妇女而入狱。小说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城市里贫穷的知识分子,他只身在彼得堡读书,但因为穷,不得不中途缀学,为了维持生计,而向高利贷者借钱。这时,他的妹妹杜尼亚为了维持家庭的体面,特别是为了哥哥的前途,同意嫁给一个她并不爱的有钱的自私自利的恶棍卢仁,面临着变相卖淫的境遇。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铤而走险,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太,又把恰巧来到现场的老太太的妹妹杀死。杀人之后,拉斯柯尔尼科夫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不断地受到道德和良心的惩罚,最后在亲友的感召下,自动投案自首,并在流放过程中皈依了上帝。
作为一部社会批判小说,《罪与罚》揭露了在沙皇统治下,城市贫民的无路可走。除了写拉斯柯尔尼科夫,作品还写了马美拉多夫一家。事实上,在最初的构思中,马美拉多夫的故事是小说的主体,只是在创作过程中,其重心才移向拉斯柯尔尼科夫,但马美拉多夫的故事仍然具有独立的社会批判价值。马美拉多夫经常处于失业状态,一家人处于极度贫困的之中。在生活重压下,马美拉多夫的妻子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对她信奉的上帝都失去了信心:“上帝啊!难道就没有公道了吗!不来保护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人,你去保护谁呢?……”。她意识到,上帝虽然“是慈悲的,可是对我们却不!”为了不使尚待抚养的孩子们饿死,马美拉多夫的大女儿索尼亚不得不去出卖肉体。最终,马美拉多夫在一次醉酒后,遇车祸而死,他的家人连安葬他的棺材都买不起。通过对城市贫民的描写,作者揭示出,在那样的社会,穷人或者像马美拉多夫那样如猪狗一样死去,或者像拉斯柯尔尼科夫那样铤而走险,或者像索尼亚那样出卖自己的肉体。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原因除了为生活所迫之外,同时受到超人哲学的影响。主人公将人分为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人,而他想从一个平凡的人,变成一个不平凡的人,即拿破仑式的人,做人类的统治者或者做人类的恩人,因此他就去杀人。通过这样的描写,作者批判了超人哲学。但是,犯罪之后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并没有成为超人,而是陷入了深重的精神危机,受到了双重的惩罚。一方面,他因触犯刑律而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另一方面,他经受着良心的惩罚,精神几近崩溃。他非但没有成为超人,反而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所累,不得不时时提防,处处躲避,再也不能与朋友亲人沟通,只能独自承受内心的痛苦,以致无法解脱。引导拉斯柯尔尼科夫走出精神地狱的是妓女索尼亚,索尼亚并没有像她的继母卡杰林娜那样由信仰上帝而最终背弃上帝,她虽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被迫以卖淫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但她却始终怀着对上帝的坚定信仰,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屈辱和苦难,成为博爱和宽恕精神的化身。同时她也执着地用这种精神去感化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索尼亚的面前,拉斯柯尔尼科夫深感自己的渺小,他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对她顶礼膜拜。在此,拉斯柯尔尼科夫由对忍辱负重精神的欣赏和崇拜,进而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决心以受难来赎罪,在苦难中洗涤自己的灵魂,最终走向上帝。这种思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归来之后所持政治主张的艺术再现。在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争论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持与斯拉夫派相近的“根基论”,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脱离人民的根基,应从人民的根基中汲取道德的理想,而人民自古以来是信仰基督和沙皇的,这种信仰有助于现实社会矛盾的解决,即实现人民和贵族之间的和解。在《罪与罚》中,作家也许想表达这样的思想,即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一样,统治者也是犯了罪的,如果他们也能像拉斯柯尔尼科夫那样真诚地赎罪,而苦难中的人民都能像索尼亚那样坚忍地忍耐并宽恕造成社会罪恶的人,那么双方终会实现和解,那样,这个社会就会是一个充满了博爱精神的社会。显然,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在此也暴露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保守、甚至反动。
《白痴》(1868)以娜斯塔西娅?费利波夫娜为中心展开情节。开篇写梅思金公爵从瑞士疗养地回国途中,在火车上遇到富商之子罗果静,知罗果静正在疯狂地追求娜斯塔西娅,从而引起了公爵对娜斯塔西娅的关心。此后是一系列过渡性描写,读者从中了解到娜斯塔西娅是托茨基的养女,长大后又成了托茨基的情妇,现在托茨基为了自己考虑,决定与叶潘钦将军做一次交易,把娜斯塔西娅嫁给将军的秘书伊沃尔金。时逢娜斯塔西娅的生日晚会,情节在此跃上高潮,所有的相关人物都到场祝贺,而娜斯塔西娅却借此机会让每个人当众讲一件自己做过的坏事,以此来羞辱这些所谓的体面人。晚会中间,罗果静带着十万卢布来买娜斯塔西娅,公爵极力劝阻,娜斯塔西娅将十万卢布投入壁炉,随罗果静而去。娜斯塔西娅爱公爵,并曾与公爵共入教堂,结为连理,但旋即又投入了罗果静的怀抱,因她自感深陷堕落的深渊而无力自拔,决计以自虐的方式求得解脱,最终她为罗果静所害,走完了其悲剧性的一生。
梅思金公爵是作者塑造的理想人物,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作者在给伊万诺娃的信中写道,《白痴》的“主要思想是描绘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美是理想,世界上只有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基督。”可见,陀氏是把梅思金公爵当作基督来描绘的。但是,即使基督再世,也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罪恶。梅思金虽然心地纯洁、善良,以爱对人,但亦无助于事,他非但不能拯救他人于水火,连他自己也救不了。面对娜西塔西娅的无辜被害,他只能陷入更深的悲哀之中,成了真正的白痴。这一形象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救世思想的软弱和失败。
,群魔》(1871-72)所引起的争论最激烈也最长久,至今评论界仍有不同的看法。由于小说对革命者的丑化,把他们写成了只会杀人放火,搞恐怖活动的极端主义者,因而被认为是对七十年代初俄国革命运动的攻击。但作品也对官僚和贵族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并塑造了斯塔夫罗金这样具有双重性格的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
,卡拉玛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长篇,被认为是他最成熟的作品。因为在这部作品中,以往作品中高略德金式的双重性格、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超人思想、索尼亚和思什金公爵的东正教观念都通过对卡拉玛佐夫这一“偶合家庭”的描写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对现实的真实描绘、对社会政治、哲学、伦理、道德等问题的揭示、对俄国前途与命运的思考都汇聚一起,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史诗的品格。
老卡拉玛佐夫是高尔基所说的“卡拉玛佐夫气质”的代表,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卑鄙无耻、自私自利、野蛮残暴、放肆淫逸、腐化堕落等品质。他出身贫贱,曾为食客,从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丑角而逐步发迹,积聚了十万卢布的家财。他的两次婚姻都与财产和私欲有关,丧妻后竟发展到无恶不作,以致奸淫疯女,生下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由仆人收养,长大后成了他的厨师。
长子德米特里是又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在他的身上,既有抹不掉的“卡拉玛佐夫气质”,也有心向上帝、赎罪自救的精神。一方面他为了和父亲争夺情妇格鲁申卡,扬言要杀死他的父亲,但当老卡拉玛佐夫被杀之后,他被指为凶手,他却不加申辩,在受难和赎罪意识的支配下,承担了弑父的罪名,以苦难来净化自己的灵魂,达到精神的“复活”。作者通过这一形象表现了“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宗教精神的最终胜利。
次子伊凡身上更多体现的是超人哲学和强权思想。他的理智多于激情,不相信上帝,对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但由于他对社会的未来没有信心,其清醒的认识反而导致了他的悲观厌世,认为世间只有暴力和奴役,人可不顾道德而为所欲为。他的思想有力地暗示了斯麦尔佳科夫,终于使他犯下弑父之罪。而伊凡在事实面前,深感自己是思想上的凶手,内心矛盾无法解脱而导致疯狂。通过这一形象,作者从基督教思想出发,否定了超人哲学和强权思想,因为它使人走向罪恶和堕落。
三子阿辽沙代表了东正教观念,虽然没有梅思金公爵那样顽疾在身,但也是一个思想上的白痴。他的纯洁、善良、友爱及牺牲精神虽然高尚,但却是被过于理想化的。他曾遁入空门,但又无法超脱于尘缘,因此现身尘世调解恩怨,结果与梅思金公爵一样于事无补,空留悲叹。作者在他的身上加载了过多的宗教意味,因此使其显得干瘪而没有血肉。
四子斯麦尔佳科夫也像他的父亲那样是恶的化身,他没有信仰,不讲道德,仇视所有的人,在他的身上只有欲望而没有灵性,因此他为了三千卢布竟敢杀死自己的父亲。他以自杀为结局显示了作者在对待“恶”时的无力,也许像斯麦尔佳科夫这样的人从来不会想到自杀。
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艺术成就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成为当代外国文学研究的热点,主要是因为他的小说在艺术观念和表现方法上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而与现代主义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苏联学者巴赫金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向来被视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经典之作。在这部著作中,巴赫金提出了诸如“复调小说”、“对话性”、“狂欢化”、“共时性”等新观念,为后人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对话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具有对话性的小说。从初入文坛,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开始了在这一方向上的探索。写小说离不开对话,因为对话描写是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但对话描写并不等同于“对话性”。传统小说中的对话往往是在作者意志主宰下的对话,所表现的是作者的意识,因此具有单声道的特点,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对话却表现为不同意识、不同思想之间的争论,即使是在独白之中,也暗含着形成争论的另一方。例如在《穷人》中,虽然采用的是书信体,主人公看似是在自言自语,但其中却充满了对话性。
本符什金在信中写道:“前两天在私人谈话中,叶夫斯塔菲?伊万诺维奇发表意见说,公民最重要的美德是会赚钱。他开玩笑说(我知道他是开玩笑),一个人不应成为任何人的累赘((这就是道德。我没有成为任何人的累赘!我这口面包是我自己的,它虽然只是块普通的面包,有时候甚至又干又硬,但总还是有吃的,它是我劳动挣来的,是合法的,我吃它无可指摘。是啊,这也是出于无奈嘛!我自己也知道,我不得不干点抄抄写写的事;可我还是以此自豪,因为我在工作,我在流汗嘛。我抄抄写写到底有什么不对呢!怎么,难道抄写有罪,还是怎么的!他们说:“他在抄写!”可是这有什么不体面呢?((是啊,现在我觉得我是有用的人,我是必不可少的,干吗要胡说八道把人搞糊涂呢。好吧,既然他们认为我和耗子一样,就算我是耗子吧!可是这只耗子是有用的,这是只有用场的耗子,人家还依靠我呢,还要夸奖这只耗子呢:瞧多么好的一只耗子!不过,这个话题讲得够多了,我的亲人,我本来没打算要讲这些,刚才有点激动了。有时候替自己说上几句公平话,总是愉快的。”
巴赫金把上述独白扩展为一段对话来说明其对话性:
他人:应该会挣钱,不应成为任何人的累赘。可是你成了别人的累赘。
杰符什金:我没有成为任何人的累赘!我这口面包是我自己的。
他人:这算什么有饭吃啊?!今天有面包,明天就会没有面包。再说是块又干又硬的面包!
杰符什金:它虽然只是块普通的面包,有时候甚至又干又硬,但总还是有吃的,它是我劳动挣来的,是合法的,我吃它无可指摘。
他人:那算什么劳动!不就是抄抄写写吗,你还有什么别的本事。
杰符什金:这也是出于无奈嘛!我自己也知道,我不得不干点抄抄写写的事,可我还是以此自豪!
他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抄抄写写!这可是丢人的事!
杰符什金:我抄抄写写到底有什么不好呢?
在《罪与罚》里,对话性得到了发展,参与对话的不仅是“我”与“他”,而是由多人构成,形成了全方位的对话。这种对话往往以间接引语的方式出现,读者须认真识别,才能搞清有哪些人物参与其中。下面一段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接到她母亲的信、得知妹妹要嫁给卢仁的消息后的心理活动:
“显而易见,这儿处于最重要位置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拉斯科利尼科夫。哼,那还用说吗,可以帮助他获得幸福,供他上大学,让他成为事务所的合伙人,可以使他的一生得到保障;大概以后他会成为富翁,成为一个体面的、受人尊敬的人,说不定甚至会作为一个享有荣誉的人而终其一生!可是母亲呢?不是吗,这儿所谈的是罗佳,她亲爱的罗佳,她的第一个孩子!为了这样的头生子,怎么能不牺牲女儿呢,哪怕是这么好的一个女儿!噢,亲爱的、不公正的心哪!而且,当然啦:在这种情况下,就连索涅奇卡那样的命运,我们大概也不会不肯接受吧!索涅奇卡,索涅奇卡·马尔梅拉多娃,只要世界还存在,索涅奇卡就永远不会消失!这牺牲,对这样的牺牲,你们俩充分估量过吗?估量过吗?能做得到吗?有没有好处?合乎情理吗?杜涅奇卡,您是不是明白,索涅奇卡的命运丝毫也不比与卢任先生在一起生活更加可憎可恶?‘这谈不上有什么爱情’,妈妈在信上这样说。如果除了没有爱情,连尊敬也不可能有,那会怎样呢,如果恰恰相反,已经有的反倒是厌恶、鄙视和极端的反感,那又会怎样呢?那么,可见结果又将不得不‘保持整洁’了。是不是这样呢?您明白吗,您明白吗,您是否明白,这整洁意味着什么?你是不是明白,卢任的整洁与索涅奇卡的整洁是完全一样的,说不定更坏,更丑恶,更卑鄙,因为您,杜涅奇卡,到底是贪图并非必需的舒适生活,而她那里要考虑的恰恰是饿死的问题!‘杜涅奇卡,这整洁的代价是昂贵的,太昂贵了!’嗯,如果以后感到力不胜任,您会后悔吗?会有多少悲痛,多少忧愁,多少诅咒,瞒着大家,背着人们要流多少眼泪,因为您可不是玛尔法·彼特罗芙娜,不是吗?到那时母亲会怎样呢?要知道,现在她已经感到不安,感到痛苦了;到那时,当她把一切都看清了的时候,又会怎样呢?而我又会怎样呢?……关于我,您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不要您的牺牲,杜涅奇卡,我不要,妈妈!只要我活着,就决不会有这样的事,决不会有,决不会有!我不接受!”(非琴译《罪与罚》第59-60页)
在这段话里,交替出现的是杜尼亚、母亲、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声音,他们都坚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要说服对方,但又不可能真正说服对方。
如果一部小说在总体上是对话性的,就可称为“复调小说”。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这确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特点。”这种小说强调的是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小说中的人物可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即使这思想是与作者的思想相冲突的。作者以及作品中的人物都没有权力宣称自己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和至高无上的。在《罪与罚》中,几乎每个重要的人物都有自己独立的声音(即意识),他们之间展开激烈的争论,但并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识,这种情况造成了小说思想上的多义性,因为站在不同人物的立场上去看,每种的看法都有其合理性。这种新的小说观念,既反映了古代先哲的影响,即古希腊的先哲们认为真理是在平等的对话中产生的,不同的思想意识的撞击才是揭示真理的基础;也有陀氏流放归来后所处环境的影响,在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之下,迫使作者对所写到的不同思想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同时,这也是文学本身的特点所规定的,即文学的象征性决定了它的多义性。
对人物深层心理的挖掘。
十九世纪的小说家大多描写的是人的正常心理,即使有时深入到潜意识的层次,也不构成作品的主体。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当中的多数都不是正常人,他们是具有双重人格的人,是酒鬼,疯子,白痴,杀人犯,色性狂,宗教偏执狂等等,特殊的心理状态要求作家用特殊的方法来表现。这就导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愈来愈倾向于描写人物的深层心理,描写人物心理的非正常状态,如直觉、幻觉、预感、激烈的内心冲突、梦境等,大段的此类描写构成了“意识流”。
例如,《白痴》中有一段对预感的描写:梅思金公爵在罗果静家看见罗果静用来裁纸的一把小刀,而这刀本来是果园里修剪果树用的。从罗果静家出来后,这把刀却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他下意识地几次伫立在一家刀铺前,观看这里出售的一把同样的刀子,甚至毫无必要地给它估了价:“当然,只值六十戈比,再多就不值了。”刀使公爵产生了不祥的预感。果然,不久刀子就派上了用场,先是罗果静在旅馆的楼梯上对公爵拔出了刀子,此后这把刀又插进了娜斯塔西娅的心脏。
《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一直是处于不平静的心理状态的,他面临着数次重大的选择,在作出最后选择之前的犹豫与反复,都反映出他内心的矛盾。他为生活所迫预谋杀人,但同时内心响起的是自责的声音:“这一切是多么卑鄙啊。”即使怀揣凶器来到了老太婆的门前,内心仍然有一个声音在说:“不,回去吧。”犯罪之后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极力逃避警察机关的追踪,但在索尼亚的感召之下,同意去自首,但走在半途,他仍不情愿:“不去不行吗?”,“可以不讲吗?”。当被告知真正的凶手已经落网时,他如释重负,起身告辞,但面对索尼亚的时,他又无力抗拒,只好再次走进警察局。即使他最终归依了宗教,同样也经历了艰难的心路历程。
梦是潜意识的藏身之所,是人的潜在意识的象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多次写到梦,且多是恶梦。
小说写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行凶杀人前梦见自己的童年,梦中一匹小黄马拉着一辆超载的车子,被一群醉鬼肆意鞭打,终于悲惨地死去。显然,这是主人公面临艰难的人生抉择的心理反映。在他的面前摆着两条路,或者像那匹瘦马那样被折磨致死,或者如他所信奉的超人那样铤而走险。事实上,他在生活的重压下,在“超人”理论的诱惑下,最终选择了后者。他虽然杀了人,但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成为超人,跨越“弱者”与“强者”之间的界线,他仍然留下了这一边,他不能像超人那样对杀人的勾当无动于衷。从精神上讲,他是把自己谋杀了,因此,他注定要不断地做恶梦。在他杀人之后,他在梦中回到杀人现场,看到的是杀不死的一直在对他笑的老太婆,以及满屋和满院子的人,人们的笑声和耳语声充满他的耳际,一只只眼睛都在盯着他。这些梦境的描写有力地揭示了他犯罪前后的心理状态。
当拉斯柯尔尼科夫经过艰苦的内心斗争终于投案自首,并被留放西伯利亚后,他的精神归宿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因此,小说有一段写他生病时,做了一个关于世界末日的梦,他梦见人们都失去了理智,互相仇恨,互相残杀,火光遍地,赤地千里,人类与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在走向毁灭。世界末日景象在拉斯柯尔尼科夫心中的呈现,预示了他信仰基督,真心忏悔的精神之路。
严格来说,意识流是指意识在不同时空间的跳跃和流动。人物身处现在,但却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过去和未来,甚至混乱无序,杂乱无章,初看让人不知所云,实际上却是人物烦乱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对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之后惊魂难定,意识常常飞出天外情形的描写,形成了较为典型的意识流段落。
戏剧化情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主要集中在同一空间而不是历史时间上。他“几乎完全不用相对连续的历史发展和传记生平的时间,亦即不用严格的叙事历史的时间”,“他总是力图把理解到的思想材料用戏剧对比的形式,组织在同一时间里,使之分散地展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并不注重在纵向的历史时间上发展情节,而是把矛盾冲突集中在了很短的时间内,虽然没有达到“三一律”那样对时间的严格限制,但也足以让读者感受到情节的紧张与压迫感,只要你走进了他的小说里,就会产生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没有片刻喘息的机会。《罪与罚》中的情节,其紧张激烈,扣人心弦,不亚于侦探小说。小说开篇,情节已处于箭在弦上之态,主人公欲实施杀人计划,杀人之后不久即接到了法庭的传票,在警察局他听到别人在议论那场凶杀案,惊悸之下当场晕倒,更引起警探的怀疑,他去凶杀现场却意外被人撞见,索尼亚对他百般劝导,他犹豫再三,终于走上了自首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