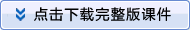第一讲 语法化理论概说
1.1 理论框架
这一部分将简要论述我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从历史事实中归纳规律,揭示汉语语法发展的具体过程。但是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有一个适合描写汉语语法史的理论框架。尽管我们认为新近的历史语言学理论(语法化最适合于我们的研究目标,但是该理论的建立主要是基于对印欧语言历史发展的考察,因此不能简单照搬,必须加以修正以适合汉语的情况。
1.1.1 语法化理论
凡是对历史语言学感兴趣的读者,一定都会对“语法化”和它的相应英语叫法grammaticalization不陌生。然而在目前通行的英语辞典中尚见不到grammaticalization这个词条,甚至大部分的语言学辞典也未收录该词条(如Trask 1993)。要了解该词条的定义只能到有关的历史语言学书中去找。下面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解释。
语法化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时性的,考察语法形式的来源,特别是它们的具体发展过程。从这一角度看,语法化是关心一个普通词汇如何演变成一个语法标记,以及一个语法标记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共时性的,基本是把语法化看作一种句法、篇章和语用现象,即语言使用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各种各样格式。(Hopper & Traugott 1993:2)
现在再让我们看看有关语法化现象的文献。首先注意到有关现象的人是中国学者。根据郑殿、麦梅翘(1964),过去一千年来,中国学者一直很注意语言中的“虚化”现象,相对于普通历史语言学中的“语义虚化(semantic bleaching)”或者“语法化”。一个名叫周伯奇的元代学者已经注意到,很多当时语言中的虚词都是来自实词。清代涌现出了一批研究虚词的优秀学者和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如王引之和其《经传释词》、袁任印和其《虚字说》等。
在西方历史语言学中,法国学者Meillet于1912年在其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章《语法形式的演化》中首先使用grammaticalization(语法化)这一术语,用以描写一个词汇形式如何演化成一个语法标记。此外,他还把语序变化归入语法化现象。该思想还可以追溯到Humboldt和Gabelentz早期关于语言演化的学说。在这篇文章中Meillet已经确立出导致新语法形式产生的两个机制(类推和重新分析。
华裔学者李讷和Thompson合作在汉语历史句法形态学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们的论著(如Li & Thompson 1974, 1976a, 和1976b)对语法化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方面是他们关于汉语连动结构(verb serialization)的研究,指出动词可以语法化为一个格标记,从而可以引起语序的变化。此外,他们还提出了“话题”和“主语”之间的历史渊源:主语实际上是从话题语法化而来的(1976b: 484)。这些研究对汉语历史句法形态学非常具有启发性,后来汉语历史语言系的研究、特别是国外的有关研究都与他们的工作有关。
孙朝奋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汉语史上的语序变化和语法化》。该书首次比较系统地运用语法化理论分析了一组汉语语法标记的发展,其中包括完成体标记“了”、处置式标记“把”、情态标记“得”以及介词的语序变化。此外,该书还讨论了诱发语法化的一些动因,诸如临摹性(iconicity)等。它是最近若干年来用英文出版的比较重要的文献。
从八十年代至今,普通历史语言学领域中出现了一批语法化的理论著作,现在我们把比较有代表性的列举如下。Lehmann的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 A Programmatic Sketch (1995[1982])总结了语法化的研究历史,并讨论了一组有关的例子。Bybee等(1985)的Morpholog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ing and Form是一部非常有影响的理论著作,对语法化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Heine等(1991)的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集中讨论了诱发语法化的语用和认知因素。语法化理论方面最全面、最系统的专著要推Hopper和Traugott(1993)的Grammaticalization一书,该书讨论了几乎所有该领域的重要问题,是我们学习历史语言学难得的好教材。Bybee等(1994)的The Evolution of Grammar从比较语言学和类型学(typology)的角度详细讨论了动词语法标记的发展,材料翔实,颇具有启发性。
另外,还有一些有关语法化问题的论文集相继发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Traugott和Heine合编的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1991),Pagliuca(1994)的Perspectives on Grammaticalization(1994)、Giacalone和Hopper的The Limits of Grammaticalization(1998)等。这些著作中的论文所讨论的问题非常广,诸如语法化与词汇化的关系、诱发语法化的篇章和语用因素、语法化过程中搭配范围的扩展等。
以前关于语法化的研究为我们今天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和经验基础。本书将以我们自己对汉语历史的调查,验证、修正、甚至挑战他们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当然,我们的研究范围并不囿于此,还提出许多我们自己的带有理论色彩的新看法。
根据我们自己的研究经验,下面是一个适合于汉语情况的语法化定义:
语法化是实词或者松散的篇章结构演变成为稳固的语法手段的历时过程,其结果常是产生新的语法标记或者句法结构。
下面分别以完成体标记“了”和动词拷贝结构的发展为例说明,新语法标记和句法结构语法化的特点。当一个词汇语法化时,通常会出现下列特征。据此可以判断一个语法化过程发生的时间。
一、已经语法化的成分会失去它原来自由运用的功能,从而变成一个附着成分(clitic)。例如,在十世纪以前“了”是一个普通动词,既可以单独用作谓语中心动词,又常用于谓语中心动词后表示动作的完成。当它成为一个体标记时,就不再能自由运用,只限于谓语中心动词之后表完成。
二、“了”的语法化过程经历了重新分析。在十世纪以前,“动词+了”代表两个独立的词,即两个独立的句法单位。两者可以被副词、否定标记和受事名词分开。可是在特定的句法环境里,动词和“了”慢慢融合成一个句法单位,其间不再允许插入任何成分。
三、随着“了”的语法化,它的语音形式也开始简化,韵母由一个复合元音变成一个较弱的央元音[c],同时也失去了调值。
四、动词和“了”融合是在它们紧邻共现的句法环境里进行的。在语法化的初期,虽然它们可以被副词、否定标记和受事名词隔开,可是也有很多机会紧邻出现。这种紧邻的环境使它们的融合成为可能。无数的汉语语法化的例子证明,两个成分的重新分析离不开紧邻出现的句法环境。
五、当“动词+了”变成一个句法单位时,整个短语的韵律特征也随之改变。起初动词和“了”各自拥有一个重音,但是语法化以后,“了”则变成一个轻声,整个短语的韵律特征变成了一个前重后轻的格式。
六、“了”原来作为普通动词的一些特点对它语法化的发展步骤具有一定的影响。“了”原来意为“完成”、“了解”,是一个及物动词,通常用于另外一个及物性的谓语中心动词后表示动作的完成。由于这一因素,它在成为体标记的初期(约十至十三世纪),只能与及物动词搭配。十三世纪以后,“了”才慢慢与非及物性成分(如形容词)搭配。
七、语法化以后,“了”失去原来一些重要的语义特征,诸如它的动作义和及物性。与此同时,它也获得了新的更抽象的语法意义,即表示动作行为发展的结构过程。
人类语言发展的普遍现象表明,语序的变化会对一个语言的语法系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Hopper 和 Traugott 1993:50),同时语序的变化也被认为是语法化的现象之一(Heine等1991:2)。在汉语史上,新语法标记的产生往往伴随而来的是新句法结构的出现,它们常常是同一个现象的两个方面。可是,如何来判定一个新句法结构的产生或者语法化呢?以下的特征可以帮助我们对此做出判断。
一、当原来的松散的篇章组织发展成为稳固的句法结构时,成分之间往往会出现相互制约的语法关系。比如动词拷贝结构来自于两个独立的单句,第一个单句的动词引进一个宾语,第二个单句的动词则引进结果补语,此时两个动词之间并没有任何制约关系。可是一旦成为一个稳固的语法结构,只有第二个动词才能加体标记等与时间信息有关的语法形式(详见李讷和石毓智1997)。
二、发展成为句法结构后,其中的成分就不能自由增删。比如动词拷贝结构里的第一个动词后必须有受事宾语,第二个后必须有补语,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成为一个不合法的结构。
三、句法结构中的各个成分常常有一定的语法或者语义限制。比如动词拷贝结构中的名词必须是光杆的或者无指的(non-referential)。
四、整个结构具有稳固而且独特的语法功能。比如动词拷贝结构主要是用于同时引进一个无指的宾语和动作的结果。
1.1.2 重新分析
重新分析是新语法手段产生的最重要的机制。由于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语法系统,特别是具有不同的语序,这个机制也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在SOV语言里,新语法形式的产生通常是通过附着成分的边界的消失、融合和语音形式的弱化而来的(Hopper和Traugott 1993:42-44)。相对地,在SVO语言里,新语法形式的产生主要是通过实词在特定句法环境里的虚化而来的(Hopper 1993:52)。比如汉语的完成体标记“了”是在与其前的动词没有插加词语的紧邻句法环境里,由普通动词演化为体标记的。那么怎么定义“重新分析”呢?先来看一下它在普通历时语言学中的定义。
一、根据Langacker(1977:58),重新分析是一种词语之间内在的语法关系的变化,它不会立刻带来表层形式的变化。它常常会导致成分之间边界的创立、转移或者消失。
二、类似地,Harris和Campbell(1995:61)提出,重新分析是这样一种机制,它改变句法格式的深层关系,但不会在表层上马上显现出来。深层关系的改变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a)成分之间的融合、(b)层次的改变、(c)词类的变化、(d)语法关系的变更以及(c)成分之间的整体性。
三、Hopper和Traugott(1993:40-41)采用Langacker的有关定义,确立出一类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重新分析现象(成分之间的融合(fusion),即两个词语或者形态标记之间的边界消失。有关的例子是复合词化:原来两个或者多个单纯词融合成了一个复合词,该现象常常影响到语义、形态和音韵的发展。此外,融合也常牵涉到成分边界的重新组合。
上述的这些关于重新分析的定义和特征都可以用来观察汉语的现象。下面我们用汉语的例子加以说明。
成分之间的边界变化是重新分析的典型特征。根据我们的考察,几乎所有汉语新语法现象的产生都牵涉到边界的变化。最典型的例证是结构助词“的”的发展。根据石毓智和李讷(1998),从三世纪到九世纪,“底”(“的”的早期书写形式)是一个指示代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这”,只用作名词的定语,即“底”和中心名词一起出现。在这个时期,“底”附着于其后的名词,它们之间存在一个较弱的边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作为指代词的“底”不再能被其它词语修饰,即不会存在“N+底”的组合。石毓智和李讷(1998)确立出“底”语法化的句法环境为:
(2)[VP/AP/NP1 + [底+NP2]]
该组织中,指代词“底”与其后的NP2首先组成一个直接成分,再受前面的VP和NP1的修饰。可是到了九世纪以后“底”成了结构助词时(元代以后书写为“的”),组织结构变成了下面这种结构关系:
(3)[[VP/AP/NP1 + 的]+NP2]
也就是说,作为助词的“的”首先与其前的成分组成一个结构体,然后一起来修饰其后的中心语NP2。在上下文可以确定中心语所指时,它可以被省略。“的”的语法化是一个典型的重新分析案例,其中涉及到成分之间边界的转移、创立、和消失:边界由原来的VP/NP1和“底+NP2”之间转移到“VP/NP1 + 底”和NP2之间,同时在“底”和NP2之间创立了一个新边界,而且VP/NP1 和“底”的边界消弱或者消失了。
但是,边界变化只是重新分析的主要特征之一。根据Langacker经典定义,重新分析不会立即引起表层组织的变化(1977:58)。很多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疑问,诸如Harris和Campbell(1995:61)、Heine等(1991:216)都提供了相反的例证。按照Langacker的说法,重新分析的初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样就无法判断它何时、何地发生。可是按照Harris和Campbell的说法,一些外在的形式标准是可以用来判定重新分析的发生。象结构助词“的(底)”的发展所示,它重新分析的初期就涉及到成分之间的融合和层次关系的改变。在九世纪以前“的”用作指代词时,它首先与其后的名词形成一个结构体,可是在此之后成为结构助词时,而是与其前成分形成一个结构体。层次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的”的语法化还有另外两个特点,改变了原来的词类和与其它成分的语法关系,由原来自由的指代词变成了一个附着的结构助词,与此同时,与其它成分的语法关系也发生变化,作指代词时它是修饰其后的名词表定指,作结构助词时它是附着于其前的修饰语,表示各种语法意义。
但是,Harris和Campbell所指出的重新分析的特征并不能完全涵盖汉语的情况。我们认为,Hopper和Traugott(1993)和Traugott(1994)所确立的重新分析现象非常重要,他们认为,最典型、最常见的重新分析现象是两个成分的融合,使得它们原来的边界消失,这也是语法化过程中最普遍的现象。典型的融合就是复合词化,原来两个或者更多的词凝固成了一个复合词。这种变化对语义、形态和音韵都有一定的影响(Hopper和Traugott: 1993:41)。汉语的情况也不例外,过去几千年来汉语的绝大多数重大变化都与融合有直接或者简介的关系,局部的融合常常是引起语法系统巨大变化的催化剂。本文所讨论的动补结构的发展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证。
首先,让我们简单看一下动补结构是如何通过融合而形成的。中古汉语的一个单句结构为:
(4)S + V + O + R
R(resultative) 是表示动作结果的各种不及物成分,主要为不及物动词和形容词。大约在六至十世纪之间,V和R在没有插加词语的句法环境中慢慢融合。融合首先发生在个别的词语之间,随着这种现象的增加,上述的句法结构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V和R由原来的两个独立的句法单位变成了一个。注意,融合后的结果成分用“-”表示,指示它语法关系的改变(下同)。
(5)S + V + O + R ( S + V-R + O
上述变化过程可以用下例来说明。
(6)唤江郎觉!(世说新语·任诞)
跟据中古汉语的句法规则,如果谓语中心动词之后有受事名词的话,不及物的结果成分只能位于该受事之后。显然,“觉”是不及物的,例(6)反映了这一句法规则。在没有受事名词或者其它插加物的情况下,“唤”和“觉”慢慢融合成一个句法单位。融合之后,受事名词等就只能出现于整个VR之后了。例如:
(7)三翁唤觉知远。(刘知远诸宫调)
从八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大量的动词和其结果成分发生了类似于“唤”和“觉”的变化。开始的时候,动补短语仅仅是个别的词汇化现象(lexicalization),尚不是一个能产的句法格式。随着V和R的大规模融合,大约在十二世纪产生了一个新的句法结构(动补结构。动补结构的出现又带来了一连串的变化,主要包括:
一、汉语的单句结构的语序发生重要变化:S + V + O + R ( S + V-R + O。
二、作为补语的一个次类,汉语的体标记系统“了”、“着”和“过”建立。
三、V和R融合后的共同结果是,不再允许受事名词插入其中。可是动补短语带宾语受到种种限制,它们很多是不能带受事宾语的。这种情况下,受事名词需要在句子的其它位置作重新安排。这又引起了一连串的语法变化,包括把字句的建立、被动句的繁荣、新话题结构的诞生和动词拷贝结构的出现。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将在本书第九章里详细讨论。现在看一下后两种结构的用例。
(8)我昨日冷酒吃多了。(老乞大)
(9)我们还是论哥哥妹妹,从小儿一处淘气淘了这么大。(红楼梦五十四回)
例(8)是一个新话题结构,受事名词置于主语和谓语之间;例(9)是一个动词拷贝结构。
四、补语位置上的成分通过融合而语法化的结果,还常常引起意义变换。例如当“过”变成体标记时,它由原来表示“经过某一地点”引申为表示“经过某一时间”。
五、补语位置上的成分的语音形式常常会弱化,最常见的是失落声调或者韵母变成央元音。比如,从普通动词向完成体标记的变换过程中,“了”的声调由上声变成轻声,韵母由复合元音变成一个较弱的央元音。
当一个普通词汇变成一个语法标记时,它们的使用范围和搭配能力几乎毫无例外地会扩大。比如,作为普通动词的“把”只限于与具体名词搭配,但是作为一个谓语动词前的受事标记,它却可以与抽象名词搭配,比如可以说“把问题想清楚”、“把思想理一理”等。
1.1.3 类推
类推是诱发语法化的两个重要机制之一。重新分析的作用主要是创立新的语法手段,类推的重要性也不可低估,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诱发一个重新分析过程;二是使得通过重新分析而产生的语法格式扩展到整个语言中去。先让我们看一下普通语言学中的适合汉语情况的有关“类推”的定义。
(a) 类推是语法结构的优化过程(optimization),它发展的步骤和范围受制于该语言的整体结构特性。(Kiparsky 1992:57)
(b) 类推是一个语法格式的表层形式的变化,不会马上带来深层结构的改变,它是对业已形成的句法规则的推广和应用。(Harris和Campbell 1995:97)
(c) 类推是句法组织的范式化,会引起表层搭配的变化。(Hopper和Traugott 1993:56,61)
简单地说,类推就是一个句法规则的扩展。下面我们以判断词“是”和结构助词“的”的发展为例扼要说明有关类推的两个重要问题:类推的源动力和类推的限制。
一、“是”的发展
多数学者(如王力1958,Li 和Thompson 1977,Peyraube和Wiebush 1994)都认为,判断词“是”是从下面的句法环境中发展出来的:
(10)Topic(话题), 是 + Comment(说明)
其中的“是”的作用是回指其前的话题。但是我们认为,“是”的发展还有更广阔的背景,它在上述结构中的发展是由当时的单句结构的类推引起的。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简单地讨论“是”发展初期的一些情况。
在没有语法化之前,“是”是一个普通的指示代词,经常用于(10)所刻划的句法环境来回指位于其前的话题。被回指的话题通常为单独的判断(句子)或者复杂的名词短语,一般不能为单纯的名词(关于“是”的详细发展过程,请参见石毓智、李讷2001)。例如:
(11)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可是大约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回指“是”出现了两种规律性的用法。一是说明部分越来越多由名词性成分充任,由《论语》时代(约公元前六世纪)的50%发展到《荀子》时代(约公元前三世纪)的近80%,如例(11)所示;二是,如果“说明”部分是一个光杆名词、人称代词或者人名,常常引起回指“是”与“说明”部分的倒装。例如:
(12)天下之道,管是矣。(荀子·荣辱)
上例中话题是一个名词短语“天下之道”,说明部分是一个光杆名词“管”,与回指“是”的位置颠倒。此时“是”常出现的两种格式可以概括为:
(a)Topic,是+NP+也。
(b)Topic,N +是+也。
自古到今,汉语的基本语序都是SVO,而且作主宾语的也常为名词性短语。同时在上下文可以确定其所指时,主语或者宾语常常可以省略。这样汉语的普通句子就有下面两个变式:
(A)V+NP(无主句)
(B)NP+V(无宾句)
很明显,回指“是”的两个格式分别对应于汉语普通句子的两个变式。这里回指“是”占据的句法位置正好与普通动词的相同,即其前或者其后常有一个名词性成分。在这种条件下,指代词的“是”就有可能通过来自普通动词格式的类推而获得普通动词的性质。语言的发展史毫无例外地证明,使用频率高、范围广的强势语法格式是类推的源动力。大约于公元前一世纪,判断词“是”的用法开始出现。作为判断词的“是”具有动词的特性,比如可以受副词修饰,连接主宾语,等等。此外,象普通动词与其后的宾语结合紧密一样,判断词“是”与其后的名词边界也被消弱了,表现为前期的副词只能插在“是”和其说明部分之间,后期则必须移到整个“是+NP”之前。
“是”的发展表明,类推的发生常常导源于业已存在的语法格式。“是”由名词性的指代词变成动词性的判断词,是受动词的语法格式的类推的影响。这种强大的类推源动力,使得判断词的用法由少到多,最后完全取代先秦汉语的判断句范式“NP (者),NP+也”,而成为汉语唯一合法的判断句。同时,“是”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分析过程,它与其后的成分边界消失。而该重新分析又是为类推机制所诱发的。
二、结构助词“的”
让我们再用结构助词“底”的发展说明类推机制的作用。“底”(“的”的早期书写形式)在三世纪和九世纪之间也是一个指代词,相当于“那”或者“哪”。根据石毓智和李讷(1998)考察,指代词的“底”向结构助词的演化首先发生在修饰语为动词性成分的句法环境里,后来才慢慢类推到其它类型的偏正短语中。类推的大致顺序为:
[VP + 底 +NP]NP(
[NP领有 +底+NP]NP (
[AP + 底+N]NP (
[Adv. + 底+V]NP
一个类推到底能走多远,取决于该语言的语法规则。从古到今,汉语偏正结构的语序都是修饰语居于中心语之前。上述四类偏正短语都共有一个抽象格式:修饰语+中心语,尽管它们所属的语义类型和句法范畴不同。
无独有偶,英语的从句标记(complementizer)也是来自于指代词,其中最常见的两个为that和which。然而英语的从句标记没有象汉语那样,向其它类型的偏正结构发展。这很可能是由于英语的偏正结构缺乏一致的语序,除了定语从句一定位于名词中心语之后外,其它相对于汉语的偏正短语都没有固定的语序,都是既可以位于中心词之前,又可以位于中心词之后。总而言之,类推的范围和步骤受该语言的总体语法结构特性的影响。
现在让我们根据自己的考察,总结一下几个分析语法化过程的步骤:
第一步 确立语法化的具体句法环境。可以根据一个语法范畴在刚刚产生时的结构、语义和用法特点,确立其语法化的句法环境。一个词语在语法化之前,常常会在某些语用格式的使用频率大幅度增加,该语用格式很可能就是诱发它语法化的环境。
第二步 寻找类推的源动力。类推的源动力常常为业已存在的一个范式句法格式。在语法化的具体句法环境被确立之后,尝试寻找它与其它范式语法结构的联系。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寻找这种联系:一、新产生的语法范畴的特性;二、范式的语法性质;三、诱发语法化的具体句法环境形成的时间;四、新的语法范畴产生的时间。类推具有双重功能:诱发一个语法化过程,并且推动一个新产生的语法格式向更广的范围扩展。
第三步 注意重新分析发生的征状。在其它语言中重新分析往往只涉及边界的改变,因此发生的初期不大能为人觉察。可是汉语的情况不一样,伴随重新分析的往往是语序的改变,这与汉语有较固定的语序有关。汉语史上典型的重新分析形式是两个成分的融合或者复合词化。当两个成分融合成一个句法单位时,原来插加其间的成分就必须移到其它位置,结果会带来有关结构的语序变化。
新语法范畴的产生离不开类推和重新分析这两种机制,没有它们任何语法变化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将会按照上述的分析步骤来考察动补结构的形成和它对现代汉语语法系统建立的影响。
1.1.4 句法理论框架
历史语言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从各个时期的口语资料中总结规律,任何规律都要有足够的经验证据,任何规律都要经得起经验事实的考验。在这个领域里,纯粹的理论假想、思辨不大能找到它们的市场,而且指导历史考察需要有尽量少的理论前提和假设,只有这样我们在观察语言事实时才会保持最大的客观性。以下就是我们总结语言规律时应该考虑的最基本的因素。
一、语法单位。语法单位包括语素、词、短语、从句和句子。语素是最小的、不能再分析的、具有意义的语法单位;词是最小的、最基本的、可以独立应用的语法单位。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词构成的单位叫做结构。
二、结构层次。结构层次是指一组语法单位如何通过句法规则形成一个具有意义的结构体,强调语法单位之间的关系是有亲疏之分的。
三、线性序列。线性序列是指一组语法单位先后的排列顺序。
四、词类范畴。词类范畴是根据词语的语法特征对词语所分的类,主要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等。
五、语法关系。语法关系是指位于同一结构体中的各个语法成分之间的相互联系,着眼于成分之间的语序排列,主要包括主语、谓语、宾语、状语、补语、定语。
六、语义角色。语义角色是指两个成分之间语法意义关系,该关系不因语序的改变而改变,主要有施事、受事、动作、结果、修饰、中心语等。
上述所列的这六个特征,是对包括汉语在内的所有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必须考虑的因素(Harris和Campbell,1995:9)。对于我们的研究,这些特征不仅是基本的而且是充分的,它们既可以使我们全面有效地概括语法发展的历史规律,又保证我们的理论偏见降低到最低程度。这样也就可以避免由于某种理论的束缚,扭曲历史事实,或者忽略某些重要的发展。
1.1.5 汉语的语序
历史语言学中所谓的“语序改变” 主要是指句子的三个基本成分(主语、谓语和宾语之间的线性顺序的改变(Greenberg 1963; Mallinson和Blake 1981; Tomlin 1986; Dryer 1991)。但是句法结构的改变远远不限于三个基本成分之间的顺序变化,还包括其它次要成分的相对位置的变更,比如宾语和结果成分之间的顺序,这对于我们理解汉语语法的发展非常重要。
人们发现,一种语言的基本语序与它表示语法范畴的具体表达方式密切相关。比如当一种语言由SOV语序变成SVO时,它原来靠形态(inflection)表示的语法范畴会逐渐为分析手段(phrasal)所取代(Hopper和Traugott 1993:52)。根据这一观察,我们可以理解,汉语主要靠分析手段表示语法范畴的特点是与它的基本语序始终为SVO密不可分的。
有一个重要的知识背景对理解我们的分析很有用,即汉语的基本语序从古到今皆为SVO。这一问题曾引起了学术界的一些争论。主要是受J. Tai (1976)和Li & Thompson (1976)等人工作的影响,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人、特别是在海外工作的学者普遍认为,汉语的基本语序经历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由SVO转变成SOV,现代汉语可能已经成为SOV语言。但是Sun和Givon对现代汉语的大量调查结果显示,现代汉语的基本语序仍然是SVO。他们发现,平均90%的宾语仍然位于动词之后。石毓智(1998)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证明作为句子成分的包孕句的语序只能为SVO,而不可能为SOV。例如:
(13) a. 这是我看书的地方。
*这是书我看的地方。
可是,在句子的层面上,受事名词“书”可以自由出现于谓语动词之前。例如:
(14) a. 我书已经看了。
b. 书我已经看了。
例(14)的两个例子都可以看作是使受事名词话题化的一种手段,与此同时它们必须被理解成“有定的”。
根据上述现象我们认为汉语句子的无标记语序为SVO。从句是句子的一个成分,句子是交际的基本单位。因此,从句的语序不受语用或者篇章因素的影响。所以说从句语序代表的是汉语句子最自然、最基本、也是最常见的顺序。相对地,在独立的句子层面上,句子的三个基本成分可以变换顺序来因应语用因素,诸如话题链或者新旧信息等。
1.2 历史语料的选择
在没有考察汉语历史句法形态之前,我们首先面临的一个任务是如何选择语料。最理想的语料当然是能够充分反应每个时期的口语状况。但是流传下来的历史语料很难见到是纯粹的代表某个时期的口语的文献,往往是书面语和口语的混合,即它们有可能代表不同时期的语言现象。幸运的是,有不少学者对汉语的口语发展史已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诸如蒋绍愚(1996)和刘坚、蒋绍愚(1990、1992)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们的成果我们可以加以借鉴。此外,一些常识可以帮助我们对历史语料进行选择。不同的文体反应口语的程度也不同。一般来说,诗词和散文的书面语色彩比较浓,使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下面几种文体反应各自时期的口语程度都比较高。
一、语录体。该类文体是各个时期重要人物或者逸闻趣事的直接纪录,基本上反应当时的口语,最有名的几部代表作品是《论语》、《世说新语》、《朱子语类》等。
二、宗教文献。很多宗教文献,特别是佛典,是以民间传说或者故事来解释教义的,而且他们的观众多是不识字的普通百姓,这两方面因素决定了他们的语言必须尽量通俗,尽量接近口语的用法。对我们研究最重要的典籍是《敦煌变文》和《祖堂集》。
三、元杂剧。它是盛行于十三到十四世纪的一种文学体裁,属于俗文学的一种,脚本由韵文和宾白两部分构成。其中的宾白部分为我们研究当时口语的重要史料。
四、白话小说。这是一种从宋代兴起的文学形式,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先是话本,后来演变成章回小说。作品相当丰富,充分纪录了这期间的语言演变情况,是我们研究近代汉语发展的最重要史料。最著名的就有《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材料值得我们注意。比如元代编写的供朝鲜人学习汉语的课本《老乞大》和《朴通事》都是纪录当时口语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