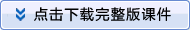第六讲 新语法手段产生的途径
(动补的搭配频率与其惯用语化、语法化
6.1 引言
在第四章里我们讨论了双音化趋势对动词和补语融合的影响,指出双音节的动补组合首先发生融合。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双音节动补组合都具有同样融合的可能性,历史事实是,同样的双音节组合,它们的融合时间差别很大。对于都满足语音条件的动补组合,融合的先后次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一对特定的动词和补语的共现频率。简单地说,分别为单音节的动词和补语共现的频率越高,融合的可能性就越大,发生融合的时间也就越早。
虽然动补结构来自于V和R的融合,但是具体的一对VR融合后并不会马上创造出一个动补结构。在刚开始的时候,个别的动补融合是复合词性质的,有很高的词汇限制,只适用于特定的某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动补搭配。所以我们认为,早期的动补短语是惯用语性质的或者词汇性质的,随着动补融合的大量增加,后来才成为一种能产的句法格式。
6.2 词语的使用频率和其语法变化之关系
词语的使用频率在语法化中的作用是语法化理论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Heine(1991:38-39)指出,从人类语言的语法发展的普遍性来看,词语的使用频率与其语法化密切相关。语法化通常发生在使用频率高的、范围广的词语上,一般不会发生在冷僻的词汇上。可是我们能否认为,一个词汇的语法化的原因单单是因为它们的使用频率高呢?Heine等(1991:38-39)则认为,高频率自身并不足以解释语法化的动因,但是它可能是词语语法化的伴随特征之一。我们同意Heine的前一点看法,但是不认为高频率仅仅是词语语法化的伴随特征。根据我们的考察,词汇的高频率常常是诱发词汇语法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那种涉及到两个成分融合的语法化过程更是如此。
“使用频率”的含义不只一种,可以指一个词语不同方面的使用特性。一个词语的不同方面的使用频率,在语法化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同。首先,使用频率可以指一个词的出现次数,而它的次数的高低是由该词的语义一般性(generality)决定的。一个词的语义越一般,它的使用频率越高。其次,使用频率也可以指在一个特定的句法环境里某个词语的出现次数。如果这个特定的句法环境发生了语法化现象,那么使用频率高的那些词最容易首先受到影响。最后,使用频率也可以指一个业已语法化的词的出现次数的增加。这种含义就是Heine所说的语法化的伴随特征。就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来说,使用频率是指一对动词和补语的共现频率,简单地说,一对动补组合的共现频率越高,它们就越容易发生融合。由此可以推知,最早出现的动补短语都应是高频率共现的动补组合。
使用频率也可以被看作一个语法标记出现的时间或者语法化程度的一个外显特征(Hopper和Traugott 1993)。在一个词汇向语法标记虚化的过程中,它会逐渐失去原来的具体词义内容,与此同时,它搭配的词汇限制逐渐减小,可与之搭配的词语也越来越多。结果就会出现语法化的词语的使用频率增加的现象。在一个语法化所涉及的句法环境里,一个词语的出现频率越高,说明它语法化的程度也就越高(Hopper和Traugott 1993:103)。
使用频率对语法发展的影响也表现在语言接触上。不同语言或者方言之间的语法借用(grammatical borrowing)现象也常首先发生在高频率的词上。比如,根据Yue-Hashimoto(1993)的考察,汉语北方方言的正反问句向南方方言的扩展,首先发生在高频率的词上,其顺序为:判断词 > 存现动词 > 祈使动词 > 普通动词。这种变化顺序存在于很多南方方言对普通话的语法借用上。
对于高频率词在语法变化中的地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句法变化是通过词汇扩展开的。我认为,高频率词或者结构比较倾向于保留旧有的用法。换句话说,最后经历语法变化的常常是高频率的词或者结构。(Tottie 1991)
在新旧形式的类推作用下,句法变化是通过词汇逐渐扩展开的。变化的速度快慢不一,随方言或者说话者的不同而变,没有什么规律可循。某个词的使用频率越高,它自身就越容易发生语法变化;与此同时,它们抗拒类推变化的能力越高。(Yue-Hashimoto 1993)
上述两位学者都认为,句法变化都是通过一个个的词汇逐步扩展的,但是对高频率词的看法似乎不尽一样。有两件事情需要分别对待:一是哪些词汇自身最容易发生新变化;二是新产生的语法标记通过类推的扩展途径。Yue-Hashimoto虽然没有说得很清楚,我们理解她的看法为:新的语法形式总是首先发生在高频率词上,然后再向低频率词扩展。Yue-Hashimoto把语法创新与类推变化区别开来,她在如下一点上与Tottie的观点一致:高频率的词不大容易受类推变化的影响。我们下面的分析将说明,使用频率对动补结构的产生也起了关键作用。
6.3 惯用语化和词汇化
Traugott (1997)认为,从历时的角度看,词汇化跟语法化具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两者都牵涉到音韵和语义的变化,也都常有多个句法单位融合为一个单位的现象(Lipka 1990:97)。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共同性也在汉语动补结构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最早的动补短语都是词汇化性质的东西。
最初的时候,每一对动补短语实质上都是惯用语性质的,它们的搭配具有很强的词汇限制性。为了理解这一问题,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英语的有关现象。类似于中古汉语的可分离式的动补组合,现代英语的动补组合也是非能产的、词汇性质的东西(Green 1972; Dowty 1979; Goldberg 1995),某个补语只能与特定的某个动词搭配。比如,to eat(吃)最常与sick(病)搭配,to cry(哭)最常与sleep(睡)搭配,然而它们与其它结果成分的搭配则不自然、甚至不能接受。
(1)a. He ate himself sick.
b. ?He ate himself ill/nauseous/full.
(2)a. She cried herself sleep.
?She cried herself calm/wet.
动补短语的搭配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首先,一个动词最常跟表示它的最自然结果的词语搭配,比如“打”最可能的结果是“死”。其次,还有一个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如上例所示,在英语中最常与to eat(吃)搭配的是sick(病),然而在汉语中最常与“吃”搭配的却是“饱”。所以两种语言的同一个概念的动词在与补语的搭配上也就不一样。
第二章讨论了,动补结构在现代汉语里是一个高度能产的句法结构,允许V和R的自由结合,只要它们搭配起来意义上说得通。但是在动补结构产生的初期,动词和补语的搭配受到极大的限制,一个动词往往只能与其最自然的结果成分搭配,是属于惯用语性质的。对于一个给定动词,它首先与跟它最常共现的结果成分融合;反过来看也是一样,对于某个特定的结果成分,它首先最有可能与那些跟它共现频率最高的动词融合成一个句法单位。
我们在第四章里讨论了双音化趋势对动补融合的影响。在一对动补组合由于高频率共现而成为惯用化以后,那些双音节的又会进一步词汇化为复合词性质的东西。一旦复合词化,它们就可以象普通动词那样带上受事名词。
在谈到动补结构产生时,我们用到了两个术语“惯用语化”和“词汇化”。两者同中有异,代表了动补结构发展的不同阶段。
惯用语化(idiomatization)(一对高频率共现的动词和补语的用法逐步固定下来而成为一个惯用语。两个成分之间具有最自然的“动作+结果”的语义关系。
词汇化(lexicalization)(双音节的已经惯用化的动补短语,在双音化趋势的作用下,进一步融合成一个复合词性质的形式。已经词汇化的动补短语就可以象普通动词一样带上受事宾语。
使用频率对动补组合的惯用语化或者词汇化起了关键作用。我们具有形式标准来判定使用频率在语法化中的作用。第三章曾详细讨论了中古汉语的多动共宾规律,该规律要求两个动词都必须是及物的,而且分别都与所带的宾语具有“动作+受事”的关系。但是大约在十二世纪左右动补结构牢固建立时,多动共宾结构消失了(第八章将有详细讨论)。表面上看来,VRO形式的出现是对当时的多动共宾结构的违背,因为R成分一般都是不及物的,而且与O并没有“动作+受事”的关系。那么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新语法手段如何能够违背业已存在的语法范式而产生、发展?我们认为,新语法手段的产生途径不能从违背业已存在的语法规律的途径产生。要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假定动补结构的发展经历了下面的发展步骤:
第一步:高频率的VR短语惯用语化。
第二步:双音节的业已惯用化的VR短语又复合词化。
第三步:复合词化的VR短语具有普通动词的语法特点,可以带宾语。
第四步:大量的已经融合的VR短语的合力产生一个动补结构。
本章后边将用具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来说明以上这些发展步骤,详细例示使用频率如何推动可分离式动补组合向动补结构发展。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动补结构的产生过程包括下列步骤:
(3) (a) 可分离式动补组合(
(b) 高频率动补组合的惯用语化(
(c) 双音节惯用语化的动补组合复合词化(
(d) 动补结构建立
上述过程似乎与普通历史语言学的两个成分的融合程度量标(cline)不太一致。Bybee等(1994:40)等所确立的有关量标为:
(4)句法关系(自由语法标记(曲折形式(派生形式(词汇化
然而,虽然(3)和(4)都是为了描写两个成分的融合程度,但是两者目的不尽相同。例(3)是为了描写一个实际的历时发展过程:动补结构如何通过一个个具体动补组合的融合发展出来的,动补结构自身是一个句法结构,它的来源又是另外一个句法结构。然而Bybee等的标尺只是着眼于特定两个成分之间的融合程度,并不是针对任何一个具体的语法现象的历史发展过程。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格式(3)所描写的动补结构的发展顺序并不是说,已经词汇化的动补短语又可以回过头来变成结构比较宽松的句法组织。对于既定的一个动补组合,一旦词汇化,就会凝固下来成为一个词条,不再能变回到原来松散的句法组织。格式(3)所刻划的过程是就动补融合的总体发展过程而说的。当越来越多的动补组合发生融合,就会引起V和R从整体上重新分析,削弱以致消失其间的边界,最后使得可分离式动补组合让位于动补结构。动词和补语融合的直接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新语法形式,同时这一变化还带来了许多新语法范畴的诞生,诸如体标记和情态式,它们都是一些结果补语的进一步虚化而来的。
6.4 个案研究
V+死
“死”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常用在跟暴力有关的动词之后作结果补语。第三章讨论了中古汉语的多动共宾规律,该规律要求,只有两个及物动词才能共带一个宾语。因此当有受事名词出现时,作为结果补语的“死”只能出现于以下两种格式:
(5)a. V+O+死
受事+V+死
格式(5)b的受事可以被看作是句子的话题。然而这种用法十世纪之后逐渐被打破了,开始出现“V死O”的形式。根据我们的考察,该形式始见于十二世纪的文献里,两百余万字的《朱子语类》中有两个这种例子。动补结构也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尔后“V死O”形式有了迅速的发展。可是即使到了十六世纪,结果补语“死”可以和越来越多的动词搭配,能带宾语的“V死”的动词仍有明显的词汇限制。表6.1是对《水浒传》的调查结果。
表6.1 “V死O”形式在《水浒传》中的分布
总合
V+死+O
V+死
打死
48
37
11
杀死
45
33
12
搠死
16
7
9
射死
7
4
3
药死
3
2
1
勒死
3
0
3
烧死
2
0
2
殴死
2
1
1
戮死
2
1
1
淹死
2
0
2
毒死
1
1
0
气死
1
1
0
吊死
1
0
1
苦死
1
0
1
睡死
1
0
1
掷死
1
0
1
弄死
1
0
1
冻死
1
0
1
病死
1
0
1
饿死
1
0
1
拼死
1
0
1
涂死
1
0
1
陷死
1
0
1
表6.1显示,VR的使用频率与它们VRO用法的内在联系。V和R的共现频率越高,它们融合的可能性就越大,它们出现于VRO形式就越早、越多。上表的前四个共现频率最高的动补短语,都可以自由地用于VRO格式。大约75%的“打死”和“打杀”都带有受事宾语。此外,最早的“V死O”用例也是发生在动词“打”上(梅祖麟1991)。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最后13个使用频率只有1次的动补短语,几乎都没有VRO形式。这些低频率的组合都是些临时搭配,尚未达到高度融合,因此不能带受事宾语。决定动词与结果补语“死”搭配频率的因素是语义的普遍性,在与暴力有关的动词中,“打”和“杀”的语义最一般,它们与“死”的搭配频率也就高。下面是两个VRO形式的例子。
(6)等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水浒传三回)
(7)林冲杀死差拨。(水浒传九回)
十五世纪左右动补结构已经牢固建立了,从总体上看动词和补语的融合已经完成。但是对于同一个补语,它与不同的动词的融合程度还是有明显的高低之分,而决定这种融合程度高低的关键因素则是某个动词与这个补语的使用频率。低度融合的动补短语虽然不再能为其它词语所分离,但是尚不能带受事宾语,只有高度融合的才可以。表6.1清晰地显示,一对动补短语的共现频率与它们融合程度之关系:共现的频率越高,融合的程度也就越高,带受事宾语的时间也就越早。一对动补组合的共现频率决定于两个成分的语义一般性和相关性。
V+觉/醒
“觉”和“醒”是用于先后两个不同时期的同义词,“觉”主要用于十世纪之前,之后逐渐为“醒”所代替。因为“觉”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受当时的语法规律的制约,它只能出现在“VOR”格式中。例如:
(8)唤江郎觉!(世说新语·假谲)
十世纪之后该概念的动词逐渐可以出现在VRO形式中,说明“觉”或者“醒”已经与其前的动词发生了融合。例如:
(9)是我唤醒他。(朱子语类)
(10)所以唤醒那仁。(朱子语类卷第二十)
到了十二世纪,表面上看来,作为结果补语的“醒”可以出现在VRO和VOR新旧两种格式中。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能用于新格式VRO的动词只有两个,如下表所示。
表6.2 《朱子语类》里“V醒”带宾语的情况
总合
VR
VRO
VOR
唤醒
31
21
10
0
提醒
9
2
7
0
点醒
2
0
0
2
喷醒
1
0
0
1
苏醒
1
1
0
0
醉醒
1
1
0
0
抖擞醒
1
0
0
1
跟结果补语“死”的情况一样,对于结果补语“醒”来说,只有共现最高的前两个动词才可以出现于VRO格式中。这再一次证明了,共现频率对动补组合的融合时间和程度的重要影响。
表6.2还揭示了另外一个重要现象。在十二世纪左右,表面上看来,结果补语“醒”既可以出现在VRO形式,又可以出现在VOR。但是事实上对于某个特定的动词而言,它可能只能出现于其中的某一个格式。两个与“醒”共现频率最高的动词“唤”和“提”只能用于新格式,而其余共现频率低的则只能用于旧格式。旧格式的用例如:
(11)以水喷之便醒。(朱子语类卷第三十四)
没有一对具体的动补组合是新旧格式都可以使用的。这种现象显示了中古汉语的可分离式动补组合向动补结构转化的途径。对于给定的一个结果补语来说,动词和补语的融合首先发生在高频率共现的动补组合上,然后向低频率的组合类推扩展。
所以,我们不能单纯根据结果补语“醒”在《朱子语类》中可以用于VRO形式就贸然得出结论:它已是作为能产的语法手段,因为用于该结构动词还只限于特定的两个。它们还是惯用语性质的东西。要看哪个语法规律在真正起作用,首先要根据临时的搭配服从哪个规律。由此判断,当时起作用的语法规律仍是可分离式动补组合,因为所有的临时搭配都服从它的要求。也就是说,那时“V醒O”还是词汇性质的。当时普通的动词和结果补语“醒”之间还可以被副词隔开,例如:
(12)莫教才醒。(朱子语类卷第十七)
前文谈到,V和R的惯用语化的动因是它们的高频率共现。一个惯用语化的动补组合是否能进一步复合词化,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于它们的音节数目。表6.2的前两个首先复合词化的动补短语都是双音节的。相对地,此时大于双音节的组合仍然是可以分离的。例如:
(13)只得抖擞得此心醒。(朱子语类卷第十)
第四章已经详细讨论了动补组合的音节数与其融合速度之关系。
音节数目对动补融合的影响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出。宋朝时期活跃着两个用于动补组合的中缀:“得”和“叫”。如果一个动补组合含有中缀,那么整个组合至少有三个音节,此时它们的组织比较松散,仍可以为受事名词隔开。例如:
(14)只要提教他醒。(朱子语类卷第五十九)
我们上边是依靠一个动补短语能否带受事名词为标准来判断它们的融合程度。原来插入动词和补语之间的副词和否定词的位移,也同样可以揭示动补融合首先在什么地方发生。《朱子语类》反映出,副词或者否定标记在“V+醒”中的位置仍有两种可能:插入它们之间或者置于整个短语之前。究竟是哪种位置,跟V和“醒”的共现频率有关,归根结蒂是由它们的融合程度决定的。
同样,如果不考虑新旧形式分布上的词汇限制,就可能得出结论说,结果补语“醒”在十二世纪可以用于VRO和VOR两种格式。然而用于两种格式的V的成员是明确不同的,频率最高的那两个只能出现于VRO,频率低的则只能出现于VOR。没有一个动词是同时可以出现于两种格式的。这种现象揭示了新格式产生的条件以及它扩展的路线。
6.4.3 “吃饱饭”和“喝醉酒”
随着动补结构的建立,中古汉语的多动共宾结构慢慢走向消亡。动补结构是来自于中古汉语的可分离式动补组合,最简单的一种变化是:VOR(VRO。但是,事实上这只是可分离式动补组合的诸多变化方向之一。动补结构的建立本质上是动词和补语的融合,融合的共同结果为,其间不再允许插加任何成分,原来位于其间的受事名词、副词或者否定标记必须出现于其它位置。副词和否定标记的位移比较简单,只能出现于整个动补短语之前。受事名词的情况就复杂得多,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很多动补短语不能带受事宾语。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为:一、动词和补语融合的程度;二、补语的语义指向。在2.3.3部分,我们讨论了现代汉语的一条规律:如果补语的语义指向为句子的主语(施事),那么所在的VR短语不能带受事宾语。例如:
(15)a. *她看病了书。
*他吃胖了肉。
例(15)两例中结果补语“病”和“胖”都是描写主语的性质,直接加上受事宾语就成为不合法的句子了。相应合适的表达式就是动词拷贝结构,例如:
(16)a. 她看书看病了。
他吃肉吃胖了。
动词拷贝结构的出现也是动补结构建立所带来的句法变化之一。第九章将系统讨论这个问题。
可是上述规则在现代汉语里慢慢出现了“例外”。根据对大量语料的调查,我们发现了两个特例:“吃饱饭”和“喝醉酒”。先看“吃饱饭”的用例:
(17)这几天吃饱了饭。(儿女英雄传)
(18)吃饱了饭练练气功。(编辑部的故事)
上例中的结果补语“饱”是描写动词“吃”的受事,但是可以带上受事名词“饭”。下表是我们对十八世纪到现在的几个文献的统计结果。
表6.4 现代汉语里“V+饱”的带宾语情况
V+饱+O
V+饱
吃饱
6
14
打饱
0
1
气饱
0
1
看饱
0
1
可以看出,能用于“V饱O”格式的动词只限于“吃”一个动词。其实只有动词“吃”后的“饱”用的才是本义,表示“摄取了足够的食物”,其它的“饱”都是用的引申义,强调程度。
“吃饱”在现代汉语里的用法再一次证明了,动补短语的共现频率决定其融合程度。在我们调查到的几个“V+饱”短语中,“吃”和“饱”的共现频率是最高的,远远高于其余所有用例的总和。根据我们调查的范围,就结果补语“饱”的本义来讲,其实真正能与“饱”搭配的动词只有“吃”一个。“吃”和“饱”的高频率共现有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它们自身分别都是最基本的词汇,在日常语言中出现的频率极高;二是它们之间存在着最自然的“动作-结果”联系。它们高频率共现的结果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惯用语化以及进而词汇化,最后可以像一个普通动词一样带上一个受事宾语。
关于动补融合的考察我们一直没有讨论宾语名词的情况,其实宾语名词的性质也可以揭示动补融合初期的一些重要语法性质。在“吃饱”可带受事宾语的全部6个用例中,受事名词全部是“饭”,即指示食物的最普通名词。如果把受事宾语换为其它名词则就不大能说,比如不说“吃饱了面包”、“吃饱了烤鸭”等。这种现象使得我们认为,“吃+饱+饭”整个短语都惯用语化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成分都不能自由为其它词语替换。也就是说,这种组织尚不是句法结构。
另外一个类似的现象是“喝醉酒”。中古汉语里,结果补语的“醉”因为是不及物成分,只能出现于VOR格式中,例如:“饮酒醉(《史记》)”。动补结构建立以后,插入中间的“酒”就被挤到外边去了。因为“醉”的语义指向为其前动词的施事,即使在动补融合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不能有“V醉O”形式出现。这种状况持续了大约七、八百年的时间,这其间要引进受事名词时通常用动词拷贝结构和新话题结构。例如:
(19)a. 他酒喝醉了。
他喝酒喝醉了。
直到最近“喝醉”之后才可以带上一个宾语。例如:
(20)他是喝醉了酒发酒疯。
跟“吃饱饭”的特点相同,结果补语“醉”前的动词只限于“喝”一个动词,其后的受事宾语也只能是“酒”。三个成分的任何一个都不能随意为其它词语所替换,比如不能说“喝醉了茅台”或者“尝醉了酒”。据此我们认为,“喝+醉+酒”三个成分一起被惯用语化了,它们也不是能产的句法结构。
“吃饱饭”和“喝醉酒”是今天的两个活生生的案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最早的动补短语的性质和业已存在的句法范式之关系。上边的分析说明,新语法现象的产生不能违背当时的语法规律。在这里,“当时的语法规律”就是补语的语义指向为施事的动补短语不能带受事宾语。表面上看来,“吃饱饭”和“喝醉酒”的出现违犯了这条语法规律,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先是因为动词和补语的高频率出现,使得它们融合成复合词一类的组合,然后再与受事名词惯用语化。整个组合现在尚是词汇性质的,与现在真正起作用的语法规律尚不在一个层次上,不直接发生关系,也就无所谓“违背”的问题。动补短语带受事宾语的语法规律支配着所有的临时搭配。但是我们也可以根据已往动补短语发展规律预测,随着“吃饱饭”这种用法的逐渐增加,它们将来也可能发展成一种范式,最后会取代现存的动补短语带宾语的规律。当然这个过程通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今天的预测只有等待几百年以后的人来验证了。
6.4.4 “V+尽”和“V+破”
现在我们再来看另外两个常见的动补短语的发展特点。“V+尽”和“V+破”是两个最早可以用于VRO形式的动补短语。动补短语可以根据补语的语义指向分为几种类型,不同类型的语法特点不仅不一样,而且引入语言的时间差别也很大。最早出现的VRO形式的R的语义指向一般为受事名词。例如:
(21)等闲读尽诸书史。(敦煌变文·父母恩重)
其中的“尽”是指受事宾语“诸书史”。
大约在八世纪左右,补语的语义指向为受事的VOR形式开始变成VRO。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典型的新旧形式共存的情况。但是就给定的某个结果补语来说,只有一部分只能用于新形式,另一部分则只能用于旧形式,一般没有两者都可的情况。下面两表是我们对九世纪的文献《敦煌变文》的统计结果。
表6.5 结果补语“尽”在VRO和VOR中的分布
“V+O+尽”式的动词
“V+尽+O”式的动词
饮、断、吟、吸
读、买、写、过、受、使、告、化
表6.6 结果补语“破”在VRO和VOR中的分布
“V+O+破”式的动词
“V+破+O”式的动词
战、拽
刺、踏、打、拆、骂、粝
表6.5和6.6列举了《敦煌变文》中所有与结果补语“尽”和“破”搭配的动词。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值得注意:一、动词和有关结果补语的融合已经完成,从可用于新格式VRO的动词类型来看,多数动词只出现于新格式。对于结果补语“尽”来说,可出现于新格式的动词是旧格式动词的2倍;对于结果补语“破”来说,则是3倍。这种对比说明,有关动词和补语的融合已经达到高度融合。二、虽然从表面上看,两个结果成分可以出现于新旧两种格式,但是两种格式中的动词绝不相混,即没有一个动词是可以用于两个格式的。这种现象说明,动补结构的融合和扩展是通过词汇扩散开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结果补语为“尽”时,两个同义词“读”和“吟”的用法不一样,前者只能用于新形式,后者则只能用于旧形式。“读”是念书行为中语义最一般的动词,而“吟”则是语义很专门的一个,指“有节奏地诵读诗文”。可以推断,“读”的使用频率应比“吟”的高,这可能是造成它们在新旧格式用法上差别的原因。
上述的分析表明,动补融合首先发生在高频率共现的组合上,新形式是通过词汇扩展开的。扩展的顺序也是从高频率组合到低频率组合。新形式刚出现的时候并不会马上与旧形式竞争,因为它一般是词汇性质的。对于一个既定的R来说,当所有的VOR都变成了VRO时,这对动补组合的融合就最后完成。新形式首先发生在共现频率最高的动补组合上,然后向共现频率较低的组合上扩展。这样的个别动补组合融合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可分离式的动补组合就会让位于动补结构。
6.5 情态结构的否定式的产生
否定式情态结构的产生和扩展是另一个理想的例子说明,动补组合首先是怎么发生的,后来又是怎么扩展的。现代汉语的否定情态式的语法意义为,某种动作行为没有实现某种结果的可能性。例如:
(22)a. 我这个月写不完那本书。
他搬不动那块石头。
在4.3.4部分讨论了否定情态式的产生分两个步骤:第一步,在结果补语的位置上,“不”与R首先融合成一个单位;第二步:“不R”再与V进一步融合成现代汉语的否定情态式。其过程可以用下式表示:
VO不R(V不RO
左端的格式就是中古汉语的可分离式动补组合,右端的则是现代汉语的动补结构。情态式是动补结构中的一个次类,它的发展动因和路线也与其它的动补短语的一致。
第一步向第二步的转换大约发生于十二世纪左右。在此之前,如果有受事名词的话,“不R”只能出现在受事名词之后。也就是说,首先在结果补语的位置上,“不”和“R”首先融合成一个语法单位。先让我们先看R的语义范畴与它们用于新旧格式之关系。
表6.7 《朱子语类》中“V不R”带受事宾语的情况
V不R
VO不R
V不RO
总合
V+不得
914
279
62
1255
V+不住
24
21
0
45
V+不下
23
9
0
32
V+不出
34
19
0
53
V+不尽
46
22
0
68
上表是对最常用的前5个“不R”的统计结果。我们假定,这时候的“不R”短语已经融合,这一点还可以从它们的意义特点上看出来,它们的真正含义已经不再是它们字面所表达的。它们作结果成分的主要语义特点可以概括如下。
(23) a. 不住:不能达到(某种目的)。
不下:不能忍受。
不出:不能发现。
不尽:不能完成。
不得:不能作。
否定情态式的发展再一次说明共现频率与动补融合之关系。类似前面的分析,如果不考虑词汇限制的话,十二世纪左右的“不R”可以出现于VRO和VOR新旧两种格式。但是可用于新旧格式的词汇类型是严格区别开的。单就R的语义范畴来看,能用于新格式的只有一个“不得”,其余仍然都只能用于旧格式中。这种现象的背后也是使用频率上的差别。单单“不得”一个结果补语就出现了1255次,其余4个的全部总合才199次!跟前面分析的原因一样,“不得”的高频率使用使得它与其前动词的融合首先发生,因而也就最早达到高度融合。下面是《朱子语类》里结果成分“不得”用于新格式的用例。
(24)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圣贤,却管不得那富贵。(卷三)
(25)据某看来,亦舍不得这个苍苍底。(卷五)
(26)敬当不得小学。(卷七)
(27)学者若不穷理,又见不得道理。(卷九)
十二世纪的《朱子语类》已经出现了“V不得O”新形式,那么在此之前的文献中的“不得”与其它“不R”的使用频率之比更具有启发性。下表是我们对九世纪左右的文献《敦煌变文》的统计结果。
表6.8 《敦煌变文》里“(V)不R”的使用频率
V+不得
V+不住
V+不下
V+不出
V+不尽
38
3
3
2
3
表6.8显示,“不得”用于结果补语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其余的总合。其结果与表6.7统计结果相近。八世纪左右尚没有“V不RO”式的否定情态式。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说明,“不得”后来首先用于新兴否定情态式是由它长期高频率用作结果补语决定的。我们的分析同时也可预测,新形式不可能首先发生在低频率的“不R”上。
我们上面只考虑了R的语义范畴,发现在所有的“不R”中,只有“不得”一个才可以用于“V不RO”形式。现在来考察“V不得O”中的V的语义类型。并不是所有的动词都可以用于新兴的否定情态式。《朱子语类》里结果补语“不得”与278个不同的动词搭配,但是只有很小一部分动词才可以用于“V不得O”格式里。
表6.9 《朱子语类》里“V不得O”式的分布
使用次数
动词数目
可用于“V不得”式%
“V不得O”用例的总和
“V不得O”用法占所有用例%
58-133
5
100%
30
50%
20-48
7
56%
10
16%
10-17
9
22%
7
11%
5-9
17
17%
3
5%
2-4
79
8%
7
11%
1
161
2%
4
6%
表5.9明确地显示,动词和“不得”的使用频率与它们可以用于“V不得O”形式之间的关系:两者的共现频率越高,它们用于新形式的机率也就越大。所有前5个与“不得”共现频率最高的动词(使用范围在58-133)都可以出现于新格式,它们用于“V不得O”的次数占全部278个动词用于该格式的用例的50%!同理,共现频率越低,用于新形式的机率也就越低。在161个使用频率仅为1次的动词中,只有2%才可以用于新格式中,只占所有新格式的6%。下面是《朱子语类》里一些低频率的动词与“不得”搭配时仍用于旧结构的用例。
(28)济人济己都不得。(卷七)
(29)盖儿时读书,终身改口不得。(卷七)
(30)若不是先有个木,便亦自生下面四个不得。(卷三)
(31)设或理会得些小道理,也滋润他不得。(卷九)
结果补语“不得”的发展显示,使用频率对否定情态式产生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补语方面。在一组功能相同的结果补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那一个最有可能首先出现于新格式中。其次是关于动词方面。对于一个既定的结果补语,与之共现频率最高的动词具有最大的可能性出现于新格式中。
在刚刚开始的时候,结果补语“不得”可以用于VRO和VOR新旧两种格式中。下表是以动词为考察对象,看多少动词可以出现于新旧两种格式,多少动词只能出现于其中的一个。
表6.10 《朱子语类》动词在新旧格式中分配的数量
只有新格式
新旧格式都有
只有旧格式
动词数目
9(7%)
18(14%)
102(79%)
表6.10的统计数字显示,否定情态式在十二世纪左右才刚刚成形,并开始扩展。但是当时真正起作用的句法规律仍是旧格式,它支配着各种临时搭配的语序。这与我们其它的调查结果一致。考虑到动词的使用频率的话,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前6个与“不得”共现频率最高的动词都是可以用于新旧两种格式的。低频率的词绝大部分只能出现于旧格式中。还有一些频率较低的词,我们只统计到了它们新格式的用法,这有可能是受新格式类推作用的影响。
现代汉语的否定情态式的最后建立不会晚于十四世纪。此后,不仅所有的“不得”都只能用于新格式中,其它在《朱子语类》时代只能用于旧格式的“不R”也可以出现于新格式。例如:
(32)他其实咽不下玉液金波。(西厢记)
(33)锁不住心猿意马。(西厢记)
大约在十六世纪左右,新格式最后取代了旧格式。一旦否定情态式发展成了一种稳定的语法手段,词汇限制就没有了,只要意义上讲得通,任何动词或者结果补语都可以用于“V不RO”格式。
6.6 理论蕴含
本章的分析涉及到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包括新旧格式转换的机制、使用频率在语法化中的作用以及融合的程度、单向性和表层结构的地位。下面我们将简要地讨论这些问题。
6.6.1 新旧格式的转换机制
语法化的结果常常是新结构的产生,而新结构的产生又会引起功能相同的旧结构的消亡。新旧格式的交替几乎毫无例外地经历一个长期共存的中间阶段,可以用下式表示(Hopper和Traugott 1993:36):A(A/B(B。这种新旧形式的转换方式不仅适用于语法变化,也适用于语音、词汇方面的变化。它揭示了语言变化的本质特征之一。人们认为,中间阶段的A和B是具有同样性质的东西,都是语法形式。所以,Hopper和Traugott(1993)认为,在最初的时期,新形式是作为旧形式的一个变式而存在的。如果只考虑表面的线性形式的话,一个新形式发展的自始自终可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如果我们以下面两个标准来判断时,就会发现一个新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可能经历性质(或者说语法地位)的改变。
惯用语化/词汇化(能进入新形式的只限于特定的某一个或者少数几个词汇,是非能产的。支配临时组合的语法规律仍然是旧形式。
句法结构(原来对新形式的词汇限制消失,新形式变成一个高度能产的的语法手段。与此同时,功能相近的旧形式很快消亡。
明确了词汇化和句法化的区别,我们就会意识到,两个通常被认为是同一语法范畴的两个变体(variation),可能是性质不同的东西,分属于语言的不同层面。
动补结构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新旧格式转化机制的理想案例。它涉及到两种变化:
变化一:VOR(VRO
变化二:Vt Vt O((
左端的两式是同一个规律的两个不同的表现方面:只有两个及物动词才能共带一个宾语;否则,不及物的结果成分只能出现于受事名词之后。因此VRO形式的出现违背了原来的多动共宾规律,因为R成分多是不及物的。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新语法形式能否在违背现有的语法规律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不管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我们都将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逻辑悖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所谓的“语法规律”就不能被看作什么规律了,因为它允许“例外”的产生和发展,而且还最后让位于这个“例外”所发展出的规律。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严格的语法规律的确在历史中存在,在相当长的时期不允许有任何例外。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结论应该是,与以前的语法规律不一致的新形式永远不可能出现。这也与历史事实不符,动补结构的产生就是这个结论的反例。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提出新旧格式转化的另外一种模式。
设定存在一个动词集合和结果补语集合:
动词集合:{V1, V2, V3, . . .}
补语集合:{R1, R2, R3, . . .}
第一步、惯用语化(V1和R1的高频率共现使得它们变成一个固定的表达式。
第二步、词汇化(如果V1R1确定一个双音节的单位,在受双音节趋势的影响下,它们就可能变成一个复合词。词汇化之后就可以像普通动词一样带上受事宾语。但是此时的V1R1O形式是词汇性质的,而不是句法性质的。
第三步、句法化(使得V1R1融合的机制对别的动补组合也起作用,越来越多的动补组合发生了融合。大量的融合就产生一个强大的类推力量,结果导致了动补结构的产生。作为句法手段的动补结构一产生就有大量的用例作为支持,而且背后还有符合当时的语言系统的深刻理据,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能力,很快战胜了原来的与之不相容的旧形式。
为了讨论的简便起见,我们假定一个融合只涉及到特定的某一个动词和一个补语。而事实上,融合过程可能是多维的,比如一个动词可以同时与几个补语融合,反之亦然。
我们新提出的新旧格式转换的模型具有多方面的优点。首先,新形式的产生并不需要与现存的语法系统发生矛盾。在刚开始的时候,新形式仅仅是词汇性质的,与现有的语法规律不直接发生关系。随着词汇化的大量积累,它们最后发展成为能产的句法格式。此时它们获得了充分的存在理由和强大的竞争能力,最后战胜了与之不相容的旧有语法格式。其次,我们的模型可以准确地把握刚出现的新形式的共同特性(词汇限制。毫无例外地,任何新形式在产生的初期,都是只有个别词语才能用于其中。比如十二世纪作用的否定情态式的结果成分只能是“不得”一个,动词也只有少数几个。又如,当结果补语“醒”刚开始出现于VRO式时,动词只限于“叫”和“提”两个。再如,当结果补语“死”用于VRO式时,动词也是语义最普通的“打”等少数几个。更有趣的是,惯用语化也会涉及到动补短语之后的受事名词,比如“吃饱”只能带“饭”一个名词受事,“喝醉”只能带“酒”一个受事名词。这说明整个“VRO”短语都是一个固定表达。最后,我们的模型也可以成功的解释一个新形式在量上由少到多的变化。
尽管最早一批的动补短语出现于八世纪左右,可是它们作为能产的语法格式是十二世纪左右的事。当它成为一个句法格式时,不仅使用频率大量增加,而且类型也变得丰富多采。与此同时,也迅速地导致VOR和多动共宾式的消亡。
我们的新格式成长模式跟Bybee等(1994:51)所提出的“词汇扩展机制”(the mechanism of lexical expansion) 很相似。他们发现,助动词开始时只能与动态动词搭配,后来扩展到静态动词。搭配范围的扩展是一个词汇语法化以后的共同特点。随着一个词汇的语法化,它的语义也会变得越来越抽象、一般,与之可搭配的词语也会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的着眼点与“词汇扩展机制”并不完全一样。我们的目的是想说明,第一个新形式是怎样产生的,它的孕育过程是什么,最后怎么样成为一种能产的语法手段。也就是说,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形式在成为语法格式之前的情况,而“词汇扩展机制”说的则是一个形式成为语法手段之后的发展。
6.6.2 使用频率、融合和语法化之关系
本章运用大量的语料和统计数字,证明了动词和补语的共现频率对他们融合的影响。“使用频率”可以指一个语言形式发展的多个方面,人们可能在完全不同的含义下用它。Bailey(1973)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新旧形式转换过程中的S-型频率增长模式。下面是Krock(1989)对这个模型的概括。
新旧形式的替换在时间上呈S型曲线发展:一个新形式对旧形式替换的初期速度相当缓慢,中间阶段呈加速度发展,到了旧形式只是残存现象时,替换的速度再一次慢下来。
Krock指出许多变化都遵循着S型的发展曲线,但是他认为这种频率的变化并不是新形式产生的动因,也不是推动它们发展的因素。Krock这里所说的“频率”是指新旧格式之间的消长关系,与我们所谈的并不是一码事。
注意,我们所说的“使用频率”是指在语法化之前一个词汇形式的出现次数,对于动补组合来说,就是它们的共现频率。我们关注的是词语的使用频率与第一个新形式之间的关系。为此我们设立了一个形式标准来判定一个新形式产生的时间。根据我们的广泛调查,最早用于新形式的动补组合毫无例外地都是共现频率最高的那些。使用频率是促使动补融合的关键因素之一。
语法化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个方面都牵涉到使用频率问题,而使用频率在这个过程中作用的方面或者发生作用的效应也会有所变化。在不同类型的语法化过程中使用频率起作用的方式也会不同。对此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Heine等1991指出,语法形式通常来自于使用频率高而且用法普遍的词语,这给人一个印象:一个词语的高使用频率赋予它语法化的资格。但是他们认为,高使用频率仅仅是一个语法化词语的伴随特征,并不是促使它语法化的动因。的确,一个新语法形式一旦建立,它的使用频率会迅速增加。在这种意义下,使用频率可以被理解成语法化词语的伴随特征。Heine等的“使用频率”所指的实际上是一个词语语法化前后的频率变化对比。这与我们所谈的也不是一回事。
我们所谈的“使用频率”是指V和R在所有语言环境中的共现次数。从动词的一方来看,我们关心的是它与某个特定的结果补语的共现频率。共现频率越高,它们融合的可能性越大,出现于新形式也就越早。同理,从补语的角度看也是一样。
使用频率只是促使动词和补语融合的四个关键因素之一,前一章讨论了音韵因素,接下来两章将要讨论另外两个因素:紧邻的句法环境和语义的完整性。并进一步分析,一对动补组合的共现频率的高低也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动词和结果成分各自的语义普遍性,它们的概念义越普遍,它们在语言中的使用频率也就越高。二、动词和补语词语之间是否存在着自然的“动作+结果”关系,两者的关系越是自然,共现频率就越高。
6.6.2 融合的程度和单向性
我们已经从多方面证明,最早的动补短语都是词汇性质的,并不代表任何句法规律。在双音化趋势等因素的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动补短语发生了融合。大规模的融合产生一种合力,导致动补结构的出现,尔后通过类推很快取代了原来的可分离式动补组合。这里我们似乎是说动补结构经历的变化为:词汇化(语法化。表面上看来,这种变化与Bybee等(1994)所提出的“语法化的单向性原则(unidirectionality)”相违背,因为他们认为发展的顺序恰好相反,语法化过程的最终点是词汇化。实际上我们的看法与此并不矛盾。任何一对具体的动补组合的融合程度都是单向性的。比如,实现体标记“了”经历了普通动词、附着成分和形态标记三个阶段,它与其前动词的融合程度也由低到高。又如,一些已经完全词汇化的动补短语,象“说明”、“扩大”等,并不能再回过头来变成关系较松的句法结构。所有这些都遵循着语法化的单向性发展原则。我们所谈的“从词汇化到句法化”的发展是就动补结构的总体发展而言的。动补结构的来源是中古汉语的可分离式动补组合,该组合的动词和结果成分是代表两个独立的句法单位。后来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一个个具体的动补组合发生了融合(词汇化),大规模融合所产生的类推力量产生了一种新语法结构(动补结构。
6.6.4 表层形式和语法
我们的分析为语法演变提供了一个新视野。一个新形式的出现并不马上意味着语法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它们结构上和语义上都与后来发展成的句法结构有关。最早的动补短语实际上都是些惯用语性质的东西。所以我们并不赞成Krock(1989)的看法,他认为使新语法形式成为可能的背后有一个“深层语法 (underlying grammar)”,它存在于最抽象的层次上。“深层语法”完全是一个假想的概念,没有任何经验证据。在我们的分析里根本不需要这种缺乏事实根据的抽象概念。相反,语法变化的动因常常是具体的、可观察到的东西,比如双音化趋势和使用频率对动补结构发展的影响,两个因素都是可以进行准确的量化分析的,并有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