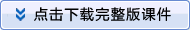第七讲 从类型学的角度探讨语法化问题
(量词、指示代词和结构助词之关系
7.1 引言
人类语言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定语从句标记(relative clause marker)大都是由指代词演化而来的。根据我们的研究(李讷、石毓智1997;石毓智、李讷 1998),汉语史上先后出现的两个主要结构助词“之”和“底”原来都用作指代词。结构助词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作定语从句标记。我们还从历史动因和语义功能等角度论证了,指代词和结构助词之间的可能发展关系。
我们认为,唐宋之际的结构助词“底”产生的历史动因为量词语法范畴的诞生。原来汉语的“数+名”短语的修饰语和中心语之间是零标记的,随着量词语法范畴的建立,汉语的数量短语经历了以下抽象格式的变化:
修饰语+中心语 ( 修饰语+语法标记+中心语
在新数量短语格式的类推作用下,普通的修饰语和中心语之间也要求一个语法标记加以连接。原为指代词的“底”就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演化成为一个结构助词,来连接一个除数词之外的修饰语和中心语。我们所用的一个重要论据是,近代汉语中曾使用过的结构助词“个”原是一个普通的量词,大量的南方方言至今仍然用“个”做结构助词,广东开平方言甚至可用任何一个与中心名词相匹配的量词来作结构助词用。
但是,如果认为量词可以直接发展成为结构助词,那么我们会遇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类型学研究中,只有汉语是这样的语言。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论是历史还是当代方言的资料都表明,所有来自量词的结构助词也同时都有指代词的用法。那么,就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是否量词必须先引申为指代词,然后再虚化为结构助词?如果是这样的话,汉语的现象就符合人类语言的一般演化规律了。可是我们还要回答一个问题:量词和指代词之间的功能和语义特点相差甚远,两者之间的引申何以成为可能?本章就是尝试探讨量词(指代词(结构助词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7.2 指代词和结构助词
7.2.1 人类语言定语从句标记的共同来源
汉语结构助词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作定语从句标记。根据Hopper & Traugott (1993:190-1),人类语言的定语从句标记的来源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
(a) 零标记;
(b)指示代词;
(c)疑问代词;
(d)人称代词(特别是第三人称代词)。
他们还从话语篇章功能的角度论证了,指代词为何倾向于发展成为从句标记的原因。
上述四种类型都可以在汉语史或者方言中找到证据。例如:
一、零标记。这种现象自上古汉语的“之”衰落以后,从魏晋到唐末一直都很常见。例如:
(1)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世说新语·容止)
(2)问其所以,乃受炙人也。(世说新语·德行)
二、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上古汉语结构助词的“之”本来也是一个指示代词,中古汉语的“底”可以兼作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例如:
(3)之子于归,远送于野。(《诗经·邶风.燕燕》)
(4)之二虫又何知?(《庄子·逍遥游》)
(5)问谁姓字在底中居,云:陶靖节、白居易、邵尧夫。(竹斋词)
(6)竹篱茅舍,底是藏春处。(无名氏,蓦山溪词)
(7)个人讳底?”(《北齐书·徐之才》)
(8)单身如萤火,持底报郎恩?”(《欢文歌》)
三、人称代词。古汉语的第三人称代词“其”曾在历史上或者现代方言中用作结构助词。比如在福州方言中,状态形容词作定语时加“其”或者“喏其”(郑懿德1988),而相应的位置普通话则必须用“的”。XAA式形容词作定语时,必加“其、喏;AABB做定语,一般要加“喏”或者“喏其”。例如:
(9)(软软其布不好做。(软软的布不好剪裁)。(福州方言
ni21 nuo(21 nuo(21 k-(i53 pu(53 pu(213 (11 x(o21 ts-(.
(10)简简单单喏其事。(简简单单的事情)
ka(21 ka(21 ta(44 ta(44 lu(44 k-i53 tai231 k-i(213.
由此可见,汉语拥有人类语言从句标记的所有四种类型。但是很多汉语的从句标记起初都是一个普通的量词,这种来源在其它语言中是极为罕见的。下面我们来举例说明。
7.2.3 结构助词的量词用法
汉语历史和方言中存在的结构助词,大都是原来用作量词的。这又可以细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来自于绝大多数方言最普通的量词“个”;二是来自某个方言内部最普通的量词,但不是“个”;三是整个量词词类具有结构助词的功能。下面我们分别加以举例说明。
一、来自于普通量词“个”的结构助词
事实上,来自普通量词“个”的结构助词在近代汉语中一直是“底”的一个竞争形式。结果,“个”在许多南方方言中取得了胜利,而“底”则在北方方言中(包括普通话)成了唯一的结构助词。下边举例说明“个”在近代汉语和当代方言中的结构助词用法。
(11)好个人家男女,有什么罪过?(祖堂集·丹霞和尚)
(12)莫怪说,你个骨是乞骨。(张协状元第四出)
(13)食水个杯子拿转分我。(把喝水的杯子递还给我。)(平远客家话
(14)买票e22斡倒去唠。(买票的人回去了。)(泉州话
(15)做庄稼个蛮坐累=种庄稼的挺辛苦 (湖北金湖话
(16)a. 修钟表格工具 (上海话
b. 炒小菜格锅子
(17)你话个我唔懂。(31 va213 k( (o31 ( t((31. (湖南耒阳方言
(18)我是前年告北京个。ba31 si33 tsu(11 hi11 kau21 pak55 ki(31 kai11。(广东海
康方言
(19)做个酒(自制的酒) 补锅个(补锅匠) (江西高安话
(20)a. 做生理个 tsou53 s(n55 li53 kai53 (永定客家话
b. 做小头个 tsou53 sien53 t(eu55 kai53
(21)a. 只滴粒滚圆个 ts((55 ti(55 li(12 ku((34 (y(31 k((55 (嘉定方言
b. 部旧个 bu13 d(y31 k((55
(22) a. 煮个一锅(粥)(煮的这一锅粥)(信宜方言
ts(u35 k(33 l((13 tsek5 (ap33.
b. 我等个一部(车)(我等的这一辆车)
hei35 (ok5 k(33 (ei33 (13 tam33 sek1 fui53.
(23)跟实着红裙个女人。(紧紧跟着穿红裙子的那个女人。)(广州话
k(n55 ((t22 t((k33 ho(11 k(u(n11 k(33 n(y23 i(n11.
二、来自于其它普通量词的结构助词。绝大多数南方方言,直接用汉语中最普遍的量词“个”来充当结构助词。还有一些方言所采用的结构助词也有量词的用法,但是从音韵特征上看,与“个”的同源关系不太明显。比如,闽南话中的“兮”[e35],广州话中的“的”[ti55]。例如:
(24)a. 夷猪兮(宰猪的人)(闽南话
b. 绣兮花(绣的花)
(25)边个话我唔记得旧阵时的苦楚。(谁说我记不得从前的苦难?)(广州话
pin55 k(33 ua22 ((23 m21 kei33 t(k55 k(u22 ts(n33 si21 ti35 fu35 ts((35?
闽南话的“兮”[e35]也同时具有量词的用法,例如:一兮侬(一个人)、四兮羊(四只羊)、五兮笔(五支笔)(张振兴1983:133-134;张惠英1990)。从该量词的分布来看,它应该是该方言中最普通的量词之一,因为可以跟各种事物的名词搭配,但是与普通话“个”的功能显然有别。类似地,广州话中的“的”[ti55]也有量词的用法表示不定数(高华年1984:155;周小兵1997),例如:
(26) 渠炒左一的菜。(他炒了一些菜。) (广州话
k((y12 ts(au35 ts(35 j(t55 ti55 ts((i33.
三、整个量词词类可以作结构助词。以上两种情况都是最普通、最常用的那个量词演化成结构助词。第三种是整个量词词类全都兼有结构助词的功能,即在这些方言中用与中心名词相配的那个量词来承担普通话结构助词的功能。比如,绩溪方言(赵日新2001)和开平方言(余霭芹1995)都属于这一类。
(27)a. 担来写对联张红纸= 拿来写对联的那张红纸 (绩溪方言
b. 吃水药只茶杯=喝中药的那只茶杯
c. 我本书呢?= 我的那本书呢?
d. 这是老师副眼镜。= 这是老师的眼镜
(28)a. 我件帽=我的帽子 (广东开平方言
b. 我只手=我的手
c. 我个细佬卷书=我的弟弟的书
这个车佬件皮衫=这个开车的皮衣
7.2.4 量词的指代词用法
与上述量词引申作结构助词相平行的现象是,在近代汉语或者上述方言中,凡可用作结构助词的量词都可以作指代词用,功能相当于普通话的指示代词“这”或者“那”。这也可以分几种情况:一是最常用的量词“个”引申为指示代词;二是某个方言中的“个”以外某一个或者几个常用的量词具有指代词词的作用;三是整个量词词类都具有指代词的作用。下面我们分类加以说明。
一、“个”的指代词用法。“个”在近代汉语中和广大南方方言中,都同时可以引申为指代词。例如:
(29)个侬无赖是横波。(隋炀帝:嘲罗罗)
(30)个里多情侠少年。(王维:同比部杨员外夜游)
(31)伊迭能讲,葛倒是讨厌格。(上海话
(32)咯只好些。ko31 (ia35 x(31 (i55.(这个好些) (湖南耒阳方言
(33)a. 个是我的老师。 (鄂东方言
b. 这是我的,个是他的。
c. 个个人我不认得。
此外,张惠英(1990)年指出,客家话的“个个”意为“那个”,第一个“个”为指示代词。根据唐志东(1986),信宜话的近指代词是“个”[k(33],远指为“那”[na11]。
二、其它量词引申作指代词的用法。根据周小兵(1997),广州话的不定量词“的”也是一个指代词,如例(34)所示。又,根据颜清徽、刘丽华(1993),娄底方言的“只”和“个”也都具有指代词的用法,如例(35)所示。
(34)a. 唔该,的茶好香呙。(谢谢,这茶好香啊!)(广州话
m11 k(i55, ti55 ts(a11 hou35 h((55 w(33.
b. 的景色好靓。(这景色很美。)
ti55 ki(35 sik55 hou35 l((33.
(35)a. 个瞎子个手艺学不得个。 (娄底方言
ko35 xa13 ts( ko (io31 ni11 xo35 p(u13 te13 ko.
b. 只媒人公个话信不得个。
t(i(13 me13 nin13 k(( ko3 (11 sin35 p(u13 te13 ko3.
此外,根据张惠英(1994),厦门话中的量词“只”也可以用作指代词。
三、整个量词词类兼有指代词的作用。在相当多的南方方言中,所有的量词在特定的句法位置上都可具有指代词的作用。但是这种用法有一个限制,它们只能用于特定的句法位置,也就是说,通常出现于主语的位置上时,才具有指代词的用法表示有定。这一问题后文还将谈到。广州方言(施其生1996)、义乌方言(陈兴伟1992)、上海方言(杨剑桥1988)、苏州方言都是(石汝杰、刘丹青1985)都属于这一类型。下面举例说明。
(36)a. 驾车开走左好耐勒。(车开走了很长时间了。)(广州话
ka33 t(((55 h(i55 t((u35 t((35 hou35 n(i22 lak3.
b. 张刀生晒锈。(刀子长满了锈。)
t(((55 tou55 fa(55 (ai33 ((u33.
(37)a. 个表儿准极。(这个表很准)(义乌方言
b. 批货有问题。(这批货有问题。)
(38)a. 本书拨我。(这本书给我。)(上海方言
b. 支钢笔是啥人个?(这只钢笔是谁的?)
(39)a. 块让俚吃脱仔吧。(这块让他吃了吧。)(苏州方言
b. 枝个笔尖坏脱哉。(这个笔尖坏了。)
根据陈兴伟(1992)的调查,义乌方言中省略指示词的量词形式还可以单独使用。例如:
(40)甲:借支笔躬!(借支笔给我。)(义乌方言
乙:要哪支?(要哪支。)
甲:支。(这支。)
(41) 甲:买双鞋。 (义乌方言
乙:哪双?
甲:双。(这双。)
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量词用作结构助词和量词用作指示代词的分布区域是一样的,几乎存在于所有南方方言之中,包括吴方言、闽方言、粤方言、赣方言、客家话等,还包括部分靠近南方的北方官话,比如湖北方言等。但是由于受调查者所提供材料的限制,当具体到某一小方言点时,可能只提供了其中某一项用法的资料。但是绝大多数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某一特定方言中,可用作结构助词的量词同时也有指代词的用法。
7.3 量词向指代词转化的机制
7.3.1 量词的单一个体用法和向有定性转变的可能性
不管从语义特征还是分布功能上看,量词与指示代词都好象搭不上界。量词主要是描写事物的形状特征的,用于称数事物用,一般用于数词和名词之间。然而,指示代词则是称代事物的远近,可独用或者作修饰语,表示定指(definite),不能出现在数词之后。那么前者如何发展成后者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看一下Croft(1990:129)根据人类语言的共性对“高度有定性”(a greater degree of definiteness)所概括出的特征:
“高度有定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一是单一的个体,二是指示代词修饰。”
“数(number)”与“有定性(definiteness)”表达在很多语言中是相互关联的。比如,Aari语言中只有有定性名词才可以加上“数”的形态标记(Hayward 1990:442-5)。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Austronesian语中,该语言有三个冠词(article):一个是标记有定性名词的单数,一个是标记有定性名词的复数,还有一个是标记专有名词。这说明,无定名词不区别单复数(Klamer 1998:92,141)。同样,在Basque语言中有定性名词必须加上单复数标记,无定名词则不能(Lafitte 1962:55)。很多语言都反映出“数”与“有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Corbett 2000: 279)。总之,语言的有定性与数的表达密切相关,而在都为有定性的名词中,单数事物的有定性最高。
据此,我们可以打开解决问题的思路。先以普通话情况为例来说明。对于“数+量+名”短语,当“数”词为“一”时,即“名”代表的事物为单一的个体时,在宾语的位置上,“一”经常省略;但是在普通话里(北方方言),主语的位置则不允许这样做。例如:
(42)a. 我上街碰见个朋友。
b. *个朋友来看我。
(43)a. 我到图书馆借了本书。
b. *本书很有意思。
(44)a. 我最近刚刚买了台电脑。
b. *台电脑是新的。
也就是说,量词在特定的句法位置上,具有表示单一个体的功能,因而具备了表达“有定性” 的第一要素。但是在这个句法位置上的量词显然是表示“不定(indefinite)”的,那么它们是如何获取表示“有定”的指示代词的功能的呢?这一点还得从量词所使用的句法位置上去寻找答案。
根据语言类型学所概括的“高度有定性”的语义特征,可以解释汉语中很多令人费解的现象。比如,张惠英(1994)指出,闽北建阳、崇安以“一”作指示词,“一、个”是一组同义词,也可以认清闽南话近指词“即”实际上就是“一”的变读。“一”是一个具体的数字,“个”是一个普通的量词,两者却在表示指代词时成为了同义词,表面上看来非常让人难以理解。事实上它们都具有表示“单一个体”的语义特征,这是它们引申为表示有定性的共同基础。
还有一种更为有趣的现象,遵义话(胡光斌1989)中,名词后加上相应的量词可以表示“有定”,“名+量”短语可以出现在以下几种表示名词有定性的句法位置。
一、主语
(45)鸡个跑了。 (遵义话
(46)鞋双烂了,穿不得了。 (遵义话
(47)我的新衣服件着耗子咬烂了。 (遵义话
二、作“把”的宾语:
(48)把书本递过来下。 (遵义话
(49)牛把麦子个吃了。 (遵义话
(50)耗子把我的新衣服件都咬烂了。 (遵义话
三、作“是”的宾语。这样用时,“名+量”必有领属性定语,后边一般有后续小句。
(51)这是你的钢笔支,还你。 (遵义话
(52)这是我的衣服件,郎格跑到你这里来啦? (遵义话
遵义话中量词的上述用法,可以看作是名词的“有定性”后缀。有了普通语言学中“有定性”的定义,我们就不难理解量词的上述用法的来源,它们很可能是量词表单一个体的语义特征引申而来的。根据作者所提供的例子,有关的名词都是表示单一的个体。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于广州方言中(施其生1996),在那里有定的“量+名”的分布范围跟“指示代词+量+名”的重合。
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于北方话中。我们以“把”字结构为例来说明。一般来说,“把”后的名词所指的事物是有定的、已知的,或见于上文,或可以意会(吕叔湘1985:54)。从清代至今,“把”后的专有名词(包括人名和地名)常加上量词“个”,例如:
(53)话未说完,把个贾政气的面如金纸,大喝“快拿宝玉来!”(红楼梦三
十三回)
(54)到底要算蘅芜君沉着,“秋无迹”,“梦有之”,把个“忆”字竟烘染
出来了。(红楼梦三十八回)
(55)黛玉白日已经昏晕过去,却心头口中一丝微气不断,把个李纨和紫鹃哭
得死去活来。(红楼梦九十八回)
(56)宝玉虽也有些不好意思,还不理会,把个宝钗直臊的满脸飞红。(红楼
梦一百一十回)
(57)这一闹,把个荣国府闹得没上没下,没里没外。(红楼梦一百一十七
回)
专有名词自身的含义已经是有定的了,那么再加一个量词“个”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个”在这里的主要作用是通过表示“单一个体”,来加强表示有定性的程度。从上面例子可知,“把”后的名词加上“个”以后,是强调谓语动词作用的是这一个个体,而不是别的,从而加强了所指有定性的程度。比如,例(54)是说,“烘染”的是“忆”这个特定的字;例(56)是说最臊的是“宝钗”这个人,如此等等。我们观察了大量的用例,“把”后名词加“个”时,往往是强调受谓语动词作用的某个特定的个体。这些现象都与确定的个体具有高度有定性有关。
7.3.2 汉语的结构赋义规律和量词的有定性语义特征的获取
根据我们的研究(石毓智2001),汉语中存在一个“结构赋义规律”: 谓语动词之前的光杆名词(通常为主语)被自动赋予一个有定性语义特征,之后的(通常为宾语)则自动被赋予一个无定性特征。例如:
(58)a. 人来了。 b. 来人了。
(59)a. 书我看了。 b. 我看了书。
上述两例中a组的“人”和“书”所指都是交际双方共知的,因此是表示有定的;然而b组则可以指任何一个个体,是无定的。我们已经证明,这是一条严格的语法规律,强制作用于普通的光杆名词。
上述规律普遍作用于汉语的各方言。上面已经看到,在普通话里,当数词为“1”时,“量+名”短语可以在宾语的位置上出现,表示“无定”。量词本身在有定、无定的表达上是中性的,这里的“无定”含义是来自于结构赋义,即在宾语的位置上被自动赋予这个语义特征。如上例所示,普通话(北方方言)一般不允许“量+名”短语出现于谓语动词之前,因此它无法获得“有定”的语义特征。然而在广大南方方言中,当表示单一的个体时,“量+名”短语可以自由地出现在主语的位置上,受结构赋义规律的作用,表示有定的事物,功能相当于加上一个指示代词。
大量的方言研究报告指出,量词具有表示定指的作用,相当于一个指示代词。根据对从不同方言得来的大量有关资料的观察,我们很赞成杨剑桥(1988)的看法。他认为,其实量词自身并没有指示作用,这里的指示作用是由名词的主语地位决定的。其根据是,在吴语和粤语中“量+名”表定指的用法基本是在主语的位置,在宾语的位置相当少见。也就是说,这是汉语的结构赋义规律作用的结果,“量+名”短语自身只表示单一个体,有定性主要来自句法位置,两者合起来才具有定指的功能。下面我们分类举例说明。
根据方言文章所提供的例子和观察,“量+名”短语在以下方言中的定指用法,只限于谓语动词之前的位置,主要包括主语、话题和处置式中的受事。例如:
(60)只录音机啥人拿去勒。(那台录音机谁拿走了。)(上海话
(61)支笔不好写。(这支笔不好写。)(温州话
(62)本书奠你读。(这本书给你读。)(永康话
(63)张画雅绝。(这张画漂亮极了。)(闽方言
(64)个人肥肥。(这个人很胖。)(汕头话
(65)张纸克来。(那张纸拿来。)(潮州话
更有启发性的是贵州遵义方言。根据胡光斌(1989),该方言的“名+量”可以表示定指,但是只限于谓语动词之前,比如“鞋双烂了”意为“这双鞋烂了”,然而在谓语动词之后表定指时则必须加上含“有定”义的修饰语,比如“这是你的钢笔支,还你”。
第二种“量+名”短语表示定指的情况是,在主语的位置上表示定指,而在宾语的位置上则既可以表示“有定”,又可以表示“无定”。广州话(施其生1996)和义乌方言(陈兴伟1992)都属于这种类型。请看广州话的用例。
一、主语
(66)驾车开走左好耐勒。(车开走了很长时间了。) (广州话
ka33 t(((55 h(i55 t((u35 t((35 hou35 n(i22 lak3.
(67)张刀生晒锈。(刀子长满了锈。) (广州话
t(((55 tou55 fa(55 (ai33 ((u33.
二、宾语
(68)食埋支烟走人。(抽完这支烟就走。) (广州话
(ek22 mai11 t(i33 in55 t((u35 i(n11.
(69)渠唔小心打烂左只碗。(他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碗。) (广州话
k(U(y23 m11 (iu35 ((m55 ta35 lan22 t((35 t((k3 un35.
(70)畀杯茶我饮。(给我一杯茶喝。) (广州话
pei35 pui55 t((a11 ((23 i(m35.
在作者所提供的例子中,共有22个作宾语的例子,其中10例都是表示不定指的。相对的,15个“量+名”短语在主语位置的用法,全部都是表示定指。这说明定指跟不定指与句法位置密切有关。
我们认为在广大南方方言中“量+名”表定指的现象,是由其所出现的句法位置所赋予的,而不是自身所固有的。这一论断可以得到以下跨方言的证据的支持。
一、不允许“量+名”出现于谓语动词之前(特别主语位置)的方言,它们就没有表定指的用法。比如广大的北方方言就属于这种情况。
二、在有“量+名”表定指用法的方言中,定指用法限于或者主要出现于主语的位置,在宾语的位置上不用或者有定、无定两可。但是没有相反的情况。上面所看到的南方方言都属于此类。
量词的定指用法本来是结构赋义现象,而不是其词义本身所固有的。这种用法的长期和高频率使用会带来两种结果:一是表“有定”的意义最后永久固定在使用频率最高的那个量词上,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个”在很多方言中的指代用法,它已经相当于一个指代词,不再受句法位置的限制。二是很多量词都同时获得表有定的意义,它们的定指用法可以逐渐出现于宾语的位置,上面所讨论的广州话和义乌方言都属于这种情况。
7.4 量词向结构助词过渡的中间环(指代词
7.4.1 量词向结构助词发展的必须过程
上一部分的分析主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在所有量词可作结构助词的方言中,量词也同时兼有指示代词的用法。二是量词是在什么样的句法环境中获得指代词的用法的。本节将证明,量词不能直接发展成为结构助词,必须经过指代词这一中间环节,即其发展步骤为:
量词 ( 指代词 ( 结构助词
这一论断得到语言类型学、汉语的历史和方言资料、普通话指示代词的篇章话语功能等各个方面的支持。
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来看,结构助词的主要功能之一(从句定语标记普遍来自于指代词。比如英语中的从句标记that、which也都有指代词的用法。从汉语的内部来看,先后出现的两个最主要结构助词“之”和“底”原来都是指示代词。还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是,凡是引申作结构助词用法的量词也都有指代词的用法,但是很多结构助词原来并没有量词的用法。这种种事实都说明,指代词可能是量词向结构助词发展的必由一环。
普通量词“个”在近代汉语中发展出了指代词和结构助词的用法,这两种用法的发展顺序也很能说明问题。根据王力(1958),“个”的量词用法已见于汉代,比如:“木千章,竹竿万个(《史记·货殖列传》)。它的指代词用法最早见于隋唐初期的文献,然而结构助词的用法直到唐末的文献中才见到。例如:
(71)个侬无赖是横波。(隋炀帝:嘲罗罗)
(72)个人讳底?(《北齐书·徐之才》)
(73)问:“如何是皮?”师云:“分明个底。”(《祖堂集·镜清和尚》)
(74)好个人家男女,有什么罪过?(《祖堂集·丹霞和尚》)
也就是说,“个”的指代用法比其结构助词用法早出现了两、三百年的时间。
从当今活生生的方言材料也可以看出,量词用作结构助词时,明显带有指代词的语义特征。根据赵日新(2001),绩溪方言中的量词连接定语和中心语时,它们的作用相当于普通话的结构助词“的”加上指示代词“这/那”。下面是作者对该方言有关例子的普通话诠释。
(75)担来写对联张红纸 = 拿来写对联的那张红纸
(76)吃水药只茶杯= 喝中药的那只茶杯
(77)我本书呢?= 我的那本书呢?
7.4.2 指示代词与结构助词的功能上的相似性
上面的解释只是说明结构助词都来自指示代词,但是要说明为什么是这样,必须确定其间功能上的相似性。根据李讷、石毓智(1998),指示代词“这”或者“那”与结构助词“的”在功能上是相通的,它们很多时候可以互换,特别是在一些必须用“的”的偏正结构里,如果有了指示代词,“的”就可省,或者常常不出现。
下面是指示代词用作领格的例子。
(78) 谁喜欢吃你那糕! (六十四回)
(79) 你知道我这病,大夫不许多吃茶。 (六十二回)
(80) 我这枝并头的怎么不是“夫妻蕙”?(六十二回)
(81) 刚才我到琏二奶奶那边,看见二奶奶一脸的怒气。 (六十七回)
(82) 况且姑娘这病,原来素日忧虑过度,伤了血气。 (六十七回)
(83) 我这一社开的又不巧了,偏忘了这两日是他的生日。 (六十九回)
上述用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如果拿开这些指示代词,句子就成为不合语法了,比如不能说“谁喜欢吃你糕”、“我并头的怎么不是夫妻蕙”。二是,有些指示代词可以用“的”替换,比如例(78)可以说成为“谁喜欢吃你的糕”,有的则不能,比如不大能说“我的一社开的又不巧了”。可见,作领格的指示代词有自己的特殊的功能,与“的”的用法并不完全相同。
为了弄清作领格的指示代词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我们调查了6篇反映当今北京口语的王朔小说。总的特点是,其用法更加普遍化,而且也更加多样化。在收集到的97个用例中,“这”占60%,共57例,“那”占40%,共39例:“这”明显占优势。但是它们的用法看不出有明显的区别。先看一组“这”、“那”与“的”自由互用的例子。
(84)a. 我那设计师没饭局不来。(谁比谁傻多少)
b. 南希看似单纯,时而语惊四座,当然这都是她那个设计师的思想。(同上)
c. 我的设计师不吃烤鸭子。(同上)
d. 我说南希你的设计师是不是动乱念的中学?(同上)
在同样一部作品的同样一个短语中,时而用“那”,时而用“的”,可见它们的功能是有相同之处的。
汉语的语法规则要求,如果定语是一个从句,或者说是一个VP的话,必须用“的”加以标记。下面再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85) a. 这些都是朋友送给我的礼物。
b. * 这些都是朋友送给我礼物。
(86) a. 我今天买的书都在袋子里。
b. *我今天买书都在袋子里。
然而,中心语之前如有指示代词的话,这个“的”就不是必须的了。指示代词的这种用法没有其领格的普遍。我们从同样的6篇王朔作品中,只收集到14例这类用法。下面根据中心语的类型分别加以举例。
一、中心语为表示事物或者人的名词
(87)你过去还真是,怎么说呢?假模三道的,跟墙上贴那三好学生宣似的。
(刘慧芳)
(88)你瞧那边站那扬重没有?(一点正经没有)
(89)你们就是鼓吹“全盘西化”那帮吧?(同上)
二、中心语为时间或地点名词
(90) 西北食油管理局在我们插队那个地方招工,我就去了。(刘慧芳)
(91) 噢,慧芳,我们接触这段时间多有得罪,别往心里去。(同上)
(92) 老陈上班那天,编辑部的一帮人都很紧张。(懵然无知)
三、表事情、方式等抽象名词
(93) 你竟从深夜一点爬楼这件事情上感动于自己的力量。(王蒙:轮下)
(94) 最后,她不可避免地走上乱搞男女关系这条路。(谁比谁傻多少)
(95)赞助艺术家这名分还不够好、道理还不够多?(一点正经没有)
虽然收集到的例子不多,但是我们注意到指示代词作从句标记也是普通话口语中很常见的现象。比如在日常交际中会听到下面的说法:
(96) 会书法那位教授已经退休了。
(97) 这儿就是刚才我看书那个地方。
(98)我送那本书你看完了没有?
指示代词作从句标记的作用,相对而言还不是很稳固。其前还常常可以插入“的”,比如也可以说“墙上挂着的那张画”、“我送你的那本书”。不论怎么说,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指示代词和“的”都可以作为从句定语的标记。
指示代词跟结构助词功能上的相似性不仅见于普通话之中,而且也广泛存在于方言之中。比如赵日新(2001)指出, 绩溪方言中作定中结构标记的“的”通常写作“仂”,读[n(]。其实,这个“仂”就是一个指代词。又,宋作艳(2000)提到,山东沂源话的指代词“那”也有相当于结构助词“的”的用法。例如:
(99)a. 我仂皮夹忘记担了。(我的钱包忘记带了。)(绩溪方言
b. 渠在那搭学发豆芽勒技术。(他在学习发豆芽的技术。)
c. 过去仂事就不去讲渠了。(过去了的事就不要讲渠了。)
(100)a. 早晨那菜还有。(早晨的菜还有。)(沂源话
b. 我那书比你那书好。(我的书比你的书好。)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上述用法中的指代词已经虚化成为结构助词,这只是它们临时的语用现象,还有明显的指代词含义。但是,不难理解,指示代词在这些句法环境中长期使用的结果,具有语法化为结构助词的可能性。
7.4.3 结构助词语法化的程度差异
汉语方言(包括北方话)的结构助词都是从指示代词语法化而来的,但是它们的语法化程度参差不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指示代词的临时语用现象。指示代词在特定的句法环境中,可以临时引进领有者或者定语从句,同时还保留着很强的指代含义。北方话的指示代词、一些南方方言里整个量词词类可用作结构助词的现象,都属于这一类。
二、语法化程度较低的结构助词。在不少方言里,指示代词已经虚化为一个稳定的语法标记,但是它们在很多时候并不是必须的。比如,平远客话的结构助词“个”在引进副词修饰语或者状态形容词之后,都不是必须的,然而这些地方普通话则都需要一个“的”。例如:
(101)a. 教室肚里灵灵利利(个)。(平远客话
b. 你一只字一只字(个)读得我听。(你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给我听。)
同时,在这类方言中,结构助词还往往保留其指示代词的用法。
三、高度语法化的结构助词。指示代词已经完全变成了结构助词,在引进定语从句、领有修饰语、状态形容词之后,都成为一个必须的语法标记。与此同时,它已经完全退化掉原来指代词的用法。广大北方方言所使用的“的(底)”就是如此。
7.5 结语
本章从多个角度论证了量词、指代词和结构助词之间的关系。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看,很多语言的定语从句标记都是来自于指代词。汉语史上先后出现的最重要的两个结构助词(“之”和“底”(也都是来自其指代词的用法。与此同时,在近代汉语和广大南方方言中还存在着一种具有类型学研究价值的现象:普通量词虚化为结构助词。另外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这些普通量词也同时具有指代词的用法。我们从人类语言的共性、历史发展顺序和语用功能等角度,论证了量词向结构助词的发展必须经过指代词这一中间阶段。文章还根据句子的结构赋义规律,说明了汉语的量词如何能够获得表示定指的功能。
本章的分析所依据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有定性”的程度问题。根据语言类型学所概括出来的规律,定指的单一个体具有高有定性。这可以解释汉语史和汉语方言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这就是量词在表示单一个体的句法环境中演变成定指标记的原因,也是量词在一些方言中发展成为名词定指后缀的语义基础。
通过对本章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要弄清楚汉语中的某些语法现象,我们的视野不能拘泥于一个单一的系统,对不同系统的比较,往往可以帮助我们打开解决问题的思路。汉语研究的类型学视野,既可以是汉语和其它语言的比较研究,也可以是汉语不同方言之间的研究。汉语的方言语法是一个宝藏,其中所隐含的问题,具有普通语言学、特别是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意义。
参考文献
陈兴伟 1992,义乌方言量词前指示词与数词的省略,《中国语文》第3期206页。
高华年 1984,《广州方言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
胡光斌 1989,遵义话中的“名+量”,《中国语文》第2期124-125页。
李 讷、石毓智1998,指示代词与结构助词的共性及其历史渊源,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Vol. 33-2: 53-70.
李如龙 2001,闽南方言的结构助词,《语言研究》第2期48-56页。
吕叔湘 1985,《近代汉语指代词》,上海:学林出版社。
邵敬敏 徐烈炯 1998, 《上海方言语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
施其生 1996,广州方言的“量+名”组合,《方言》第2期113-118页。
石汝杰 刘丹青 1985,苏州方言量词的定指用法及其变调,《语言研究》第1期160-166页。
石毓智 2001,论汉语的句法结构和词汇标记之关系(有定和无定范畴对汉语句法
结构的影响,《当代语言学》第3期。
石毓智、李讷 1998,论助词“之”“者”和“底(的)”的兴替,《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165-180页。
宋作艳 2000,《沂源(悦庄)话中的指示代词》,北京大学本科学年论文。
唐志东 1986,信宜方言的指示词,《语言研究》第2期98-108页。
王 力 1958(1980), 《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
项梦冰 2001,关于东南方言结构助词的比较研究,《语言研究》第2期1-6页。
颜清徽 刘丽华 1993, 娄底方言的两个语法特点,《方言》年第1期65-68
页。
杨剑桥 1988,吴语“指示代词+量词”的省略式,《中国语文》第4期286页。
余霭芹,1995,广东开平方言的“的”字结构--从“者”、“之”分工谈到语法类型分布,《中国语文》1995 年第 4 期,第 289-297页。
赵日新 2001,绩溪方言的结构助词,《语言研究》第2期30-36页。
张惠英 1990,广州方言词考释(二),《方言》第4期293-306页。
张惠英 1994,闽南方言常用指示词考释,《方言》第3期212-217页。
张振兴 1983,《台湾闽南话记略》,福建人民出版社。
郑懿德 1988, 福州方言形容词重叠式,《方言》第4期301-311页。
郑懿德 1988,福州方言“礼”的词性及其用法,《中国语文》第6期450-452页。
周小兵 1997,广州话量词的定指功能,《方言》第1期45-47页。
Corbett, Greville G. 2000. Nu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oft, William. 1993.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yward, Richard J. 1990. Notes on the Aari language. In: Richard J. Hayward (ed.) Omotic Language Studies, 425-93.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lamer, Marian. 1998. A Grammar of Kambera (Mouton Grammar Library 18).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Lafitte, Pierre. 1962. Grammaire Basque (Navarro-Labourdin Litte(raire). Donostia: Elk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