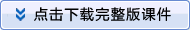第7讲 社会转型与政治转轨
摘 要:不同的社会型态对应不同的政策范式,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政策困顿需要公共政策的创新回应。“回应型+维护型”二元治理结构背景下的政策转轨是一个复杂的创新系统工程,要实现不协调成本最小化、改革福利最大化,就必须寻求“平行推进”和“循序渐进”相结合的创新路径。从政治层面上来说,中国的政策转轨实践必须突破“政治制度化不足”和“制度化政治僵化”两大顽疾。
关键词:社会转型 政策转轨 政治制度化 制度化政治
一 社会型态与公共政策范式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按照社会的秩序状况简单地把社会型态划分为常态社会和非常态社会。一般来说,常态社会表征为制度规范、社会理性、政局稳定、生活有序,非常态社会表征为制度混沌、社会病态、问题丛生、生活无序。为此,为了巩固公共权力机构的权威地位和建构良性的社会秩序,不同型态的社会类型要求不同的“宏观性”公共物品。比如,针对常态型社会所对应的相对正态的公共事务就必然需要维护型公共政策,也必然要求常规性的、程序化的公共管理;与此相反,针对非常态型社会所对应的相对病态的公共事务就必然需要回应型公共政策,也必然要求非程序化的公共管理或危机管理(见表1)。当然,这种“两分法”不是截然对立的,比如常态社会亦存在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也需要回应型政策和危机管理,且在一定的时间段比较突出,如美国的“911事件”、中国的SARS危机等,只不过相对于非常态社会而言它所表露的显度、频率、强度较轻较少而已。同时,我们发现一个社会并非只是“静止地”存在仅有的两种社会型态,还存在着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常态、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非常态的“过渡”型态,即通常所谓的“转型社会”。其实,转型社会是隐含的、必需的社会型态形式,任何社会变迁都无法摆脱这一阶段。
表1 不同社会型态下宏观性公共物品的提供方式
公共物品
常态社会
非常态社会
公共事务
公共政策
公共管理
正态
维护性
常规管理
负态或病态
回应性
危机管理
根据常态与非常态性质不同的社会型态,我们可以发现转型社会可能存在四种转换形态,即非常态到常态的过渡类型(A类)、常态到非常态的过渡类型(B类)、常态到常态的过渡类型(C类)、非常态到非常态的过渡类型(D类)(见图1)。例如,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军阀割据到国家统一、从殖民半殖民到国家独立等弱势转换成强势、负态转换成正态就属于A类转型形态;从强大无比的封建王朝到衰败破落的殖民半殖民,从国家独立、民族团结到任人宰割、民族分裂等诸如此类强势转换成弱势、正态转换成负态就属于B类转型形态;依此类推,由一种强势形态转换成另一种强势形态或从一种正态转换成另一种正态就属于C类转型形态,由一种弱势形态转变成另一种弱势形态或从一种负态转换成另一种负态就属于D类转型形态。相比较而言,A、B两类属于重度转型,C、D两类属于轻度转型,它们所引发的社会振动幅度显然不一样。从四种形态来看,B、D是公众最不愿意看到和接受的,而公众经常讨论的也就是A、C两类。那么,在正常时期的转型社会通常指的就是C类,即在良好的统治秩序下社会形态从一种正态转换成另外一种正态。一般而言,这种转换形态基本上涉及体制的转轨、制度的变迁、观念的变更,而不涉及“伤筋动骨”颠覆式的政权更替,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规则”的形态变换。
非常态――――→常态(A)
常态――――→非常态(B)
常态―――――→常态(C)
非常态―――→非常态(D)
图1 转型社会的不同转换形态
不同的社会型态需要不同的公共政策范式。比如,按照上述宏观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常态社会更多地需要维护型公共政策范式,那就是根据社会公共事务的正常要求通过公共政策工具开展维护性的常规化管理;而非常态社会更多地需要回应型公共政策范式,那就是针对复杂多变的公共事务通过公共政策工具进行回应性的非程序化管理。因此,维护型政策范式与回应型政策范式是“有机社会”当中两种常见的公共政策范式。根据著名政策科学家叶海卡?德洛尔(Yehezkel Dror)提出的三种公共政策制定类型,即“繁荣时期的政策制定”、“严重逆境中的政策制定”和“巨大灾难形势下的政策制定”,[1]我们也可以推导出社会共同体所存在的三种公共政策范式:顺境型政策范式、逆境型政策范式和危机型政策范式。国内学者胡宁生教授依据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对法律范式所进行的一般性划分而把公共政策范式区分为压制型政策范式、自治型政策范式、回应型政策范式三种类型[2](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公共政策一般表现为“准法律”,重大的、稳定的、成熟的公共政策会转化成法律,因而法律范式与政策范式从一定程度上讲是一致的)。德洛尔、塞尔兹尼克以及胡宁生的著述对于我们理解公共政策范式类型提供了积极的理论思考和有用的学术支持,对转型社会的公共政策范式形态提供了适当的类型参照。但不管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对公共政策范式进行解构,无论是德洛尔的“社会具体情境”,还是塞尔兹尼克的“公共治理方式”,都可回归到“维护型”与“回应型”这两种基本的范式类型当中来。
那么,转型社会的公共政策范式又如何呢?从一种常态过渡到另一种常态所谓“规则”的社会转型,与其他相对“非规则”的社会转型一样,裂痕、冲突、对抗都是在所难免的。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公共权力机构一方面通过传统公共政策范式去维系社会原有格局,另一方面又急欲寻找新的公共政策范式去弥合新出现的“缝隙”以及“非对称”的社会状况,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范式守护、范式冲突和范式叠加,所谓的“双轨制”就是这一阶段的特色产物。作者认为,转型社会的公共政策范式基本上呈现为“维护型+回应型”的所谓“双轨制”二元型政策范式。这种范式表明:(1)人们留恋既存的社会型态,希望维持原有利益格局,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进行风险性制度转换,因而“政策格式”表征为信息垄断、决策单一、沟通阻滞、执行刚性;(2)随着新的事物、新的情况不断地出现,旧的平衡慢慢打破,旧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此时的“政策格式”表征为主体分化、信息失衡、执行无序、效率缺失;(3)在社会“混沌”状态越来越明显的情形下,政策受益者与政策受损者分化严重,受益者既希望享有原有格局所得的既成政策利益,又希望在转型中获得更多的政策收益,因而期冀享受政策“双轨制”的“差价”好处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权力、声望等更多资源;(4)在“制度阻隔”愈来愈严重的情况下,新型的、理性的制度秩序安排成为政策议程,由“政策断裂”走向政策均衡,突破政策双轨制“瓶颈”已经必不可少,公共政策创新成为可能,渐进式增量改革成为理想的路径选择,公共政策的回应力显得特别重要。
二 转型期的政策困顿及其创新回应
对社会转型作出研究的主要集中于社会学学者,而经济学学者则偏向于从“过渡”或“转轨”来表达社会的转型[3]。在学者们的学术视野中,“过渡”或“转轨”的涵义基本上描述的是从一种制度安排转变到另一种制度安排、从一种实践模式转变到另一种实践模式。根据经济学家科勒德克的估计,目前已有35个国家、占世界1/4的人口,被卷入了这场转轨变革中[4]。经济学家科尔奈(J.Kornai)对这种转轨经济的趋势作了概要性的论述,他认为转轨经济的趋势主要有市场化、私营部门的发展、宏观非均衡的再生产、一个立宪政体的发展、民主制度的发展、民族团体的重新定义、福利提高中的不公平等七种[5]。科尔奈所预测和描述的这些趋势很好地说明了社会转型的基本特点,其中也蕴含着社会转型中旧体制与新体制的冲突与融合,反映了转型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非静止与非均衡状况。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转型主要体现为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转的转轨,因而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形成了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凸显了体制转轨的中国案例和独特经验。这种独特性表现在:第一,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性的,在改革进行了20多年后的今天,居于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原来的政体和意识形态;第二,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的,许多重要的改革和转型过程是使用变通的方式实现的;第三,在变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开始的阶段,新的体制因素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现并传播的;第四,非正式体制的生长和发育,往往是发生在体制运作的过程当中。[6]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市场经济过渡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这样就规定了市场化的可能性边界和一般约束条件;同时,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会反过来推动政策、法律和制度的一些变化。经济学学者张宇认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最重要的特征和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它把市场化、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三重重大的社会转型浓缩在了同一个历史时代,在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双重约束下推进市场化[7]。
由于“可能性边界”与“一般约束条件”的存在,也由于制度环境的非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在由计划模式(旧体制)转为市场模式(新体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政策困顿与制度失范,“转移性制度效益缺失”、“二元治理”、“时空错位”等现象就是例证。所谓“转移性制度效益缺失”指的是原有的公共政策与其他制度形态随着政策或制度语境的变换而遭遇“侵蚀”乃至于“失语”,比如计划时期的粮食供给制度和原有完善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同时,新的政策或制度出台刚开始由于固有阻力或动员不力等原因也使政策转移产生低效或无效,比如农村费改税政策的最初推行等等。所谓“二元治理”指的是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同时使用计划与市场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公共治理模式,即如上述所言的公共政策“双轨制”二元化现象——新老结合、并行不轨,比如高等教育政策中的公费(计划内)与自费(计划外)的区别、价格政策中的“指标”(计划价)与“黑市”(市场价)的差异、开放政策中的特区与非特区的设置以及“城乡分治,一国两策”[8]的现状等等。所谓“时空错位”指的是政策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而政策文本却固守不变,此所谓“语境的转换与文本的固化”现象,因而导致了公共政策时间与空间上的相对不一致,也说明了公共政策的惰性、刚性与不适应性的事实存在,比如户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等等。
转型社会所出现的公共政策困顿,很明显与政策变迁中的政策时滞相关,与相关利益主体参与的政策博弈相关……总而言之,政策困顿的出现与政策系统内外的变量及其博弈状况有关。从“二元治理”和“时空错位”来看,政策困顿现象反映了体制内不同政策之间以及政策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不协调,从而加大了“不协调成本”(incoherence cost)[9]。这种“不协调成本”的产生和增大,可能源于以下方面的原因:(1)旧政策的惰性、刚性和惯性或政策既得利益者的强大势力及其阻碍导致政策沉淀成本加大;(2)新政策没有及时展开,或观望等待的时间过长,从而导致“政策滞后”;(3)由于政策目标和政策质量存在问题,可能导致“政策超前”或“政策失误”;(4)政策改革战略选择错位,政策改革技术粗糙;(5)政策系统内各要素的改变速度或新要素的“成长速度”存在差异;(6)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政策资源不均衡,政策之间的摩擦成本增高;(7)政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压力;等等。由于多数的体制改革和政策建设是需要时间的,因此不协调成本总是会存在的。面对全球化、市场化与WTO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政策改革的不协调成本还会继续增加,这种局势必须是我们所清醒地认识到的。
我们知道,在二元型双轨制公共政策范式的作用下以及公共政策出现大面积耗损导致“不协调成本”迅速增加的情形下,公共权力机构必须而且应当作出策略性回应,从而形成回应型公共政策创新。公共管理学者格洛威?斯塔林(Grover Starling)认为,回应(responsiveness)一词是指公共组织快速了解民众的需求,不仅“回应”民众先前表达的需求,更应洞识先机,以前瞻主动的行为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民众常常批评政府行动迟缓、犹豫不决、无能为力,便指的是政府的回应力不够。[10]著名学者俞可平先生也认为,回应的基本意义是,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的和负责任的反应,不得无故拖延或没有下文。在必要时还应当定期地、主动地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回应性越大,善治的程度也就越高[11]。由此,回应型公共政策主要表现为政策对外界的反应能力,对来自政策环境及基层、民众的信息的反馈速度,对公共问题、突发性事件的应急水平。比如,基于SARS危机所建构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基于“孙志刚事件”由原来的《生活无着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而代之以《生活无着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些都是回应型公共政策在具体实践中的及时与有效表达。近几年来,中国公共政策的人性化与文明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公共政策的人本性与回应性的特点越来越突出,我们可以从艾滋病人可以结婚、取消婚检、结婚离婚无需单位介绍信、WHO针对娱乐场所的100%使用安全套试点、公务员招考中的“乙肝歧视”突破等等方面感受出来。如今,阻碍中国人才流动的带有身份歧视的户籍制度已经慢慢消融,而被认为人才流动另一大阻碍的同样也带有身份歧视的传统人事档案制度也很有必要进行创新了,因为它有可能成为中国纵深改革中的“瓶颈”或改革木桶原理中“最短的一块木板”。
由此,公共政策要走出转型期的困境,消除“政策硬化症”[12],就必须因时而变、适时创新。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经典定义,创新就是“实施新的组合方式”(新的商品、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市场以及新的组织)。[13]那么,作为社会创新之一的公共政策创新就是基于旧政策老化失效的情况下,寻求新的政策组合方式,选择成本小、收效快的组合路径,探索良性的政策替代方案,从而尽量减少不协调成本、摆脱转轨阶段的政策困境,使适应相关制度环境的、新型的公共政策回到常态社会当中来。
三 政策创新的转轨路径
在体制转轨的最优路径问题上,经济学者樊纲、胡永泰的《“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进”?——论体制转轨最优路径的理论与政策》对于政策创新的转轨路径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考。我们知道,“循序渐进”(sequencing)是一个历时性概念,其目的是尽可能避免因过激方式而造成损失最大化,从而寻求政策创新的平稳过渡。循序渐进理论的基本内容是:改革政策B应当在改革A完成以后才能实行,B体制的实现以A体制的形成为前提条件。[14]政策转轨循序渐进路径可以图示为:
循序渐进:政策A→政策B→政策C
图2 循序渐进的体制转轨路径
“平行推进”(parallel partial progression,PPP)是一个共时性概念,它的目的是尽可能降低政策创新的“不协调成本”、寻求“改革过程的福利最大化”。所谓“平行推进”,就是指改革政策A、B、C互为前提、互为条件,改革同时逐步展开,而不是等一个政策改革搞完再搞另一个政策的改革。“平行推进”的涵义,就在于在各个领域内同时进行这部分的改革,尽可能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阻碍。[15]理想化的(“完美的”)政策转轨平行推进路径可以图示为:
政策A:10%A→15%A→25%A→…
↑ ↑ ↑
↓ ↓ ↓
政策B:10%B→15%B→25%B→…
↑ ↑ ↑
↓ ↓ ↓
政策C:10%C→15%C→25%C→…
0—————————→t
图3 平行推进的体制转轨路径[16]
循序渐进转轨路径最大的优点是过渡平稳,但最大的缺点是不协调成本大。平行推进转轨路径的最大优势恰恰是尽可能地降低不协调成本,从而获取最大化改革福利。当然,平行推进的风险也是最大的,因为“在所有的制度领域尽可能早地开始推进改革”有可能由于时机把握不准、战线拉得过长、横向投入过大,没有集中精力解决“瓶颈”问题而导致整个体制改革的“早夭”。在体制变革过程中,究竟是采取“循序渐进”创新战略还是实行“平行推进”创新战略呢?实际上,转轨实践是一个具体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完全没有必要过分地把两者“绝对化”运用。樊纲、胡永泰认为,在对待某一方面、某一种具体体制的改革进程中,技术上先做什么、在做什么的“顺序”当然是重要的问题。但是在考虑一个制度体系整体改革的过程时,关键的问题不在于顺序,而在于“协调”。[17]从历时性角度和改革的纵向层面来说,在某项政策实施方式上的可能执行策略为循序渐进,比如开放政策的推行就是如此。纵观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发现其政策演绎轨迹是:点→线→块。首先,设立四个经济特区,给予相当优惠的特区政策,这是早期的改革开放之“点”状格局;其次,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开发上海浦东,继而进入沿海-沿江—沿边的改革开放之“线”状格局;最后,特别是近些年来国家相继推出“开发大西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的政策战略,于是连同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改革开放之“块”状格局。这种由“点”到“线”到“块”的政策格局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自然的逻辑推演过程,是梯度发展理论实践的典型中国案例。显然,从具体政策实施的过程层面而言,“点”是试验,“线”乃推广,“块”为普及,从而亦步亦趋构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改革开放战略蓝图。[18]
从共时性角度和横向层面来说,体制系统内的各政策及其要素转轨模式或执行策略应该是“平行推进”。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和市场要素不断流动的时代里,我们有理由相信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同步协调,但是,迫于转轨的意识形态风险和时局稳定的压力,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远远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转轨经济中“强政府”的正面效应和市场化改革要求实现宪政约束下的有限政府的冲突已经出现。腐败现象、农民负担过重、中央与地方利益冲突、公司治理结构难以改善、产权保护不足等等问题,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相关,因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中国整体改革进程中的最大瓶颈。同样,统一市场体系的形成除了商品、资本、产权等要素的流动之外,人才要素的流动也特别重要,于是户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的改革也理所当然地进入“配套式改革”的政策议程和改革行动之中。然而,涉及政治体制内的制度改革往往表现为“怕出乱子”的求稳心态而搁置一边,一种等待观望、亦步亦趋的“非不得已”策略加大了改革过程中的不协调成本,转轨实践的强政府特征及其强政治约束使得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一般性被减弱。由于没能在“正常时间”内足够快地推进改革,户籍制度和人事档案制度改革已经明显滞后,从而有可能成为限制其他领域改革乃至整个国家发展“木桶原理”中的最短的“一块木板”。如果当初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逐步“平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今天已经改革了的经济体制就会更有效率和效益。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体制转轨就是政策转轨、制度转轨,但很明显,体制转轨是一个包含政策A、政策B、政策C……等众多政策转轨的过程。相对于不同领域的多项政策转轨而言,单项政策内部的转轨又有其自身的转轨路径或转轨轨迹,在社会转型时期通常以新旧两种政策形态的“二元转换”模型表现出来(见图4)。从时序和过程来说,这种转轨是一种包含“接触渗入”、“摩擦磨合”、“创新替代”的循序渐进过程。在图4中,以黑色圆圈表示旧政策,以白色圆圈表示新政策,在初始阶段,旧政策占有绝对优势,新政策只能进行尝试性“接触”和逐步向旧政策“渗入”的状态,相对新政策来说,这一阶段是一个动员化阶段;在中间阶段,新政策和旧政策势均力敌,处于非合作博弈下的“摩擦”和合作博弈下的“磨合”状态,这一阶段也是一个调适化阶段;在终程阶段,新政策占有绝对优势,旧政策慢慢退隐,从而进入了一个“创新替代”时段,这个时段也是一个逐步制度化阶段。由此可见,政策转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有始有终的内部演化过程,其目的就是实现政策替代,但旧政策的退出和新政策的替代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旧政策的守护者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固化已有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模式,而且还可能会对新政策的实施作出种种阻碍,从而导致转轨成本增加和改革的难产。面对政策转轨的复杂性、艰巨性和系统性,作为政策创新者(包括政策规划者、设计者——我们也可谓之为“政策工程师”)必须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要充分考察创新的边界与约束条件,选择合适的创新时机、方式、技术和策略,衡量创新的成本与效益比较。同时,也说明政策转轨的过程只能选择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其目的是把转轨成本降到最低,使创新效益发挥到最佳最大状态。由此,政策转轨的过渡性和政策创新的回应性是社会改革转型的必然趋势和必定要求,回应型公共政策的质量和转轨速率构成了社会转型增量函数中的重要变量。
A.接触渗入 B.摩擦磨合 C.创新替代
图4 公共政策二元转轨演绎轨迹
四 政治制度化与制度化政治
如前所述,社会的转型、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公共政策的有效安排以及政治的作为。一提到“政治”,很多人便想到“权力斗争”、“阶级压迫”、“思想汇报”、“学习总结”等等。实质上,政治并非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而且“政治不能被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19]。作为社会的一个纬度,政治与经济、文化一样都是人类社会的实质性内容,它是围绕公共产品供求状况而开展的公共事务管理。这种放大了的政治概念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一是公共资源配置或公共产品供给;二是公共事务管理或公共危机处理。在政治形态的范畴中,政治制度化和制度化政治是社会实现有效公共管理不可回避的两大要素。简单地说,所谓政治制度化即政治组织、政治行为及其过程的制度化,它是政治资源合理配置所依赖政策或法律时的规划化保障,是对复杂的公共事务进行系统的制度简化处理的过程和形态;所谓制度化政治即已制度化的若干政治组织、政治体制、政治行为和政治程序,它反映了处于制度化状态下社会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事务管理的现实状况。
在人类早期的原始社会里,单个的人无法抵御野兽和洪水等自然的威胁,他们必须团结并组织起来共同抵御来自外界的“恶行”,同时也必须实行“扶老携幼”的具体措施以调节内部成员的实物分配,于是以自然共同体内部的公共事务为对象产生了原初的、小规模的政治共同体及其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的公共管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民族、宗教、地域、经济或社会身份等社会力量猛增并呈现多元化趋势,为了维持秩序、解决争论、遴选权威领导人而作出政治组织或程序的安排成为必要。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叙述道:“从历史上看,政治体制的出现是由于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分歧,以及为解决这些分歧而采用的程序和组织手段的逐步发展,规模小、成分划一的统治阶级的解体、社会力量的多元化,以及这些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增强,是政治组织手段和程序的出现,继而最终建立政治体制的先决条件”。[20]然而,政治体制要走向稳定和谐并最终建构政治均衡就必须寻求政治的制度化,政治制度化水平决定着政治体制的稳定性、政治结构的均衡性和政治现代化的先进性。因为,“复杂社会中的政治共同性取决于该社会中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力量;转而,这种力量又依赖于这些组织和程序所得到的支持范围及其制度化水平”[21],“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借以取得重要性和稳定性的过程”[22],同时“具有高度制度化的统治组织和程序的社会能够更清楚地表达和实现公共利益”[23]。那么,政治制度化水平通过什么样的维度来衡量呢?亨廷顿认为,“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都表现在其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一致性上。同样,任何特定组织或程序的制度化水平,都能以其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一致性衡量。”[24]
政治制度化的目的就是要诉求和谐社会的政治均衡,力求通过公共政策和法律强化政治生活或政治系统的制度处理。比如,在政治参与问题上,就需要拓宽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参与渠道,使其政治愿望、经济诉求、社会权益都能通过合法的渠道输入政治系统,从而减少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再比如,在人事管理问题上,就需要建构选拔、录用、培训、使用等方面的人才制度,需要具体的人事档案制度来进行技能业绩、工作经历等方面的簿记式管理,从而减少非制度化的随意性人事行政。按照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模型,政治制度化是这样一个过程:要求和支持输入政治系统,经过转换过程成为政治系统的输出(图5),从而对社会作出权威性的价值分配。以人事档案制度为例,由于当时外在环境和时局的压力“要求”作为新政权的政治系统作出反应,加之内渗于强力政权的动员技术“支持”着政治系统的作为,因而全面推行的人事档案制度成为了政治系统输出的政治产品。显然,这种理性化的政治产品是政治制度化的必然结果,政治系统的权威性输出和相关性输出构成了政治制度化的有机形态(表2)。由此,政治系统通过输入—转换—输出的制度化路径在非均衡—均衡—非均衡的不断变动演化中向前发展。
表2 政治系统的输出类型[25]
性质
陈述
执行
权威性
相关性
约束性的决议、法令、规章、命令
和司法决议
政策、基本理论和许诺
有约束力的行动
利益和恩惠
要求 决策与行动
输入 输出
支持
环 境
反馈
图5 政治系统的简化系统[26]
实质上,政治的制度化形成了制度化政治。可以说,制度化政治是一种依赖制度规则而形成的比较凝固的政治形态,是一种人人都必须遵守的制度陈述(包括政策和法律等)和制度执行。但是,制度化政治绝对不是一种僵化的政治,它必须是一种环境适应性较强的、不断创新的政治形态。在伊斯顿的政治系统模型中,由输入—转换—输出的行动路径不是一个单向的简易流动过程,输出是一个流程的环节但远不是整个流程的终点,因为一次结果的“输出”反馈给政治系统又变成了新的“输入”。这个时候,可能明显感觉到“输出是一种特殊的刺激。它们为成员提供某种利益,反过来,由于这种刺激就可以指望成员提供支持;或者输出可能给成员强加某种明摆着的不利,如现行的繁重租税和苛刻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料,它们将成为政治目标的反对者,并增大消极性支持”[27]。政治系统与环境的反馈刺激形成了一种交动的局面并产生着多样化的反馈环。为了重新达致政治系统的均衡,创新政治系统的公共管理体制和有效修正输出制造者的输出已经成为必要,从而实现伊斯顿所言的“缓减现存的不满”或“预期未来的不满”、削弱“消极性支持”和“诱发错误性感知”。
制度化政治是一种均衡—非均衡—均衡的递进演化的政治形态,这种政治演化必然遵循着制度变迁的逻辑和规律,同时也内含着公共政策变迁的逻辑。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个人和组织都要学习。个人要学习如何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社会要学习哪种制度更有效,组织要学习如何适应环境。[28]与转轨经济内涵一样,从非均衡政治到均衡政治必然是转轨政治,这种转轨政治仍然需要学习,特别需要学习和吸收人类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从而建构良好的政治治理结构和走向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可持续的政治文明。人事档案制度建构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化政治形态,为一定时期内的干部管理、国家安全、社会信用作出积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加速的今天,刚性固化的人事档案制度显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人才流动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有人说它的继续存在只能构筑坚硬的“人才壁垒”,有人说它是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体制阑尾”,有人说它已经成为了可有可无的“鸡肋”,不论如何,这种过高的制度成本已经成为了转型中国“下一步”的政策改革回应的焦点,干部制度和人事档案制度实现由身份型走向信用型的政策转轨已经不可避免!
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显得顾虑重重、步履蹒跚,一种双轨制式的政治治理结构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现实。因此,中国的政策转轨实践和转轨政治学研究必须解决如下两大突出问题:一是政治制度化不足;二是制度化政治僵化。
参考文献:
[1]参见叶海卡?德洛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王满传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2]详见胡宁生:“体制转轨阶段公共政策创新特点分析”,《江海学刊》2003年第4期,第107~113页;亦可参见《公共行政》2003年第5期,第55~57页。
[3]“转轨”与“转型”经常混义使用,但也有所区别。所谓“转轨”(transition)一般多指体制的转变、模式的变更;所谓“转型”(transformation)一般侧重包括体制在内的制度以及社会其它方面如观念等的转换。不论转轨还是转型,它们基本上都是制度变换或社会创新的过渡进化形态。关于经济学学者对于“过渡”或“转轨”的理解和论述,可以参见雅诺什?科尔奈的《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张宇的《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吕炜的《经济转轨的过程与效率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
[4]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
[5]详见亚诺什?科尔奈:《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肖梦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3~70页。
[6]孙立平:《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三农中国2005-04-15。
[7]张宇:《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8]“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对香港、澳门等历史遗留问题的一种公共政策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经典案例。而在中国还有一种明显的公共政策现象就是“城乡分治,一国两策”,城市与乡村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采取两种不同的公共政策与公共物品安排,造成了不同的公共治理结果,致使城乡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此所谓“二元结构社会”。最先提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话语命题的学者是陆学艺先生,可参见其文《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载其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242页。
[9]科尔奈最早在体制转轨的研究中提出了“体制之间的相互协调问题(coherence)”的问题。一个经济体系中各体制之间的相互兼容和相互协调,是一个稳定的体系性的重要保证,也是这个体制有效运行的基本保证。各体制之间相互不协调,就会出现混乱,从而破坏效率,使经济增长率下降。我们称这种由“体制间不协调”所引起的无效率,称为“混乱的效率损失”(efficiency loss of chaos),或称为“不协调成本”(incoherence cost)。事实上,这种“不协调”在社会科学中是一个普遍被讨论的问题。政治学称其为“社会冲突”(social conflict),而社会学家称其为“认知无序”(cognitive dissonance)。参见樊纲、胡永泰:《“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进”?——论体制转轨最优路径的理论与政策》,《经济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0]Grover Starling,Managing Public Sector(3rd.ed),Chicago,Illinois:Dorsey.p.115~125.转引自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页。
[1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12]作者将这种因“时空错位”导致的公共政策时间与空间的相对不一致性或者公共政策环境的不适应性而表现出来的惰性、刚性,称之为“政策硬化症”。
[13]转引自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陈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14]樊纲、胡永泰:《“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进”?——论体制转轨最优路径的理论与政策》,《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
[15]樊纲、胡永泰:《“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进”?——论体制转轨最优路径的理论与政策》,《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
[16]图4中横坐标t代表时间,是指改革开始后的一系列时点;竖的箭头表示体制之间的相互依存与相互协调。图中的所有数字都是随机假设的,并无真实意义,但它们要表示的是在改革开始后的各个阶段上各体制之间的改革相互协调,从而使“不协调成本”最小。参见樊纲、胡永泰:《“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进”?——论体制转轨最优路径的理论与政策》,《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
[17]樊纲、胡永泰:《“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进”?——论体制转轨最优路径的理论与政策》,《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
[18]陈潭:《“子女成长论”与中部崛起的政策构造》,《湘声报》2005-03-17。
[19]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20]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21]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22]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23]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24]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25]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页。
[26]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27]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457页。
[28]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关于转轨问题的几个建议》,载孙宽平:《转轨、规制与制度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