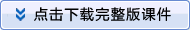中国的劳动分工为何难发展主持人:追求进步、学术倾听,世纪大讲堂问候您,我们知道李约瑟写过《中国科技发展史》,亚当·斯密写过《国富论》,在一般人看来,这两个人之间毫无关系,但是有的人就想把他们拿捏在一起说事。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陈平教授。好,今天我把他请到场,让他说一说这两个人有什么关系,好,有请陈教授上场。请坐。在咱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想跟您说点家常话。
陈 平:好。
主持人:我想问问您,您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陈 平:50多岁了吧。
主持人:50多岁了,那有一个秘诀应该传授给我们。我34岁的时候还认为我会永远像您一样瘦下去,但是,35岁突然就胖起来了。
陈 平:这个秘诀很简单,我的老师普里高津跟我讲,不是老师教学生,而是学生教老师,所以如果我能永远从学生那里学习的话,我第一永远年轻。第二呢,永远不会变胖。
主持人:这我就听不懂了。一般来说,从外界摄取东西多的话,他就会更丰富,从体型上来说也会变胖。
陈 平:你要知道,年轻人给老一点的人的挑战是让你足够伤脑筋、让你想问题的;然后你就睡不着觉,你就不会长胖。
主持人:是这样。我大致看了一下您的履历,我发现您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统统没有研究过经济,都是研究物理,怎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经济话题呢?
陈 平:只对一部分,因为我1981年开始跟随普里高津做非平衡态统计物理以后,主要我做的是研究经济问题,而且是研究经济波动,但是,因为我们是非均衡派,所以容不得,不被这个主流经济均衡学派容纳,所以我只能呆在物理系里面研究经济问题。我已经研究了16年了。
主持人:是这样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最开始上大学是哪一年?
陈 平:我是1962年进的北京中国科技大学,那时候还在科学院底下呢。
主持人:那这就奇怪了,我们认为中国科技大学一直在安徽,您怎么说它叫北京中国科技大学?
陈 平:是,搬到安徽是在文化革命期间,1968年,被强迫迁到合肥,从那儿以后就回不来了。
主持人:是谁强迫它搬到那里的。
陈 平:那时候当时的李德生,中央军委的委员。
主持人:李德生现在是好人哪。
陈 平:是好人,我觉得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儿,这个全世界有两个国家,这个首都和文化中心是重合的,一个是法国的巴黎;一个是中国的北京,所以你就知道学生运动对政府冲击也很大,政府干预学术也很大,所以学术作的好的话,要离开首都一点,所以搬到合肥去以后,我在合肥做的研究,要比在北大可能做的研究要好很多。
主持人:照您这个意思,您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您应该给人民代表大会写一个提案,建议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统统都转到外省。
陈 平:我建议是应该中国政府迁离北京建立一个新的都。这样的话呢,这样会大大提高政府的效率,就好像巴西建个新都一样。但是文化中心应该留在北京。
主持人:您准备把中国的首都迁到什么地方?
陈 平:我想应该在中部吧,这样的话比较合适,建都北京,是为了防御游牧民族的侵略,当然经济中心又在南方,所以我想这个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的情形,应该是能够解决的话,将来的新都应该设在中国的中部靠海一点。
主持人:中部靠海一点,中部有海吗?
陈 平:中部没有海,就是说离海不能太远。中国的分布的话,人口和经济发展是靠的东南沿海,但是这个军事的屯田以前都在西北。所以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政治、经济分离的一个矛盾。
主持人:请您还是给我们更加具体的一个概念,到底在中国的哪一个城市,西安?
陈 平:我想大概应该靠近武汉那边比较好一点。
主持人:靠近武汉。
陈 平:可能太热了一点,大家不愿意。大概武汉我想还是比较好一点。
主持人:您读硕士大致是哪一年
陈 平:我没有读过硕士,物理是只读博士的,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大学,主持人:到外面去读了。据说呢,您攻读物理博士的导师是一个化学家?
陈 平:他是物理学家,但是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主持人:您是跟他学的,自己学的物理,然后搞经济。
陈 平:因为他是要解决物理学和生物学之间的差距,那么我就想如果你能解决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差距的话。我就能解决物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差距,所以就这么做了。
主持人: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瞄准经济学研究了。
陈 平:瞄准应该是从文化革命后期开始的。
主持人:能不能大致告诉我李约瑟和亚当·斯密到底有什么关系?年代差得很远,研究的学科也不在一起,好象是一个国家的人。
陈 平:这个思想方法是一致的。因为我作的那个学科我们叫做非平衡态物理或者叫复杂系统科学,那么他研究的问题,就是说事物,不是事物,应该说是生物复杂系统,特别是生物或者经济社会系统,它演化的规律,李约瑟的问题是说什么呢?李约瑟的问题是说为什么科学出现在西欧,而没有出现在中国或者其它的文明。那么,中国人喜欢问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这么长?但李约瑟换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科学出现在西欧?但是呢,亚当斯密讲的问题是这样,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的起源,所以我就把李约瑟的问题改一下,为什么劳动分工起源在西欧而不是在中国,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呢,可以用我们复杂系统科学的研讨来回答。
主持人:好,陈老师已经把话题深入到他今天要说的学术报告了。今天陈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学术报告是《中国的劳动分工为何难以发展》,好,有请陈老师。
陈 平:谢谢诸位,我对这个问题的关心,是从文化革命开始,因为毛泽东当时号召,我们学生要去调查一个农村、一个工厂、一个学校,而且要了解中国这个社会落后的原因,当时认为落后的原因,封建社会那么长,就是因为地主剥削厉害,前进的动力是农民战争,当时我带着这个问题去调查了一个工厂,那是太原重型机器厂,那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项目,苏联研究的项目,我就发现建厂十几年,生产能力只达到设计能力的三分之一,我就非常奇怪。我想这是什么道理?调查结果,道理非常简单,就是说这个生产能力是按照成批、大规模生产来设计的。而当时因为帝国主义封锁的话,中国什么东西都必须要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所以即使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一个重型机器厂,一套模具做出来,生产一个重型机器,国内订货大概只有两三台。所以你就知道这样的话,企业就没有规模效益,所以企业非常抵制新技术,因为你一个新技术上来,他们就要重新换一套模具,然后就要亏本。当时我就感到非常奇怪,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读马克思的书,然后,我就发现,马克思和亚当·斯密是都高度称赞劳动分工,但是当时毛主席号召我们是武器道路,要“亦工、亦农、亦军”,恰恰是要违背劳动分工,要搞自给自足,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社会。所以当时我就想,中国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中国要抑制劳动分工,而这个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从劳动分工开始的。这样我就对李约瑟的问题感兴趣,所以李约瑟当时是说“科学为什么产生在西欧而不是中国”,虽然当时中国在很多技术上是领先的,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得到回答。
那时候呢,我在成昆铁路当工人,我还订了一份物理学杂志叫《今日物理》,《今日物理》1973年11、12月号,发表了一篇普里高津的革命性的文章,叫《演化的热力学》,他当时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物理学有一个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你说,熵永远是增加的,那意思是什么?秩序一定要瓦解,人总是要死的。这个和生物学矛盾,因为生物我们知道达尔文演化,从简单到复杂一个演化,是越变越复杂,那要是按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讲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个矛盾呢?普里高津就提出来热力学系统应该要分类,那么第一类孤立系统,熵永远是增加的,也就是秩序一定要瓦解;第二类是个封闭系统,那么你像这个水里如果有盐,融化在里面,你把温度一降,这个晶体就从水里面分离出来,这种结构是叫低温的均衡结构,它不可能产生生命这种演化,那么,生命的演化必须是要开放系统,开放系统就是说它要和外界交换,不但交换能量,而且要交换物质流,交换信息流,这样才能维持一个动态结构,这叫耗散结构,所以他的理论叫耗散结构理论。当时他区分开放系统和封闭系统这个思想,一下子就给我一个闪电一样的启示,我就明白了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停滞,不是因为阶级斗争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政府腐败,也不是因为中国民族性有什么恶劣,像五四运动那样批判,而是中国社会很长的时间是“闭关自守”的政策。
那么,第二个问题我马上就要问了,那就奇怪为什么历史上中国历届皇朝,都要重农抑商,一直到文化革命也是这样,而西方一直是要重商?我就不明白这件事情,那么,我看所有的历史教课书都得不到回答。所以我这个回答,是我看闲书得来的,我一开始是在看斯科特的骑士小说叫《艾凡吓》,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当时欧洲中世纪统治阶级的贵族住在乡下的庄园、不住在城里面,中国的统治阶级都是住在城里面。所以你看中国的城市都是一个军事要塞。城市统治这个农村,所以你马上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生态危机造成的结果。
所以后来我就偶然看到竺可桢,也是科学院副院长,写过一个《五千年气侯的变化》,就讲商代的时候中国非常暖和,但周代非常寒冷。所以我们都知道每次一旦寒潮过来,你马上就会听见报道,内蒙古大量的牲畜死亡,你知道这个动物是不能耐寒的。所以我的猜测的话呢,在商代以前,中国是一个和西欧一样的农牧林混合经济,然后周代的时候,这个寒潮来的时候呢,把那个牲口大量的消灭了,只有耐寒的作物才能生长,所以春秋的时候又开始变暖以后,中国就实现了一个转折,是从农牧的混合经济演化为以粮食为主的单一农业经济,然后再加上人口增长以后,引起列国争霸。
你就知道,越王勾践的时候开始奖励人口增殖,男子多少岁不娶、女子多少岁不嫁就要罚款。所以呢,我当时就读毛泽东著作,我就读出来一条道理。就是中国这个内战的规律和欧洲不一样,欧洲这个,打仗的话,如果你看一下历史,中国战争的规模是欧洲的十倍到一百倍,亚历山大东征只有两万人,你去看看欧洲的农民起义大概只有几千人,但是你去看一看春秋战国时期,一次秦国坑杀赵降兵四十万人,这就已经达到两次大战的规模,所以你去数一下的话,中国历史上人口伤亡,从三分之一到十分之九的这种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历史上有十三次大动荡,欧洲只有一次,就是黑死病,黑死病以后,因为这个劳力不足,然后就鼓励工业革命,那是节省劳力的发明,我们就会知道蒸汽机这些东西。
第二个问题就是“年鉴学派”,你知道就是布劳代尔,还有他的一个学生叫沃勒斯坦,他在早以前的话,还有文化人类学的一个人类学家叫哈里斯,他们都想要推广马克思的理论,来解释社会变化,那马克思来讲,是讲生产力这个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革命,那么他们就问一个问题,什么东西引起生产力的发展呢?他们就猜测是生产力下面应该是生态和技术。它决定这个的发展,然后再生产关系的上边一国的发展,不是一个单独的现象,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一个英国的现象,是一个各个文明的冲突结果,是拿我们物理学话来讲,是催化反应的结果,是扩散反映的过程。所以它的上面还有一个世界系统。那么,沃勒斯坦他们当时观察,就是说,世界系统的产生,东西方文明的分岔,大概在十五世纪左右,那时候有一个历史学家法国的,叫肖奴,还有沃勒斯坦他们观察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把他叫做“肖奴—沃勒斯坦佯谬” 他们说在十五世纪的时候,中国是地少人多,这个西欧是地多人少,这个地少人多到什么程度呢?我告诉你们一个基本的概念,西欧的平原面积是中国的八倍,但是西欧的人口一直比中国少,所以你要算一下他的人均的资源的话,他这个比我们要大很多。
所以照这个逻辑推理的话,中国应该缺少生存空间,西欧应该缺少人口,但是历史发展相反,西欧感到他们缺少生存空间,所以向外扩张、所以有历史大发现,有欧洲的殖民、澳洲的殖民。中国感到是缺乏劳力,所以中国是唯一的一个文明,在工业化以前,就人口翻了两番,从宋代的大概一亿左右,翻到清代的四亿左右,这是历史上非常奇怪的现象。那么看起来,照经济学解释的话,中国这个民族非常没有理性。
但是我发现这个理性很简单,就是说,事实上就可以用经济结构来解释,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同样的生存,我可以放牛、喝牛奶、吃牛肉,我也可以种粮食、我也可以打猎。但这样需要的资源是不一样的。能差多少呢?我告诉你们我有一个调查。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呆了二十年,德克萨斯它是一个以牧业为主的经济。在工业发展后,德州的一个基本单位,三口之家要生存,他是需要多少单位呢?他需要一百头母牛,所以我们现在翻译的牛仔是翻错了,是母牛仔,它是COW BOY,他的生产单位是母牛,因为下一个小牛,他可以卖肉吃,可以杀肉吃,牛奶可以拿来喂,平时来喂孩子。他一百头母牛,一头母牛需要多大的牧场呢?需要10到15英亩的牧场,一英亩是6亩,所以你就知道他需要大概6000到9000亩牧场,才能养活一个三口之家,你在中国的话,你可以养活几百户种粮食的农民。所以你就会明白了,所谓的中国文明是什么呢?中国的文明是一种节省资源,但是劳力密集的技术。而西欧呢?是资源密集,但是节省劳力的技术。所以,你后面就知道了劳动分工,现在我们讲的劳动分工,都是节约劳力,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批历史学家在那讨论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他就没有想到,这个资本主义萌芽,并不仅是商业,而是劳动分工的发展趋势,所以我想这个可以解释,李约瑟问题和这个“肖奴—沃勒斯坦佯谬”我们都可以解释,也可以是同时现在,我跟西方人解释,为什么中国构不成对西方的威胁,因为他们觉得,中国要走西方道路的话,那13亿人口对外扩张,那全球资源都不够。我说这是你们西方文明的逻辑,不是中国人的逻辑。
但在后面有一个问题就比较有意思,我到了这个普里高津研究中心以后,才发现在理论生物学里面有一个类似的问题,那是在控制论发展以后,控制论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是韦纳,但是第二个重要人物是一个英国工作人员叫阿西比,阿西比写过一本老的设计,他当时问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这个系统的演化从简单到复杂,应该是越复杂的系统越稳定呢?还是越复杂的系统越不稳定。那么你去问生物学家,生物学家一定说,越复杂的系统越稳定。为什么?因为达尔文讲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适者什么意思,适者就是稳定,它适合这个环境。
我顺便讲一下我们这个粱启超的篡改这个达尔文的,把那个适者生存变成优胜劣败,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曲解吧,适应的不一定是优的,比如说蟑螂,可以适应非常恶劣的环境,人没有蟑螂有生存能力。你不能说蟑螂比人优越。所以讲这个演化一定是进化的,这是不对的。演化大部分90%以上的突变都是退化的。很少才能进化,但是它进化以后。比如象生命起源这种东西,劳动或者资本主义起源。它一旦过了一个临界值以后,它就势不可挡。但是呢,作为控制论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话,他对这个问题是,不会先验的去承认的,他要做计算机模拟,计算机模拟的结果是否定的,随便你怎么样构造一个系统,开始有十几个变量,后来增加到上百个变量,你就会发现系统越大越不稳定。这个结果呢?生物学家一片哗然。说你们这个控制论学家一定是错了,为什么错了呢,你的模型不现实,所以就有一个很好的理论物理学家在普林斯顿,改行去做理论生物学,他就说,因为你们的系统是线性的,真实的生物问题都是非线性的,所以他就把非线性的系统放进去研究,结果也是一样的,越复杂的系统越不稳定。这就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谜了。
这个理论生物学家也是混沌理论的开创者叫罗伯特·梅,现在从普林斯顿搬到牛津去了。所以当时我八十年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立刻从中国就得到一个启发,为什么你想一件事情很简单,物理学家如果是重复的失败,他一定不会钻牛角尖,他一定会承认,失败的结论是有道理的。比如说物理学家拼命想要做永动机做不成,那怎么办?你就用热力学定理,你就知道,这个能量是守恒的。你老想做单热源的热机做不成,那你就知道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是成立的。你想要做速度无穷大的机器做不成,那你就承认相对论是有道理的,光速是有限的。那我就说,那一想的话,物理学家一定是对的,就是说复杂的系统越不稳定,简单的系统稳定。道理非常简单,也是从中国的现实来的,比如说越南战争,为什么中国游击战能打败国民党,它就是一个简单系统打败一个复杂系统,当然,在纽约如果你断电的话,一个摩天大楼马上就混乱。一个蚯蚓把它砍成两断,它两段都可以变成蚯蚓,人给砍成两段,他绝对不会再变成一个人。我就立刻想到了一个经济学的道理,就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定理,就变成一个复杂性和稳定性之间的trade off,中文讲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是一个此消彼长的消长关系,就是说你想要稳定性大一点,你牺牲的代价是你的复杂性或者你的发展的机会,如果你要发展得快一点,你牺牲的是稳定性。所以你就会知道,中国社会的优越性是,中国这个简单系统,自给自足,南泥湾精神,要比西欧的系统稳定。当然反过来呢,它代价呢?如果你搞自给自足,你走武器道路,你牺牲的是工业革命的机会。我想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 那么后来我们又想到,我前年到北大经济中心来工作的时候,我偶然间又发现经济学家有了类似的问题,非常著名的芝加哥已经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叫斯蒂格勒,他在1951年就发现一个亚当·斯密的困境。此话怎讲?我们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有两个非常著名的理论,一个叫“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是什么意思呢?就意味着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也就是说你进这个市场的话,没有不任何人能够操作这个市场,大家都是机会平等。但亚当·斯密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叫“斯密定理”,他是说劳动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的限制。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比如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农村劳力过剩,大量的人口要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你的方向怎么办?中国很多善良的经济学家呼吁应该发展小城镇。如果你学过亚当·斯密定理,你就发现,小城镇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城镇很小,劳动分工就受规模限制,你的服务业就发展不起来,所以你只能发展大中城市,你才能发展劳动分工,才能吸收大量的农村人口。但是如果亚当·斯密这个定理是对的话,它就跟前面的看不见的手矛盾了,为什么呢?你达到这个市场规模限制的时候,就出现什么?就出现垄断,所以你马上就证明马克思的预言是对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结尾一定会导致垄断,垄断也就会……,照列宁说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就要灭亡。那这就是林毅夫老师讨论的问题了,为什么现在资本主义不但不灭亡,还有生命力呢?那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是亚当·斯密的这两个东西,在现实里面能不能共存?事实上永远都在共存。为什么?你看美国,它有大量的小企业存在,也有大量的跨国的垄断的企业存在,如果要照我们选优的理论的话,你就要么相信完全市场都是小企业,要么就相信,全是垄断企业,基本没有小企业存在的余地,你怎么理解这两者的共存呢?那么这个共存的问题,在传统的均衡的理论里面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在我们复杂科学里面就可以解决,解决办法就是拿我做研究生的时候,1987年发现的复杂性和稳定性之间的消长关系,所以我就在去年提出一个广义的斯密定理,就把原来的斯密定理给推广了,原来斯密定理讲就是说,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我发现这是不完全的,应该正确的表述,我是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表达,今天我不讲数学,我讲思想就好了,它受三样因素的限制,第一个限制是市场规模,因为每一个技术到后来达到它的潜力以后,效益都会递减,比如说种地,你拼命的投入肥料或者人力,到后来它产量增长越来越缓慢。但是,你要新的技术革命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新的资源,所以你第二个限制是资源的种类,比如说我们中国如果老呆在土地上,你要发展它,你就没有前途了,但是如果你开辟新的资源,你发现新的矿产,甚至发现新的脑力的资源,我们现在开发新的信息,那你的资源种类越多,你创造财富的机会越多,所以它第二限制于资源的种类。第三呢?受限制于环境的涨落,这话怎么讲?这话就是前面我讲的,如果你环境的涨落非常大,大起大落,那么这个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它就会从复杂系统简化为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比较高。如果你系统的涨落相对比较小,那么这个系统才有可能从简单系统演化成复杂系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同意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创造力,当然农民战争不是自觉战争,是统治阶级逼出来的。但是你就知道,这个涨落非常大以后,会使得这个社会经常打断重来,打断重来,所以中国好多发明都会失传,好多发明重复发生,因为它没有一个连续的积累的系统。所以,你就会得到一个一般的结论,如果一个社会,它这个社会是鼓励创新和发明的,不断创造新的资源,而且社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么它的系统才能够从简单向复杂演化,才能产生劳动分工,产生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形态。否则的话,你就会往另外一个方面演化,所以演化是象树一样的形状,而且演化可能是双向的。这一条也可以顺便就回答了,我们五四以来辩论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全盘西化,如果你是一个均衡理论的话,你从时间、空间任何一点,可以走到任何已涉及的目标,但是如果象个树一样,你就知道,你到了这个杈上,你就跳不到那个杈上,所以你的演化是受你的历史、经济还有生态条件的制约,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最后我想,我们可以稍微用一点(时间)来讨论中国的改革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争论到底是应该在发展中求稳定,还是在稳定中求发展。那我就会偏向说,稳定中求发展要好一点,如果你发展太快,造成社会大动荡的话,你就会倒退到原来简单的系统中去了。这是一个。
但是另外一个呢,有没有可能说,对一个企业,比如说国有企业保值增值,也不可能。一个开放系统里面,唯一能够做的是保持你的竞争力,要么你就被淘汰。所以保持竞争力保守的文化,是阻碍劳动分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然后一个风险,喜欢冒险的,进取的文化,才有可能发展劳动分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的那个书。叫《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学》,我在里面还专门做了一个模型,就是说,两种文化竞争的时候,一种是保守的文化,一种是进取的文化,那么进取文化有利于劳动分工,保守的文化有利于社会稳定。然后还有现在我们金融改革里面,能不能防范金融风险,我想就不能防范金融风险,为什么呢?你在一个正常的金融市场里面,风险和回报是正相关的,你可以防范舞弊,没有办法防范风险,所以你应该是“大禹治水”开渠道,而不是(衮???)治水,到处修堤坝,堵决口。所以我就在讲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一个新的学科,叫非平衡态物理学,或者叫复杂系统科学,可以打破原来劳动分工的学科的局限,把生物演化、社会演化、经济变革里面的问题,从一个自组织科学的高度来理解,谢谢。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先看一看,来自凤凰网站的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叫“快刀浪子”。他说,听说您1979年曾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同时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中国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我很佩服您,网友说,我很佩服您,您很有远见,那么早就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指出了一条通向开放经济的康庄大道,而且您那么早就有了商业意识,竟敢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种大刊上一稿两投?
陈 平:这个事情我要讲一下,这不是我的远见,因为当时我能读到的书是有限的,所以我出国以后,就知道有一个美国文化人类学叫哈里斯,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小册子,叫做《猪、母牛和巫婆》。他就是用生态的原因来解释文化的差异,包括为什么伊斯兰教不吃猪肉这个问题。但是我是用生态问题来解释中国更大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所以是不谋而和,但是我并不是第一次从生态来解释马克思的思想。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文章能够发表,是经济改革的领导人的决策,而不是我的勇气,因为我这个文章,我是在七十年代中就写好了,我根本发表不出去。《光明日报》拒绝发表,说你的阶级斗争呢?我说阶级斗争,马克思早就讲过了,我没有贡献,我的贡献只在这个地方。但是后来中国因为要进行改革,改革的话,突破点在农业改革,当时的主业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毛泽东的以粮为纲,前面我不是讲过以粮为纲吗,毛泽东思想就是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然后那时候我们文化革命的号召叫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后来我就明白一件事情,这个事情事实上朱元璋讲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所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要做一个注解,就是有粮则有军,有军则有权,这是中国内战的逻辑,但是对西欧统一的逻辑并不一样。所以当时很有意思,做经济改革的好多领导人,都从科学院出来的,说你能不能简单写一篇文章,说明你的观点。结果我一个晚上就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就拿到,当时东北的一个农业政策的讨论会上去,目的是要打破以粮为纲,转为全面发展。打破以粮为纲以后,才允许农民自己决定种什么,然后你才可能包产到户,才有增长余地,如果你包产到户,还下令种粮食的话,那就不行了。人民公社制度,它不是为了鼓励生产发展,而是为了保证国家安定,强制农民种粮,要粮食安全,这么一个考虑。所以这个文章在人民、光明同时发表,是我们国家改革派领导人一个政治决策,而我只是起了一个小卒子的作用。
主持人:下一个网友的提问,这个网友叫做“不喜欢台湾的三毛”,他说,陈教授您好,我对您有一种复杂的感觉,你曾说,中国的股市的症结是政府干预不当,而股市大起大落,与政府干预有很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股市是政策市而不是经济市,这是陈教授说的。陈教授还接着说,这给金融机构公款炒股提供了机会。然后又是网友的评价了,他说您的这个观点我很赞成,并喜欢听到您现在更细致地阐述它,但是我必须告诉您,台湾的三毛也叫陈平,我劝您趁早改个名。
陈 平:这个问题我已经苦恼很久了,就是说,同名的人很多,刘邦的左丞相是陈平,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是陈平,现在北京还有一个集团董事长也叫陈平,还有一个画家叫陈平,所以叫陈平的名字非常多。但是我这个名字是我的外祖父给取的,因为我生在抗日战争,所以中国世代的愿望都是要和平,所以我就知道,我的取名是和平。但是我跟我父母讲,我应该叫“陈不平”就对了,我一天都没有太平过。但是我真的想不出应该改什么名字,因为我没有找到一个字或者号能代表我的风格,因为我老在那里变化。
主持人:行,那我告诉这位网友,这个陈平跟台湾那个陈平根本就不是一码事。他还是想听到您对股市的一些见解。
陈 平:中国股市的发展,我觉得大的趋势还是好的。因为所有的股市的发展都有一个大起大落,然后逐渐规范化的过程。所以你就看美国大箫条以后,股市监管严厉了很多,但是也不能防止股票市场的崩溃。所以在经济学界里面,金融领域只有两派,如果相信均衡理论的话,也就是叫“有效市场假说”,他就证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是对的,政府不用干预也行。但是现在我们做非均衡经济学的人,就越来越多地发现了,股市内部是不稳定的,为什么呢?你看见股票价格涨,如果相信均衡的话,你就应该卖,他不但不卖,他还要买进,为什么呢?他相信股票市场还要涨,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机制,那么这种情况底下,就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修改市场的规则,比如说限制换手率,或者是换手太高要收税,或者是政府干预的时候要降低过度反应,要降低时间的延迟。中国政府经常干预时间太晚,说粮食价格低的时候,说粮食不足,它进口粮食,结果等它进口的时候,已经生产过剩。经常会有这种问题。但是最重要的办法,还是要加强市场的竞争,就是市场竞争,防止垄断,是打破少数做庄,操纵市场的可能性。所以政府扮演一个角色,我想要比较多的从亲自干预,变成是制定良好的游戏规则,来当裁判,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然后在市场本身,也不能够自动达到稳定,要让市场健康地发展,第一要降低进入的门槛,让更多的,现在主要大量的经营良好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它不能入市。但另外一方面,你要打破少数国有银行,打破少数国有基金的垄断,让比较多的人参与竞争,这样股市就能比较健康的发展。
观 众:陈教授,我想请问一下,您刚才说到中国传统上都是长期的闭关自守,但是我看到的一些历史材料上面讲,说中国从明确的海禁是从明代开始的,但是实际上研究的结果表明,“大明海岸不寂寞”,这好象是方舟子先生的一篇文章,而且据我看一些闲书所得来的感觉是,明清实际上对东南亚的这种民间贸易还是很繁荣的,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您这个。
陈 平:这个你说的也很对,因为做科学的人喜欢抽象和简化,如果你要把所有的历史细节放进去,那你的理论就没有了。所以如果严格来说的话,中国社会从来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如果要封闭的系统的话,它应该是静止不动的。但是你会发现,中国社会还在变化,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农业区从中原地区扩展到江南地区,这是很大的变化。第二,中国的象吸收那种,红薯、玉米这种高产作物也是很大的变化,所以中国人口增加了很多。然后中国的丝绸之路的贸易和海上跟阿拉伯的贸易量也很大。但是你马上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市场产生的过程里面,主要经历的一个矛盾,就是说你是要搞关税保护,还是要搞开放竞争。事实上欧洲经过几百年的路才走过来的。中国改革一开放的时候你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是羊毛大战,是否你还记得?是价格大战,封锁产品,还是开放竞争。所以它每一个社会,面临外来竞争的时候,永远有一个政策选择,一个是你要不要升高保护壁垒,还是强化开放的竞争。所以严格来说的话,你会发现,中国的政策在两个之间摇摆,一个摇摆就是说,因为中国冀朝鼎有一个非常好的分析,就是中国统治是控制富裕的产量区,主要集中在江南一带。然后政治中心是在北方,因为要对付游牧民族的侵略,所以它把粮食运到北方。所以你就会发现,中国在政治经济的选择里面,也就是说在萨缪尔森一开始讲经济学的时候,是在大炮和黄油之间选择,也就是说在军用和民用之间选择,也就是林毅夫老师讲的,赶超还是比较优势的选择里面。中国经常是把政治、军事的考虑放在经济发展的考虑的前面,它一旦感到安全威胁的时候,它就强调要粮食安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对中国是非常深刻的教训,包括大跃进,包括以前的汉代的屯田,都是造成短期的农业的利益,然后造成长期的生态破坏,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中国是除了撒哈拉沙漠以外,北非以外,中国是生态环境最困难的国家之一。这个行为要不改变,中国将来的前景就很可忧,如果这个心理能改变,中国的竞争将在世界上是非常好的。
主持人:接下来看两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名字叫“骑着毛驴来上网”,他说鲁桂珍,鲁桂珍是李约瑟先生在中国娶的中国太太,他们俩结婚的时候好象两个人都八十多岁了。现在想起来非常浪漫。网友说,鲁桂珍在李约瑟小传中坦言说,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我知道,这又是网友的说话了,说我知道,这老家伙根本没有正式听课学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了一下,所以,他根本不能算圈里人,最多只能算是票友中的名票而已。我估计他的意思是您就别研究他了,不值。
陈 平:我觉得他的问题很有意思,我在给我们经济研究中心的同学上课的时候,我开章名义就讲一件事情,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我说这句话只对一半,为什么呢?知识也是负担。为什么呢?所有新科学的创始人,你去看马克思也好,达尔文也好,牛顿也好,爱因斯坦也好,都是知道甚少的青年人,但他知道老的一代人的问题所在,他会有新的思想,如果你学很多的东西,你就没有创造可能性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来说,我觉得李约瑟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象我这个是理科中学,理科大学出来的,从来没有受过人文历史的正规训练,反而能看到所谓的反常现象。
主持人:他的意思是,您也是票友?
陈 平:我现在已经从票友转化为专业了,为什么呢?原来我在大学里面人家给我起个外号,叫“杂家”,非常奇怪的,现在新兴的科学,改成叫复杂科学系统,所以我现在成了复杂科学系统的创始人之一。
主持人:下一位网友叫做“像我这样的八戒”,这位网友说,李约瑟沉迷于道教和长寿术,热心收集房中术书籍。有一次,他在北京琉璃厂,一位出名的女老板那里买到了《双梅警案丛书》,李约瑟一阵狂喜,说这本书是伟大的中国性学著作,而且他在中国科技发展史第二卷专门写了房中术,大谈采阴补阳和还精补脑,还说这些理论具有很大的生理学意义。他有一番话,真让我这个四川八戒受不了,他居然说,当他问一位四川人有多少人按照房中术的训诫行事时,得到的回答是,四川的绅士淑女,半数以上都是这样做的,请问陈教授,这老色鬼的话您也信以为真吗?
陈 平:我没有注意这个李约瑟研究房中术,但是我倒是非常注意研究中国和西欧的美学观点的不同,因为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是学素描的,然后你就知道,西方的,希腊人的美的观念,是裸体美,中国的画,画画都穿衣服的。所以我后来出国以后,就发现,西方的观念是普遍状态,你去看看,印度那个佛像,那个女孩子的乳房都圆滚滚的,然后中国的佛像就看不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你去看非洲人和印地安部落的文化,对性的崇拜都是非常鲜明的。这个有什么道理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说对做科学的,喜欢自然的状态,而且喜欢科学独立的发展。这个东西怎么出来的呢?我到巴黎去,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巴黎的建筑都是古典的,它受希腊罗马文化影响很深。建筑上面都是雕塑,最高一层全是女神,中间一层都是小孩,小天使,代表天真可爱,最底下,第三层,才是丑恶的男人,将军、主教、元帅、政治家这些。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观念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就是说,抱着一个平常的心态来研究的话,其实你就会发现,中国在性的方面,要比西方不亚于,比如说西方在基督教以后,强调一夫一妻制,但是又有很多情人。中国呢,公开的就是男女不平等,男的可以很多妻妾成群,皇帝有宫女上千,而且中国也不以为怪,我觉得这个事实上可以研究的。
观 众:谢谢主持人,我提一个跟您今天讲的不太有关的问题。就是说,我看了一个也算是很有名的人,他对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评价,他说……可能是有所指,可能是跟北大经济学家也有关系,因为我觉得你特富有批判精神。他是怎么评价的呢?他说,现在经济学界存在着幕僚情结和帮忙主义,他们坚守在岸上大呼小叫,捕风捉影等等,我记住了头。我觉得,您作为他们群体中的一员,您怎么评价。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经济学家都是支持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集团中的一员,那么您从属于哪个既得利益?那么您为哪个集团服务? 陈 平: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已经变成一个经济学家,我非常希望成为经济学家,但是我每次在国外或者国内,在国外是挑战主流经济学,在国内是请教国内经济学家的时候,我总是说,我是物理学家出身的,所以我愿意当经济学家的学生,我现在还是学生,所以我不认为我已经变成经济学家了。第二,我认为中国经济学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工程已经是国际化的,所以非常有竞争能力,但是中国的经济学界还是传统的人文的规范,比如说非常奇怪的事情,包括北大,包括教委,对学科的分类都是不合科学常理的,因为我做物理的,物理有四大基础科学,力学、电磁学,统计物理,量子力学,经济学有三大基础课,微观、宏观、计量,这些东西在中国被称为“西方经济学”,我是做宏观和做计量的,所以我就不能带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生,我只能说要么我选西方经济学,要么我选金融学,所以我现在带博士生的项目是金融学,金融只是我的一个应用的领域,并不是我的主业,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国内对社会科学的看法还是落后在以前的时代。我想,科学如果对的话,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改革的经验,应该融入世界经济学宝贵财富的一部分,而不能讲我是中国特色经济学,那我就跟人家不一样,这你是作茧自缚。第二我不赞成国内经济学界没有劳动分工这个传统,这是我非常反对的。所以我最近建议我们的新闻记者,以后报纸上报道的时候,不要用著名经济学家这种提法,也不要引用某某人是人大还是科学院还是什么职位,哪怕你得过诺贝尔奖,也不能证明你的观点是对的。但是你可以要说明他是哪个领域的专家,你到底研究的是货币,还是研究的证券,还是研究的债券,还是研究什么,你让人家明白你是哪个领域。然后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会知道又有不同的学派,你是什么学派,什么方法,我就知道你怎么分析这个问题,而不要用一个职位来吓唬人。这样来看的话,中国可以被称得上是有贡献的经济学家,在世界上被同行所认可的,就非常之少了,所以我不晓得你说的经济学家他们是什么样的经济学家,谢谢。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希望您用一句话回答我,您说这个中国的劳动分工为什么难以发展?原因是什么?一句话。
陈 平:环境涨落太大以后,发展单一农业经济。
主持人:好,谢谢您。追求进步,学术倾听,世纪大讲堂向您道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谢谢陈教授,谢谢大家。
陈 平:好。
主持人:我想问问您,您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陈 平:50多岁了吧。
主持人:50多岁了,那有一个秘诀应该传授给我们。我34岁的时候还认为我会永远像您一样瘦下去,但是,35岁突然就胖起来了。
陈 平:这个秘诀很简单,我的老师普里高津跟我讲,不是老师教学生,而是学生教老师,所以如果我能永远从学生那里学习的话,我第一永远年轻。第二呢,永远不会变胖。
主持人:这我就听不懂了。一般来说,从外界摄取东西多的话,他就会更丰富,从体型上来说也会变胖。
陈 平:你要知道,年轻人给老一点的人的挑战是让你足够伤脑筋、让你想问题的;然后你就睡不着觉,你就不会长胖。
主持人:是这样。我大致看了一下您的履历,我发现您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统统没有研究过经济,都是研究物理,怎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经济话题呢?
陈 平:只对一部分,因为我1981年开始跟随普里高津做非平衡态统计物理以后,主要我做的是研究经济问题,而且是研究经济波动,但是,因为我们是非均衡派,所以容不得,不被这个主流经济均衡学派容纳,所以我只能呆在物理系里面研究经济问题。我已经研究了16年了。
主持人:是这样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最开始上大学是哪一年?
陈 平:我是1962年进的北京中国科技大学,那时候还在科学院底下呢。
主持人:那这就奇怪了,我们认为中国科技大学一直在安徽,您怎么说它叫北京中国科技大学?
陈 平:是,搬到安徽是在文化革命期间,1968年,被强迫迁到合肥,从那儿以后就回不来了。
主持人:是谁强迫它搬到那里的。
陈 平:那时候当时的李德生,中央军委的委员。
主持人:李德生现在是好人哪。
陈 平:是好人,我觉得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儿,这个全世界有两个国家,这个首都和文化中心是重合的,一个是法国的巴黎;一个是中国的北京,所以你就知道学生运动对政府冲击也很大,政府干预学术也很大,所以学术作的好的话,要离开首都一点,所以搬到合肥去以后,我在合肥做的研究,要比在北大可能做的研究要好很多。
主持人:照您这个意思,您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您应该给人民代表大会写一个提案,建议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统统都转到外省。
陈 平:我建议是应该中国政府迁离北京建立一个新的都。这样的话呢,这样会大大提高政府的效率,就好像巴西建个新都一样。但是文化中心应该留在北京。
主持人:您准备把中国的首都迁到什么地方?
陈 平:我想应该在中部吧,这样的话比较合适,建都北京,是为了防御游牧民族的侵略,当然经济中心又在南方,所以我想这个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的情形,应该是能够解决的话,将来的新都应该设在中国的中部靠海一点。
主持人:中部靠海一点,中部有海吗?
陈 平:中部没有海,就是说离海不能太远。中国的分布的话,人口和经济发展是靠的东南沿海,但是这个军事的屯田以前都在西北。所以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政治、经济分离的一个矛盾。
主持人:请您还是给我们更加具体的一个概念,到底在中国的哪一个城市,西安?
陈 平:我想大概应该靠近武汉那边比较好一点。
主持人:靠近武汉。
陈 平:可能太热了一点,大家不愿意。大概武汉我想还是比较好一点。
主持人:您读硕士大致是哪一年
陈 平:我没有读过硕士,物理是只读博士的,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大学,主持人:到外面去读了。据说呢,您攻读物理博士的导师是一个化学家?
陈 平:他是物理学家,但是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主持人:您是跟他学的,自己学的物理,然后搞经济。
陈 平:因为他是要解决物理学和生物学之间的差距,那么我就想如果你能解决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差距的话。我就能解决物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差距,所以就这么做了。
主持人: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瞄准经济学研究了。
陈 平:瞄准应该是从文化革命后期开始的。
主持人:能不能大致告诉我李约瑟和亚当·斯密到底有什么关系?年代差得很远,研究的学科也不在一起,好象是一个国家的人。
陈 平:这个思想方法是一致的。因为我作的那个学科我们叫做非平衡态物理或者叫复杂系统科学,那么他研究的问题,就是说事物,不是事物,应该说是生物复杂系统,特别是生物或者经济社会系统,它演化的规律,李约瑟的问题是说什么呢?李约瑟的问题是说为什么科学出现在西欧,而没有出现在中国或者其它的文明。那么,中国人喜欢问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这么长?但李约瑟换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科学出现在西欧?但是呢,亚当斯密讲的问题是这样,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的起源,所以我就把李约瑟的问题改一下,为什么劳动分工起源在西欧而不是在中国,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呢,可以用我们复杂系统科学的研讨来回答。
主持人:好,陈老师已经把话题深入到他今天要说的学术报告了。今天陈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学术报告是《中国的劳动分工为何难以发展》,好,有请陈老师。
陈 平:谢谢诸位,我对这个问题的关心,是从文化革命开始,因为毛泽东当时号召,我们学生要去调查一个农村、一个工厂、一个学校,而且要了解中国这个社会落后的原因,当时认为落后的原因,封建社会那么长,就是因为地主剥削厉害,前进的动力是农民战争,当时我带着这个问题去调查了一个工厂,那是太原重型机器厂,那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项目,苏联研究的项目,我就发现建厂十几年,生产能力只达到设计能力的三分之一,我就非常奇怪。我想这是什么道理?调查结果,道理非常简单,就是说这个生产能力是按照成批、大规模生产来设计的。而当时因为帝国主义封锁的话,中国什么东西都必须要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所以即使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一个重型机器厂,一套模具做出来,生产一个重型机器,国内订货大概只有两三台。所以你就知道这样的话,企业就没有规模效益,所以企业非常抵制新技术,因为你一个新技术上来,他们就要重新换一套模具,然后就要亏本。当时我就感到非常奇怪,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读马克思的书,然后,我就发现,马克思和亚当·斯密是都高度称赞劳动分工,但是当时毛主席号召我们是武器道路,要“亦工、亦农、亦军”,恰恰是要违背劳动分工,要搞自给自足,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社会。所以当时我就想,中国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中国要抑制劳动分工,而这个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从劳动分工开始的。这样我就对李约瑟的问题感兴趣,所以李约瑟当时是说“科学为什么产生在西欧而不是中国”,虽然当时中国在很多技术上是领先的,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得到回答。
那时候呢,我在成昆铁路当工人,我还订了一份物理学杂志叫《今日物理》,《今日物理》1973年11、12月号,发表了一篇普里高津的革命性的文章,叫《演化的热力学》,他当时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物理学有一个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你说,熵永远是增加的,那意思是什么?秩序一定要瓦解,人总是要死的。这个和生物学矛盾,因为生物我们知道达尔文演化,从简单到复杂一个演化,是越变越复杂,那要是按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讲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个矛盾呢?普里高津就提出来热力学系统应该要分类,那么第一类孤立系统,熵永远是增加的,也就是秩序一定要瓦解;第二类是个封闭系统,那么你像这个水里如果有盐,融化在里面,你把温度一降,这个晶体就从水里面分离出来,这种结构是叫低温的均衡结构,它不可能产生生命这种演化,那么,生命的演化必须是要开放系统,开放系统就是说它要和外界交换,不但交换能量,而且要交换物质流,交换信息流,这样才能维持一个动态结构,这叫耗散结构,所以他的理论叫耗散结构理论。当时他区分开放系统和封闭系统这个思想,一下子就给我一个闪电一样的启示,我就明白了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停滞,不是因为阶级斗争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政府腐败,也不是因为中国民族性有什么恶劣,像五四运动那样批判,而是中国社会很长的时间是“闭关自守”的政策。
那么,第二个问题我马上就要问了,那就奇怪为什么历史上中国历届皇朝,都要重农抑商,一直到文化革命也是这样,而西方一直是要重商?我就不明白这件事情,那么,我看所有的历史教课书都得不到回答。所以我这个回答,是我看闲书得来的,我一开始是在看斯科特的骑士小说叫《艾凡吓》,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当时欧洲中世纪统治阶级的贵族住在乡下的庄园、不住在城里面,中国的统治阶级都是住在城里面。所以你看中国的城市都是一个军事要塞。城市统治这个农村,所以你马上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生态危机造成的结果。
所以后来我就偶然看到竺可桢,也是科学院副院长,写过一个《五千年气侯的变化》,就讲商代的时候中国非常暖和,但周代非常寒冷。所以我们都知道每次一旦寒潮过来,你马上就会听见报道,内蒙古大量的牲畜死亡,你知道这个动物是不能耐寒的。所以我的猜测的话呢,在商代以前,中国是一个和西欧一样的农牧林混合经济,然后周代的时候,这个寒潮来的时候呢,把那个牲口大量的消灭了,只有耐寒的作物才能生长,所以春秋的时候又开始变暖以后,中国就实现了一个转折,是从农牧的混合经济演化为以粮食为主的单一农业经济,然后再加上人口增长以后,引起列国争霸。
你就知道,越王勾践的时候开始奖励人口增殖,男子多少岁不娶、女子多少岁不嫁就要罚款。所以呢,我当时就读毛泽东著作,我就读出来一条道理。就是中国这个内战的规律和欧洲不一样,欧洲这个,打仗的话,如果你看一下历史,中国战争的规模是欧洲的十倍到一百倍,亚历山大东征只有两万人,你去看看欧洲的农民起义大概只有几千人,但是你去看一看春秋战国时期,一次秦国坑杀赵降兵四十万人,这就已经达到两次大战的规模,所以你去数一下的话,中国历史上人口伤亡,从三分之一到十分之九的这种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历史上有十三次大动荡,欧洲只有一次,就是黑死病,黑死病以后,因为这个劳力不足,然后就鼓励工业革命,那是节省劳力的发明,我们就会知道蒸汽机这些东西。
第二个问题就是“年鉴学派”,你知道就是布劳代尔,还有他的一个学生叫沃勒斯坦,他在早以前的话,还有文化人类学的一个人类学家叫哈里斯,他们都想要推广马克思的理论,来解释社会变化,那马克思来讲,是讲生产力这个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革命,那么他们就问一个问题,什么东西引起生产力的发展呢?他们就猜测是生产力下面应该是生态和技术。它决定这个的发展,然后再生产关系的上边一国的发展,不是一个单独的现象,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一个英国的现象,是一个各个文明的冲突结果,是拿我们物理学话来讲,是催化反应的结果,是扩散反映的过程。所以它的上面还有一个世界系统。那么,沃勒斯坦他们当时观察,就是说,世界系统的产生,东西方文明的分岔,大概在十五世纪左右,那时候有一个历史学家法国的,叫肖奴,还有沃勒斯坦他们观察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把他叫做“肖奴—沃勒斯坦佯谬” 他们说在十五世纪的时候,中国是地少人多,这个西欧是地多人少,这个地少人多到什么程度呢?我告诉你们一个基本的概念,西欧的平原面积是中国的八倍,但是西欧的人口一直比中国少,所以你要算一下他的人均的资源的话,他这个比我们要大很多。
所以照这个逻辑推理的话,中国应该缺少生存空间,西欧应该缺少人口,但是历史发展相反,西欧感到他们缺少生存空间,所以向外扩张、所以有历史大发现,有欧洲的殖民、澳洲的殖民。中国感到是缺乏劳力,所以中国是唯一的一个文明,在工业化以前,就人口翻了两番,从宋代的大概一亿左右,翻到清代的四亿左右,这是历史上非常奇怪的现象。那么看起来,照经济学解释的话,中国这个民族非常没有理性。
但是我发现这个理性很简单,就是说,事实上就可以用经济结构来解释,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同样的生存,我可以放牛、喝牛奶、吃牛肉,我也可以种粮食、我也可以打猎。但这样需要的资源是不一样的。能差多少呢?我告诉你们我有一个调查。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呆了二十年,德克萨斯它是一个以牧业为主的经济。在工业发展后,德州的一个基本单位,三口之家要生存,他是需要多少单位呢?他需要一百头母牛,所以我们现在翻译的牛仔是翻错了,是母牛仔,它是COW BOY,他的生产单位是母牛,因为下一个小牛,他可以卖肉吃,可以杀肉吃,牛奶可以拿来喂,平时来喂孩子。他一百头母牛,一头母牛需要多大的牧场呢?需要10到15英亩的牧场,一英亩是6亩,所以你就知道他需要大概6000到9000亩牧场,才能养活一个三口之家,你在中国的话,你可以养活几百户种粮食的农民。所以你就会明白了,所谓的中国文明是什么呢?中国的文明是一种节省资源,但是劳力密集的技术。而西欧呢?是资源密集,但是节省劳力的技术。所以,你后面就知道了劳动分工,现在我们讲的劳动分工,都是节约劳力,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批历史学家在那讨论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他就没有想到,这个资本主义萌芽,并不仅是商业,而是劳动分工的发展趋势,所以我想这个可以解释,李约瑟问题和这个“肖奴—沃勒斯坦佯谬”我们都可以解释,也可以是同时现在,我跟西方人解释,为什么中国构不成对西方的威胁,因为他们觉得,中国要走西方道路的话,那13亿人口对外扩张,那全球资源都不够。我说这是你们西方文明的逻辑,不是中国人的逻辑。
但在后面有一个问题就比较有意思,我到了这个普里高津研究中心以后,才发现在理论生物学里面有一个类似的问题,那是在控制论发展以后,控制论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是韦纳,但是第二个重要人物是一个英国工作人员叫阿西比,阿西比写过一本老的设计,他当时问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这个系统的演化从简单到复杂,应该是越复杂的系统越稳定呢?还是越复杂的系统越不稳定。那么你去问生物学家,生物学家一定说,越复杂的系统越稳定。为什么?因为达尔文讲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适者什么意思,适者就是稳定,它适合这个环境。
我顺便讲一下我们这个粱启超的篡改这个达尔文的,把那个适者生存变成优胜劣败,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曲解吧,适应的不一定是优的,比如说蟑螂,可以适应非常恶劣的环境,人没有蟑螂有生存能力。你不能说蟑螂比人优越。所以讲这个演化一定是进化的,这是不对的。演化大部分90%以上的突变都是退化的。很少才能进化,但是它进化以后。比如象生命起源这种东西,劳动或者资本主义起源。它一旦过了一个临界值以后,它就势不可挡。但是呢,作为控制论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话,他对这个问题是,不会先验的去承认的,他要做计算机模拟,计算机模拟的结果是否定的,随便你怎么样构造一个系统,开始有十几个变量,后来增加到上百个变量,你就会发现系统越大越不稳定。这个结果呢?生物学家一片哗然。说你们这个控制论学家一定是错了,为什么错了呢,你的模型不现实,所以就有一个很好的理论物理学家在普林斯顿,改行去做理论生物学,他就说,因为你们的系统是线性的,真实的生物问题都是非线性的,所以他就把非线性的系统放进去研究,结果也是一样的,越复杂的系统越不稳定。这就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谜了。
这个理论生物学家也是混沌理论的开创者叫罗伯特·梅,现在从普林斯顿搬到牛津去了。所以当时我八十年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立刻从中国就得到一个启发,为什么你想一件事情很简单,物理学家如果是重复的失败,他一定不会钻牛角尖,他一定会承认,失败的结论是有道理的。比如说物理学家拼命想要做永动机做不成,那怎么办?你就用热力学定理,你就知道,这个能量是守恒的。你老想做单热源的热机做不成,那你就知道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是成立的。你想要做速度无穷大的机器做不成,那你就承认相对论是有道理的,光速是有限的。那我就说,那一想的话,物理学家一定是对的,就是说复杂的系统越不稳定,简单的系统稳定。道理非常简单,也是从中国的现实来的,比如说越南战争,为什么中国游击战能打败国民党,它就是一个简单系统打败一个复杂系统,当然,在纽约如果你断电的话,一个摩天大楼马上就混乱。一个蚯蚓把它砍成两断,它两段都可以变成蚯蚓,人给砍成两段,他绝对不会再变成一个人。我就立刻想到了一个经济学的道理,就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定理,就变成一个复杂性和稳定性之间的trade off,中文讲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是一个此消彼长的消长关系,就是说你想要稳定性大一点,你牺牲的代价是你的复杂性或者你的发展的机会,如果你要发展得快一点,你牺牲的是稳定性。所以你就会知道,中国社会的优越性是,中国这个简单系统,自给自足,南泥湾精神,要比西欧的系统稳定。当然反过来呢,它代价呢?如果你搞自给自足,你走武器道路,你牺牲的是工业革命的机会。我想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 那么后来我们又想到,我前年到北大经济中心来工作的时候,我偶然间又发现经济学家有了类似的问题,非常著名的芝加哥已经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叫斯蒂格勒,他在1951年就发现一个亚当·斯密的困境。此话怎讲?我们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有两个非常著名的理论,一个叫“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是什么意思呢?就意味着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也就是说你进这个市场的话,没有不任何人能够操作这个市场,大家都是机会平等。但亚当·斯密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叫“斯密定理”,他是说劳动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的限制。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比如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农村劳力过剩,大量的人口要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你的方向怎么办?中国很多善良的经济学家呼吁应该发展小城镇。如果你学过亚当·斯密定理,你就发现,小城镇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城镇很小,劳动分工就受规模限制,你的服务业就发展不起来,所以你只能发展大中城市,你才能发展劳动分工,才能吸收大量的农村人口。但是如果亚当·斯密这个定理是对的话,它就跟前面的看不见的手矛盾了,为什么呢?你达到这个市场规模限制的时候,就出现什么?就出现垄断,所以你马上就证明马克思的预言是对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结尾一定会导致垄断,垄断也就会……,照列宁说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就要灭亡。那这就是林毅夫老师讨论的问题了,为什么现在资本主义不但不灭亡,还有生命力呢?那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是亚当·斯密的这两个东西,在现实里面能不能共存?事实上永远都在共存。为什么?你看美国,它有大量的小企业存在,也有大量的跨国的垄断的企业存在,如果要照我们选优的理论的话,你就要么相信完全市场都是小企业,要么就相信,全是垄断企业,基本没有小企业存在的余地,你怎么理解这两者的共存呢?那么这个共存的问题,在传统的均衡的理论里面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在我们复杂科学里面就可以解决,解决办法就是拿我做研究生的时候,1987年发现的复杂性和稳定性之间的消长关系,所以我就在去年提出一个广义的斯密定理,就把原来的斯密定理给推广了,原来斯密定理讲就是说,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我发现这是不完全的,应该正确的表述,我是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表达,今天我不讲数学,我讲思想就好了,它受三样因素的限制,第一个限制是市场规模,因为每一个技术到后来达到它的潜力以后,效益都会递减,比如说种地,你拼命的投入肥料或者人力,到后来它产量增长越来越缓慢。但是,你要新的技术革命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新的资源,所以你第二个限制是资源的种类,比如说我们中国如果老呆在土地上,你要发展它,你就没有前途了,但是如果你开辟新的资源,你发现新的矿产,甚至发现新的脑力的资源,我们现在开发新的信息,那你的资源种类越多,你创造财富的机会越多,所以它第二限制于资源的种类。第三呢?受限制于环境的涨落,这话怎么讲?这话就是前面我讲的,如果你环境的涨落非常大,大起大落,那么这个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它就会从复杂系统简化为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比较高。如果你系统的涨落相对比较小,那么这个系统才有可能从简单系统演化成复杂系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同意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创造力,当然农民战争不是自觉战争,是统治阶级逼出来的。但是你就知道,这个涨落非常大以后,会使得这个社会经常打断重来,打断重来,所以中国好多发明都会失传,好多发明重复发生,因为它没有一个连续的积累的系统。所以,你就会得到一个一般的结论,如果一个社会,它这个社会是鼓励创新和发明的,不断创造新的资源,而且社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么它的系统才能够从简单向复杂演化,才能产生劳动分工,产生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形态。否则的话,你就会往另外一个方面演化,所以演化是象树一样的形状,而且演化可能是双向的。这一条也可以顺便就回答了,我们五四以来辩论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全盘西化,如果你是一个均衡理论的话,你从时间、空间任何一点,可以走到任何已涉及的目标,但是如果象个树一样,你就知道,你到了这个杈上,你就跳不到那个杈上,所以你的演化是受你的历史、经济还有生态条件的制约,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最后我想,我们可以稍微用一点(时间)来讨论中国的改革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争论到底是应该在发展中求稳定,还是在稳定中求发展。那我就会偏向说,稳定中求发展要好一点,如果你发展太快,造成社会大动荡的话,你就会倒退到原来简单的系统中去了。这是一个。
但是另外一个呢,有没有可能说,对一个企业,比如说国有企业保值增值,也不可能。一个开放系统里面,唯一能够做的是保持你的竞争力,要么你就被淘汰。所以保持竞争力保守的文化,是阻碍劳动分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然后一个风险,喜欢冒险的,进取的文化,才有可能发展劳动分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的那个书。叫《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学》,我在里面还专门做了一个模型,就是说,两种文化竞争的时候,一种是保守的文化,一种是进取的文化,那么进取文化有利于劳动分工,保守的文化有利于社会稳定。然后还有现在我们金融改革里面,能不能防范金融风险,我想就不能防范金融风险,为什么呢?你在一个正常的金融市场里面,风险和回报是正相关的,你可以防范舞弊,没有办法防范风险,所以你应该是“大禹治水”开渠道,而不是(衮???)治水,到处修堤坝,堵决口。所以我就在讲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一个新的学科,叫非平衡态物理学,或者叫复杂系统科学,可以打破原来劳动分工的学科的局限,把生物演化、社会演化、经济变革里面的问题,从一个自组织科学的高度来理解,谢谢。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先看一看,来自凤凰网站的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叫“快刀浪子”。他说,听说您1979年曾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同时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中国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我很佩服您,网友说,我很佩服您,您很有远见,那么早就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指出了一条通向开放经济的康庄大道,而且您那么早就有了商业意识,竟敢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种大刊上一稿两投?
陈 平:这个事情我要讲一下,这不是我的远见,因为当时我能读到的书是有限的,所以我出国以后,就知道有一个美国文化人类学叫哈里斯,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小册子,叫做《猪、母牛和巫婆》。他就是用生态的原因来解释文化的差异,包括为什么伊斯兰教不吃猪肉这个问题。但是我是用生态问题来解释中国更大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所以是不谋而和,但是我并不是第一次从生态来解释马克思的思想。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文章能够发表,是经济改革的领导人的决策,而不是我的勇气,因为我这个文章,我是在七十年代中就写好了,我根本发表不出去。《光明日报》拒绝发表,说你的阶级斗争呢?我说阶级斗争,马克思早就讲过了,我没有贡献,我的贡献只在这个地方。但是后来中国因为要进行改革,改革的话,突破点在农业改革,当时的主业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毛泽东的以粮为纲,前面我不是讲过以粮为纲吗,毛泽东思想就是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然后那时候我们文化革命的号召叫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后来我就明白一件事情,这个事情事实上朱元璋讲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所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要做一个注解,就是有粮则有军,有军则有权,这是中国内战的逻辑,但是对西欧统一的逻辑并不一样。所以当时很有意思,做经济改革的好多领导人,都从科学院出来的,说你能不能简单写一篇文章,说明你的观点。结果我一个晚上就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就拿到,当时东北的一个农业政策的讨论会上去,目的是要打破以粮为纲,转为全面发展。打破以粮为纲以后,才允许农民自己决定种什么,然后你才可能包产到户,才有增长余地,如果你包产到户,还下令种粮食的话,那就不行了。人民公社制度,它不是为了鼓励生产发展,而是为了保证国家安定,强制农民种粮,要粮食安全,这么一个考虑。所以这个文章在人民、光明同时发表,是我们国家改革派领导人一个政治决策,而我只是起了一个小卒子的作用。
主持人:下一个网友的提问,这个网友叫做“不喜欢台湾的三毛”,他说,陈教授您好,我对您有一种复杂的感觉,你曾说,中国的股市的症结是政府干预不当,而股市大起大落,与政府干预有很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股市是政策市而不是经济市,这是陈教授说的。陈教授还接着说,这给金融机构公款炒股提供了机会。然后又是网友的评价了,他说您的这个观点我很赞成,并喜欢听到您现在更细致地阐述它,但是我必须告诉您,台湾的三毛也叫陈平,我劝您趁早改个名。
陈 平:这个问题我已经苦恼很久了,就是说,同名的人很多,刘邦的左丞相是陈平,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是陈平,现在北京还有一个集团董事长也叫陈平,还有一个画家叫陈平,所以叫陈平的名字非常多。但是我这个名字是我的外祖父给取的,因为我生在抗日战争,所以中国世代的愿望都是要和平,所以我就知道,我的取名是和平。但是我跟我父母讲,我应该叫“陈不平”就对了,我一天都没有太平过。但是我真的想不出应该改什么名字,因为我没有找到一个字或者号能代表我的风格,因为我老在那里变化。
主持人:行,那我告诉这位网友,这个陈平跟台湾那个陈平根本就不是一码事。他还是想听到您对股市的一些见解。
陈 平:中国股市的发展,我觉得大的趋势还是好的。因为所有的股市的发展都有一个大起大落,然后逐渐规范化的过程。所以你就看美国大箫条以后,股市监管严厉了很多,但是也不能防止股票市场的崩溃。所以在经济学界里面,金融领域只有两派,如果相信均衡理论的话,也就是叫“有效市场假说”,他就证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是对的,政府不用干预也行。但是现在我们做非均衡经济学的人,就越来越多地发现了,股市内部是不稳定的,为什么呢?你看见股票价格涨,如果相信均衡的话,你就应该卖,他不但不卖,他还要买进,为什么呢?他相信股票市场还要涨,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机制,那么这种情况底下,就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修改市场的规则,比如说限制换手率,或者是换手太高要收税,或者是政府干预的时候要降低过度反应,要降低时间的延迟。中国政府经常干预时间太晚,说粮食价格低的时候,说粮食不足,它进口粮食,结果等它进口的时候,已经生产过剩。经常会有这种问题。但是最重要的办法,还是要加强市场的竞争,就是市场竞争,防止垄断,是打破少数做庄,操纵市场的可能性。所以政府扮演一个角色,我想要比较多的从亲自干预,变成是制定良好的游戏规则,来当裁判,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然后在市场本身,也不能够自动达到稳定,要让市场健康地发展,第一要降低进入的门槛,让更多的,现在主要大量的经营良好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它不能入市。但另外一方面,你要打破少数国有银行,打破少数国有基金的垄断,让比较多的人参与竞争,这样股市就能比较健康的发展。
观 众:陈教授,我想请问一下,您刚才说到中国传统上都是长期的闭关自守,但是我看到的一些历史材料上面讲,说中国从明确的海禁是从明代开始的,但是实际上研究的结果表明,“大明海岸不寂寞”,这好象是方舟子先生的一篇文章,而且据我看一些闲书所得来的感觉是,明清实际上对东南亚的这种民间贸易还是很繁荣的,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您这个。
陈 平:这个你说的也很对,因为做科学的人喜欢抽象和简化,如果你要把所有的历史细节放进去,那你的理论就没有了。所以如果严格来说的话,中国社会从来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如果要封闭的系统的话,它应该是静止不动的。但是你会发现,中国社会还在变化,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农业区从中原地区扩展到江南地区,这是很大的变化。第二,中国的象吸收那种,红薯、玉米这种高产作物也是很大的变化,所以中国人口增加了很多。然后中国的丝绸之路的贸易和海上跟阿拉伯的贸易量也很大。但是你马上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市场产生的过程里面,主要经历的一个矛盾,就是说你是要搞关税保护,还是要搞开放竞争。事实上欧洲经过几百年的路才走过来的。中国改革一开放的时候你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是羊毛大战,是否你还记得?是价格大战,封锁产品,还是开放竞争。所以它每一个社会,面临外来竞争的时候,永远有一个政策选择,一个是你要不要升高保护壁垒,还是强化开放的竞争。所以严格来说的话,你会发现,中国的政策在两个之间摇摆,一个摇摆就是说,因为中国冀朝鼎有一个非常好的分析,就是中国统治是控制富裕的产量区,主要集中在江南一带。然后政治中心是在北方,因为要对付游牧民族的侵略,所以它把粮食运到北方。所以你就会发现,中国在政治经济的选择里面,也就是说在萨缪尔森一开始讲经济学的时候,是在大炮和黄油之间选择,也就是说在军用和民用之间选择,也就是林毅夫老师讲的,赶超还是比较优势的选择里面。中国经常是把政治、军事的考虑放在经济发展的考虑的前面,它一旦感到安全威胁的时候,它就强调要粮食安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对中国是非常深刻的教训,包括大跃进,包括以前的汉代的屯田,都是造成短期的农业的利益,然后造成长期的生态破坏,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中国是除了撒哈拉沙漠以外,北非以外,中国是生态环境最困难的国家之一。这个行为要不改变,中国将来的前景就很可忧,如果这个心理能改变,中国的竞争将在世界上是非常好的。
主持人:接下来看两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名字叫“骑着毛驴来上网”,他说鲁桂珍,鲁桂珍是李约瑟先生在中国娶的中国太太,他们俩结婚的时候好象两个人都八十多岁了。现在想起来非常浪漫。网友说,鲁桂珍在李约瑟小传中坦言说,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我知道,这又是网友的说话了,说我知道,这老家伙根本没有正式听课学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了一下,所以,他根本不能算圈里人,最多只能算是票友中的名票而已。我估计他的意思是您就别研究他了,不值。
陈 平:我觉得他的问题很有意思,我在给我们经济研究中心的同学上课的时候,我开章名义就讲一件事情,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我说这句话只对一半,为什么呢?知识也是负担。为什么呢?所有新科学的创始人,你去看马克思也好,达尔文也好,牛顿也好,爱因斯坦也好,都是知道甚少的青年人,但他知道老的一代人的问题所在,他会有新的思想,如果你学很多的东西,你就没有创造可能性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来说,我觉得李约瑟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象我这个是理科中学,理科大学出来的,从来没有受过人文历史的正规训练,反而能看到所谓的反常现象。
主持人:他的意思是,您也是票友?
陈 平:我现在已经从票友转化为专业了,为什么呢?原来我在大学里面人家给我起个外号,叫“杂家”,非常奇怪的,现在新兴的科学,改成叫复杂科学系统,所以我现在成了复杂科学系统的创始人之一。
主持人:下一位网友叫做“像我这样的八戒”,这位网友说,李约瑟沉迷于道教和长寿术,热心收集房中术书籍。有一次,他在北京琉璃厂,一位出名的女老板那里买到了《双梅警案丛书》,李约瑟一阵狂喜,说这本书是伟大的中国性学著作,而且他在中国科技发展史第二卷专门写了房中术,大谈采阴补阳和还精补脑,还说这些理论具有很大的生理学意义。他有一番话,真让我这个四川八戒受不了,他居然说,当他问一位四川人有多少人按照房中术的训诫行事时,得到的回答是,四川的绅士淑女,半数以上都是这样做的,请问陈教授,这老色鬼的话您也信以为真吗?
陈 平:我没有注意这个李约瑟研究房中术,但是我倒是非常注意研究中国和西欧的美学观点的不同,因为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是学素描的,然后你就知道,西方的,希腊人的美的观念,是裸体美,中国的画,画画都穿衣服的。所以我后来出国以后,就发现,西方的观念是普遍状态,你去看看,印度那个佛像,那个女孩子的乳房都圆滚滚的,然后中国的佛像就看不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你去看非洲人和印地安部落的文化,对性的崇拜都是非常鲜明的。这个有什么道理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说对做科学的,喜欢自然的状态,而且喜欢科学独立的发展。这个东西怎么出来的呢?我到巴黎去,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巴黎的建筑都是古典的,它受希腊罗马文化影响很深。建筑上面都是雕塑,最高一层全是女神,中间一层都是小孩,小天使,代表天真可爱,最底下,第三层,才是丑恶的男人,将军、主教、元帅、政治家这些。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观念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就是说,抱着一个平常的心态来研究的话,其实你就会发现,中国在性的方面,要比西方不亚于,比如说西方在基督教以后,强调一夫一妻制,但是又有很多情人。中国呢,公开的就是男女不平等,男的可以很多妻妾成群,皇帝有宫女上千,而且中国也不以为怪,我觉得这个事实上可以研究的。
观 众:谢谢主持人,我提一个跟您今天讲的不太有关的问题。就是说,我看了一个也算是很有名的人,他对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评价,他说……可能是有所指,可能是跟北大经济学家也有关系,因为我觉得你特富有批判精神。他是怎么评价的呢?他说,现在经济学界存在着幕僚情结和帮忙主义,他们坚守在岸上大呼小叫,捕风捉影等等,我记住了头。我觉得,您作为他们群体中的一员,您怎么评价。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经济学家都是支持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集团中的一员,那么您从属于哪个既得利益?那么您为哪个集团服务? 陈 平: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已经变成一个经济学家,我非常希望成为经济学家,但是我每次在国外或者国内,在国外是挑战主流经济学,在国内是请教国内经济学家的时候,我总是说,我是物理学家出身的,所以我愿意当经济学家的学生,我现在还是学生,所以我不认为我已经变成经济学家了。第二,我认为中国经济学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工程已经是国际化的,所以非常有竞争能力,但是中国的经济学界还是传统的人文的规范,比如说非常奇怪的事情,包括北大,包括教委,对学科的分类都是不合科学常理的,因为我做物理的,物理有四大基础科学,力学、电磁学,统计物理,量子力学,经济学有三大基础课,微观、宏观、计量,这些东西在中国被称为“西方经济学”,我是做宏观和做计量的,所以我就不能带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生,我只能说要么我选西方经济学,要么我选金融学,所以我现在带博士生的项目是金融学,金融只是我的一个应用的领域,并不是我的主业,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国内对社会科学的看法还是落后在以前的时代。我想,科学如果对的话,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改革的经验,应该融入世界经济学宝贵财富的一部分,而不能讲我是中国特色经济学,那我就跟人家不一样,这你是作茧自缚。第二我不赞成国内经济学界没有劳动分工这个传统,这是我非常反对的。所以我最近建议我们的新闻记者,以后报纸上报道的时候,不要用著名经济学家这种提法,也不要引用某某人是人大还是科学院还是什么职位,哪怕你得过诺贝尔奖,也不能证明你的观点是对的。但是你可以要说明他是哪个领域的专家,你到底研究的是货币,还是研究的证券,还是研究的债券,还是研究什么,你让人家明白你是哪个领域。然后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会知道又有不同的学派,你是什么学派,什么方法,我就知道你怎么分析这个问题,而不要用一个职位来吓唬人。这样来看的话,中国可以被称得上是有贡献的经济学家,在世界上被同行所认可的,就非常之少了,所以我不晓得你说的经济学家他们是什么样的经济学家,谢谢。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希望您用一句话回答我,您说这个中国的劳动分工为什么难以发展?原因是什么?一句话。
陈 平:环境涨落太大以后,发展单一农业经济。
主持人:好,谢谢您。追求进步,学术倾听,世纪大讲堂向您道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谢谢陈教授,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