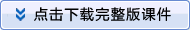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主持人:追求进步,学术倾听,世纪大讲堂向您问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哲学好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学问,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哲学多少带点洋味道,那今天呢,有人提出哲学也要现代化和民族化,这位大师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陈来教授,好,有请陈教授上场。
陈 来:你好,阿忆。
主持人:请坐。我听人说,如果是您跟一个哲学以外的老师说话的话,这个老师都会笑。但是如果您跟哲学老师说话呢,哲学老师只能是眼睛里发出深邃的光,一般是不会笑的。
陈 来:北大校庆的时候,有个记者也叫阿什么,阿旭大概是。
主持人:跟我的姓是一样的。
陈 来:给我照一张相,不许我笑,要我表现出一个深邃的、冷峻的目光。
主持人:是不是我们在网上轻易搜索,就可以看到您穿着风衣,在燕南园里(的照片)。
陈 来:没错,就是那张。
主持人:而且不管是在哪个网站去搜索,搜索您的第一条信息,就是这张照片。
陈 来:其实那根本不是我的性格。
主持人:您的性格是老笑。
陈 来:我的性格其实很随和,而且不能说喜欢笑吧,但是也不排斥笑。
主持人:让我们了解您一下,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哲学的想法的?
陈 来:我哲学意识应该是1969年。
主持人:1969年,您是?
陈 来:1969年那个时候,我是上山下乡,那时候我到内蒙古西部。
主持人:您在那么苦的地方,大家都是想弄个萝卜吃一吃就很好了,您在想哲学问题?
陈 来:那个时候虽然谈不上温饱吧,但是大家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并不是很高。而那个时候呢,社会环境啊,给大家造成一个力量,就是促使大家去学习这些东西,特别是哲学。当然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也好啊,毛泽东思想也好啊,那个时候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那个时候开始有哲学的这些想法。
主持人:据我所知您的本科是工学士。
陈 来:没错。
主持人:怎么没有当时就报哲学呢?
陈 来:因为我上大学那个时候,是不能自己选择志愿的,因为我是从农村出来,那个时候上面给你分配哪一个地方去上学,那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
主持人:那读这四年地质的时候您是不是非常痛苦?因为您也不喜欢它,是党给您派去的。
陈 来:那倒也不是,因为我对知识本身是有兴趣,虽然那不是我自己最心仪的专业,但是很多的知识对我来讲是新的,好多知识呢,也都是我自己自学的,所以大部分可以说百分之八九十的课程,我都是在这门课程的前一个学期甚至前两个学期就自己自学完了。所以很少有的课程是我被动的听老师学的,都是自己主动的把它学习来的。
主持人:那您当时地质学得好吗?
陈 来:因为我们那个专业一方面是地质类的课程,另一方面很多机械类的课程。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我觉得掌握起来不是那么难,我也有一定的兴趣。但是同时呢,我在当时那个时代,那时候叫又红又专嘛,就是你除了这些课,学的专业知识以外,还要寻求一些人生理想,所以我在当时的工科院校也念了很多很多的哲学的书,当然也包括历史,经济这方面的书。
主持人: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学哲学了?
陈 来:真正呢,当然是到1978年开始。
主持人:1978年您又考上了研究生了。
陈 来:研究生。这是1978年开始恢复中国的研究生制度,第一年我就考入北大。
主持人:谁是您的导师呢?
陈 来:我的导师是张岱年先生。
主持人:那很幸运。研究生完了以后又接着读博士了?
陈 来:没有,研究生念完了以后,到1981年我就开始在北大教书了,因为那个时候北大没有开始文科的博士的招生制度,所以到我教书的一年多以后,才又开始,这个时候我才转变为博士生的身份。
主持人:导师是谁呢?
陈 来:张岱年先生。
主持人:还是他,真是幸运。听到陈来老师这么幸运,我们也就能猜到,在一个大师的领导下,指导下,他能够把学问做得非常好,下面咱们就听听他这个好的学问是怎么化做了他今天的讲演,他的讲演题目叫《哲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好,有请。
陈 来:大家好,其实这个题目呢,《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我今天主要谈的还是民族化的方面,里面又牵扯到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就是说从整个文化来讲,不仅是哲学,应该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课题。
我们看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不断奋起、奋争,寻求现代化的一部历史。因此呢,可以说追求现代化,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的共识,我想这一点呢,大家都可以切身体会到。但另一方面,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也可以看作具有五千年历史和渊源的中国文化,它在受到冲击,处于失落,这样一个逆境里面,不断地寻求奋起,寻求新的自我肯定的这样一段历史。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在文化上面,除了现代化的意识出现以外,中国化和民族化的意识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在哲学上来看,一方面我们看到现代化的这个观念,它或隐或显的,影响到许多哲学家,他们关于哲学的那个理解,成为他们建构自己哲学的重要的动力。
那么另一方面呢,怎么使这个哲学的工作能够呈现出民族化的特点,也是很多的哲学工作者,他们内心没有间断的一个内在的冲动,而且随着这个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体现为各种不同的诉求和实践。这个现象呢,是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因为新的世纪到来,我们可以展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的前景是越来越灿烂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从前不太被注意的,关于这个文化的民族化的问题,我想现在提到日程上来了。 今天因为这个课题很大,我们只能就一个小的方面,提出一些浅显的例子,特别集中在我们北大的已故的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他的一些思考上面,来跟大家做讨论。第一个,我想回顾一个现象,这是一个具体的讨论吧,就是我们知道,二十世纪现代化这是个主流,民族化的问题呢,考虑得比较少。在三十年代的时候,有两个著名的哲学家,一个就是冯友兰先生,一个是金岳霖先生,这两位先生呢,就注意到有一个现象,他们就做这样一个讨论,就是说呢,比如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可是我们不会说,化学的民族化,电子学的民族化,我们不会提这类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子?那么在那个时代,三十年代的时候,冯先生和金先生呢,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语言里面,经常会说,英国哲学,英国文学,德国文学,德国哲学,可是我们比较少说英国化学,德国化学,这个我们比较少,这个语言现象怎么解释?那么他就做了一个叫“的”和“底”的分别,底就是瓶子底的那个底,汉语发言,在口语上都叫“de”,但是在文字上面有这个分别。他说,当我们说英国文学、德国文学,这个时候呢,我们讲的是英国底哲学,德国底哲学,或者英国底文学,德国底文学,这个“底”呢是一个形容词的意思,表示这个学术形态呢,它有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一个特性。那么当我们说英国化学或者德国化学的时候,不是指英国底化学,我们只是说英国的化学,德国的化学,这是什么意思呢?“的”在这个里面是一个所属的关系,表示我在这个地方发生,是在这个地方出现,并不表示说,它跟英国的语言,跟德国的语言,英国和德国的文化传统有什么特别密切的内在的关系。那么这里面呢,从这儿讨论,他们就发现“的”和“底”的用法,可以演变出一套宏观的理论,就是我们在人文科学里面呢,有很多很多都可以用到“底”的,特别是文学,因为文学是要用特定的民族的语言,那么哪种语言里面有它自己这种民族语言的一种特别的技巧,那么这种特殊的民族语言它会形成特殊的一些文学的趣味和文学的技巧,当然包括审美的特点。因此呢,它所体现出来的这些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里充满了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文学呢,一定是“底”,它是充满了这个文化,这个民族的传统的这些特色。科学,科学一般来讲,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科学,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写作,当然会用不同的民族语言来写,但是他所追求的是一些公共的、普遍的这些真理,这些原理,那么这些普遍的原理,虽然可能借助于某种特别的文字表达出来,但是这个文字和这个原理之间,照它来讲,没有那种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呢,他就指出来,说哲学到底是属于什么形态呢?他就发现,哲学处于文学和科学之间,兼有它们两种特点,一方面哲学也是追求这种公共的,普遍的这种原理,可是另一方面呢?哲学跟它这个民族的传统,跟它的语言也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从这个“的”和“底”的分别呢,他就发现,哲学也是可以有民族性的。 那么冯先生呢,他就以金岳霖先生为特点,他说金先生有两本书,一本书叫《论道》,说《论道》这个书啊,它是“中国哲学”,而不是“哲学在中国”。他说金先生还有一本书,叫《知识论》,他说这个《知识论》不算“中国哲学”,是属于“哲学在中国”。那这里面又有一个新的名词出现,就是“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或者说中国的哲学和哲学在中国。这个所要表达的分别,跟三十年代表达的“的”和“底”是一样的。那么三十年代他们用的,象冯友兰先生用的那个“的”和“底”的用法,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用,也有些人“的”和“底”是反过来用的,但是以后呢,现代汉语慢慢变化了,不管哪一种用法,他们的那种区分已经意义不大了。所以他又用新的语言来作区分,就是用中国哲学或者中国的哲学,表示有中国性的,表示有中国性的哲学,那么另外一种,叫做哲学在中国,照他来看,就是有两种,我们做哲学工作有两种,就是我们中国人做哲学工作有两种,一种我们做的叫做哲学在中国,那么这里面呢,不是刻意地去凸显,去表现,或者去继承,或者去发扬,那么跟中国哲学、古代哲学的资源有密切关系的,这个方向。那么另一方面是中国哲学,或者叫中国的哲学,那么这个方向呢,它是继承、发展,当然也有改造,跟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有密切关联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是他到晚年提出的,就变成“的”和“在”了,不是“底”和“的”,而是“的”和“在”,中国哲学,中国的哲学和哲学在中国,做这样的分别。那么这里表达的同样是,所谓哲学,中国哲学或者中国的哲学,这里面所凸显的中国性,其实就是个民族化的问题,这个民族化就是跟中国文化的传统,跟中国哲学的,古代的传统有密切联系的这样一个方向。那,我刚才讲,我们要以冯友兰先生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看,前面都涉及到他,那么他自己的观念是什么呢?我们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册,我们就看到,他说,中国需要现代化,哲学也需要现代化,这是第一句话。第二,他指出来,他说,他自己所谋求的,所致力的是作一个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就是他要作的这个哲学,一方面是一个近代化的哲学,一方面呢,又是一个中国性的哲学。那么要做这样一个哲学,他指出来,做这样一个哲学,不是凭空,我们没有任何基础,一下子就可以做出来,就是一定要跟传统有一个接续的关系,你这个中国性才能表现出来。那么另外呢,你如果仅仅是跟传统接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那不是近代化。所谓近代化呢,一定要引进西方的和世界其它的这些文化哲学资源,来重新了解、分析和构造我们的中国哲学。那么这是冯先生他自己一个追求。那么这个目标,这样一种工作的方式呢,他有时候用另外两句话来区分,来表达,他习惯上,是什么话呢?就是“照着讲”和“接着讲”,他喜欢用“照着讲”和“接着讲”这个话来区分,照他来看,照着讲,是保持中国性的一种方式,比如,古人怎么讲,我们也照着这个讲,那么这当然是一个中国性的表现。那么可是这个照着讲呢,它不是一个近代化的东西,那么只是重复古人,再现古人的讲法,这个不是冯先生的工作目标,所以他讲,我的工作目标是要采取接着讲的方式,那么什么是接着讲呢?接着讲就是一定要接引西方的这些的文化资源,对中国的传统的资源进行分析、重建,这样一条工作。所以照着讲和接着讲这个分别,我们习惯上呢,是把它作为说,照着讲就是不发展,接着讲就是发展,这个解释呢,是单一了一些,就冯先生的意思不止于此,就是冯先生不只是强调说哲学不能够故步自封,还是要发展,有照着讲和接着讲这个不同,那么冯先生讲的照着讲和接着讲,里面包含着近代化和民族化的统一这个问题,以前这个大家没有很好的注意。他说,只有用西方的哲学的方法,来分析和研究中国这个哲学资源,这个才是接着讲,所以冯先生他讲的接着讲,他不仅仅是说要发展,而且包含一个学术转型,不仅要转型,又在这个转型里面,要保持中国性,发展这个中国特色,中国性。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冯先生的一些努力吧。 那么哲学的这个民族性呢,怎么体现,或者有什么地位?他认为呢,可以说,用两个方面来讲,来表达,一个叫做“就哲学来说”,一个叫“就民族来说”。就哲学来说,他说呢,就哲学来讲,就是把哲学作为一个普遍的学科,普遍的一个类型的学问来说,那么各个民族的民族性的特色,在这里面是一个外在的形式的因素。可是呢,如果我们要就民族来说,那就不同了,比如说,我们就看爱因斯坦这个个人,那他长的什么什么样子,他的性格如何,甚至他的口音,他的各种爱好,都是这一个人区别其他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特点。所以哲学也是一样,哲学的民族性也是一样,照冯先生讲,如果就民族来说,一个国家的民族的哲学,它能够提供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人民,给他一些非常重要的,而别的东西,别的民族的东西所不能给予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满足,和精神上的愉快。他甚至提出来,包括能够促进这个民族的精神上的团结。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哲学的这种民族性,就不是可有可无,外在的东西了,就变成这个民族生存,它的精神生活,在精神上存在的重要的条件,变成相干的,内在的因素。那么这个民族性,就形式上的体现两个方面,一个呢,它的讨论是接着这个民族的哲学史来讲的,这是它体现它民族性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它的民族性体现在,它用它自己这个民族所熟悉的,跟它的这个文化传统密切关联的语言来讲述的,那么如果你,讲哲学,你是接着西方哲学来讲,不是接着中国自己哲学问题来讲的。那么这个呢,就不能体现这个哲学的民族性。那么这种接着讲,不是冯先生所讲的那种接着讲,所以冯先生所讲的这种哲学的民族性的接着讲,他是讲,你要接着中国这个文化的传统,中国哲学里面传统的这些问题来讲,那么这个叫做中国性的这种哲学。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问了,就是说冯先生这些思想呢,有的刚才我提到表达,特别是说,他说这个哲学的民族性的表现,能够促进这个民族精神上的团结,给这个民族以它自己别人所不能给予的一种满足,这个话当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讲的。今天呢,时代是不同了,我们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那么全球化的时代,这个民族性的问题,传统性的问题,现代性的问题,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怎么样来看?那么这就涉及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前面所提到的这些问题的互相的连接。那么我想这里面仍然可以提到冯先生在谈到民族哲学的时候,它的一个别的区别,“程度的不同”和“花样的不同”。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另外也处在一个多元文化盛行的一个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怎么看这 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另外也处在一个多元文化盛行的一个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怎么看这个问题,冯先生当时呢,应该说他有一些先见之明,或者他接触过这样的课题,他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广义地看文化,文化的这种冲突、变化,这种情况来讲,他说文化的这种差异,和对待差异,有两种基本的方式和不同,一种呢,这个文化的不同呢,是属于程度的不同,那么这种程度的不同呢,应该把程度低的改进为程度高的。比方说,牛车和汽车,牛车和汽车这个是程度的不同,那么牛车 呢,就应该改进为汽车,这是文化的程度上的差异,那么这里面,现代和全球化非常有意义,我想我们这一个世纪以来做的工作,都是很重要,要谋求这个东西。另外,他说,有些东西呢,文化之间的差异不是这种程度上的不同,是什么呢?是花样上的不同。你喜欢意大利歌剧,那我喜欢京剧。你喜欢吃这个烤猪排,我喜欢吃酸菜鱼,变成这样,变成一种文化的花样的不同,这种花样的不同呢,照冯友兰先生的看法,花样的不同,不是程度的不同,所以不存在哪一方面要改进在哪一方面,这是一个互相对话,互相理解,那么当然,也可以相互吸收,相互学习,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照冯先生的这个看法,我们对全球化也可以说有类似的看法,凡是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有关系,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有促进,能够使我们这些程度低的改进为程度高的东西,那我们要举双手欢迎全球化,促进全球化。但是如果全球化同时带来一种危险,会消解一切民族文化,把一些地方性的民族文化全部拉平,那么这样的倾向,我们在欢迎这个全球化的这个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有所警惕,我们也要注重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危险面前,怎么样能够注重来发掘和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和中国性,用我们自己的身份来讲,中国性这个问题。 刚才我讲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但是我的主题呢,因为时间的限制,和我个人研究的专业方向,我们是侧重在民族化这个方向。那么由于强调民族化呢,我们比较注重中国底哲学和那个中国哲学,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说哲学在中国,我们中国人做哲学,只能发展这种,不是这样。那么哲学在中国这个方向,我们同样也要大力发展,要继续发展。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在继续促进现代化、全球化的同时,我们觉得这一个方向应该受到大家较多的重视,我们要重新挖掘和总结二十世纪那些自觉地寻求哲学的中国性的重建,这些人,我们要总结他们的工作,看看他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有哪些思考,那么这些思考有没有什么道理。那么我们当然看到,在这一支发展中,是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象我们刚才提到的冯友兰先生,那么在冯友兰先生之外,也有其他的许多先生,比如说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以及所谓有些新儒家哲学的一些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呢,它跟冯先生的工作可能不太相同,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那几位先生,他们可能不是说仅仅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些资料和材料,而是注重中国哲学的那些精神的方向,那么以中国哲学内在的精神方向为依归,或者以中国哲学固有的那些观念和理念为主张,比照西方哲学的这些观念,把它加以阐发,把它加以表达。今天,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想继续推进这个方向的研究和发展,我们要总结他们的经验,要了解他们在这里面的一些苦心和成败,这有益于我们今后我们自己的哲学建设的工作。 最后我们可以总结讲几句话,就是当代哲学和文化的发展,显示出根源性、民族性、地方性,这些东西,和世界性、普遍性、现代性,这两组东西不是启蒙时代所理解的那种非此即彼的那种对立,而越来越被大家理解成为一种我们叫做对立的统一这样一种辩证的关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也就是说可以普遍化的。所以作为我们在参与迎接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一个成员,我们在一方面促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的同时,要深入的思考,考虑怎么样进一步的挖掘、再现和重建中国文化的中国性。这是我今天讲的一个基本的内容,谢谢大家。
主持人:好,先看一下来自凤凰网站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一个叫做“思想被我三姨所控制”的网友提的,他说,我真的认为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我的这个想法来源于我的三姨,有一天,我朋友结婚,我给他们买了一束鲜花,回家后,我姨问我,买花干啥,我说朋友结婚送礼。三姨回答,要是我,就不买那东西,我买两瓶水果罐头。我蓦然发现,这就是中国现实,她连鲜花都不喜欢,何况是哲学?您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两个哲学实用的好例子,说服我,我再去说服我三姨。
陈 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哲学有没有实用性。那哲学的实用性是要比较广义的看,比如说哲学包括很多的门类,哲学里面包括很多的门类,不是我们现在、以前所讲的,只是一个对世界普遍规律的一个了解,不是那么简单。比如哲学里面有一门学问叫做伦理学,伦理学是讨论怎么样做人的问题,这个是很实际,这就是很古老的学问,你到哪里,在我们中国社会里要碰到做人的问题,哲学,特别我们中国传统的哲学,是要跟你讨论怎么样做人,做人这个问题重要不重要。这就是一个很实用的。比如说,象新的问题,比如说现在有所谓的克隆人,这类的问题,克隆什么什么东西,那么引起很多叫做生命伦理,一些新的伦理学的问题,那么哲学有一支就是伦理学,伦理学就要讨论这些课题,研究这些问题,这个就是很实用的。那么再比如说,哲学有一个门类是美学,美学当然是在理论上讨论审美的,但是美学呢,也跟我们这个生活中的审美现象有很多很密切的关系。
观 众:陈教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以前一般的观点都认为,中国的哲学就是一种儒家的思想,但是现在有些人认为,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哲学占过统治地位,因为在象秦朝以前是百家争鸣,秦朝法家占统治地位,然后汉朝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一种改造,这时候它已经不是原来那种真正的儒家思想了,到唐宋时期,然后佛家,还有一些宗教思想开始占有一定的地位,然后到明清,中国正统的哲学思想已经不太明显,这种概念非常模糊了,您对这种观点是怎么看的?中国究竟有没有一个哲学真正占过统治地位?
陈 来: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它是有发展过程,我们的概念、我们的理解里面是要允许它发展的,不能说,儒家只能是孔子和孟子讲的那个,如果讲得比孔子、孟子多了就不是儒家了,比如说董仲舒,董仲舒他讲当然跟孔子、孟子那个时代有点不同,他吸收了一些阴阳家的讲法,吸收了一些别的东西,包括一些这个……当时甚至某些,当时的那些比较原始的自然科学的一种讲法,这种感应论,这种讲法。但是不等于说他就不是儒家。那么到宋代以后,就是所谓宋明理学,宋明理学里面也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很多佛教的一些理论思维,但是这不等于它就不是儒家,所以儒家本身它是有一个发展的。那么至于说,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哲学占主导地位,那么这个呢,当然是各个时代不一样,这不能有一以贯之的讲法,比如说在先秦,先秦是百家争鸣嘛,但是百家争鸣里面呢,虽然有比较主要的,比如百家争鸣里面,在早期是儒墨,儒家和墨家,儒墨为显学,这两家势力最大。你刚才讲了,到秦国的时候,法家呢,通过政治取得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时间比较短。那么到魏晋的时候,是新道家出现,玄学,玄学是新道家出现,到了隋唐,当然佛教的影响是比较大。但是如果我们看,从十世纪到十一世纪以后,这段历史,这个酝酿着新的变化里面,儒家思想可以说占了一个最重要的地位,虽然这个时代里面还是有佛教、有道教,有所谓儒释道三教,甚至还有三教合一的提法,到了明代的后期。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可以说儒家思想就占了比较主导的、中心的地位,特别是它的新的形式,所谓新儒学,就是理学,而且一直接续到我们的所谓前近代,就是跟我们现在这个近代最近的传统,我们现在最近的传统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应该实事求是,应该承认这个。
观 众:您刚才说冯友兰先生在三十年代的时候,他的主要工作是以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哲学为素材,引用西方近代哲学观点来审视来继承中国的传统哲学,那么为什么冯友兰先生不倒过来一下,就是以中国的传统哲学和思想为基础,来吸收和批判外国就是近代的那些哲学观点?就是说,冯友兰先生不选择后者,而选择前者,在三十年代这种历史背景下,有没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陈 来:我想,因为冯先生在三十年代他是一个比较注重现代化的,是比较注重现代化的一个观点。一方面是社会的现代化,一方面是哲学的现代化,他是比较注重这个的。所以呢,当时的知识分子,我想普遍象你讲的那样,非常关切,怎么样从西方引进很多先进的东西,一些好的东西,我们缺乏的东西,来帮助中国进一步地发展。所以我想,那个时代应该说,不就政治层面,帝国主义当然都是要批判的,就是你刚才提到,为什么冯先生不选择以中国的思想为基础来批判西方,是吧?我想当时呢,不仅是冯先生,一般来讲没有这个潮流,那么当然了,冯先生在这个时代,他注重现代化,所以他在经济上,在文化上,他都非常注重吸收西方的东西。那么但是因为他同时又是个中国哲学家,他就想把这两者结合,所以他采取的,比如说《新理学》这本书,他写一本书叫《新理学》,不是老的理学了,是新的理学,新的理学就是接着讲,照着讲就是老的理学了,什么叫新理学?新理学就是那些概念,还是中国的概念,但是那个讲法,和那个问题的组织方式,这个就变成一个西方了,这是他选择的一个路径,这个选择呢,当然是跟整个当时这个时代,大家怎么样思考东西文化的问题,考虑中华民族的现实处境那是联系在一起的,是跟这个背景有一定的关系的。
主持人:好,下面看两个来自凤凰网站的网友的提问。先看这一个。这个网友的名字叫“会跳迪斯科的现代大儒”,他说请问陈老师,哲学是否有一个真正的分支叫生活哲学?据说林语堂和周国平就是这样的哲学家,就是生活哲学家,他们写的书都是畅销书,好象现在的大学教授就是看不起那些能写畅销书的教授,我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复兴哲学,促进哲学现代化和民族化,您怎么看林语堂和周国平,会不会看不起他们?
陈 来:那不会了。我想他讲的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这些人的工作是有意义的,而且应该受到重视,我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另一方面,这个,他讲的另一方面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就是说,因为这个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不管是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学科,还是在现代教育制度里面的一个教学的领域,它确实没有生活哲学这一门。
主持人:根本就没有这一分支?
陈 来:它没有这个名称叫生活哲学这一门,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不等于不讨论生活问题,我刚才讲了,伦理学里面当然是讨论生活问题,象林语堂里面讨论的问题,象周国平所讨论的问题,有些是属于人生哲学,在伦理学里有一个表达叫人生哲学,是跟人生哲学有关系,但是他们的表达呢,可能是比较具体的,比较文化的,比如林语堂,那么这个呢,在广义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跟人生哲学有关系的一种表达。但是就哲学里面,我刚才说作学术研究领域本身来讲,人生哲学呢,它也有它理论上的一套做法,就是这个学科里面它有一套规矩,就是要做人生哲学怎么样做理论的表达,这些规矩当然不是不可以打破,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做人生哲学的人呢,就是看不起前面提到这两位先生的工作,据我了解,应该不是这样。只是说,他们不是选择这样的方式,是选择比较理论化的建构方式,而不是选择象林语堂和周国平,他们这种比较具体的、具项的,甚至文学性比较强的那种表达。所以就我个人来讲,我不会说看不起,我很佩服,我很佩服写畅销书的,因为我写不出畅销书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畅销书都是好书,这也是同样的道理。我想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主持人:这位网友呢通过您的这个回答,知道了您不会看不起这两位写所谓生活哲学的作家兼哲学家,但是他不知道,我觉得我应该替他追问一下,您会不会不仅是不讨厌他们,而且跟他们一样,也去写这样的书?
陈 来:我其实呢,向来是肯定做这种比较有点普及性的哲学工作的学者,所以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的主要的方向一定是理论、学术的研究这些方面,我自己,可以说我的职业,我的工作性质,当然也包括我个人的兴趣,是不大会向那个方向发展的。
主持人:行,我听明白了。
主持人:好,先看一下,下面一个网友的问题,这个网友叫“喜欢老梁”,他说梁漱溟和冯友兰都是中国哲学家,但两个人却截然不同,老梁因为直抒心意,而三缄其口,老冯批林批孔,晚节不保,直到他们行将就木,老梁也几乎没有原谅过老冯。据我所知,陈老师曾经是为冯友兰小传写过序,想必呢,有幸认识冯老前辈,不知道您怎样看这两位前辈?
陈 来:那当然,因为冯先生是我们的老师,跟我个人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也给他做过助手,一直到他去世。他讲的这段公案,我想不是……他的了解可能还不够细致,另外这个问题牵扯比较复杂,先说简单的吧,就是说他说梁先生始终没有原谅冯先生,这个讲法呢,我想是不对的。就是梁先生,他曾经跟一个人讲话,批评过冯先生在批林批孔的时候的一些著述、言论,当然冯先生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梁先生,就是讲这个过程,然后把这个冯先生写的自传类的书叫《三松堂自序》,现在在《三松堂全集》的第一卷,把它送给梁先生,那么梁先生后来就来联系,还是要跟冯先生见面。
观 众:刚才你说,就是上个世纪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激进主义的批判态度是主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割裂了我们与传统的关系,那么您现在也提倡哲学的民族化,那这种割裂给哲学的民族化带来哪些困难呢?
陈 来:对,我觉得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比如说,不管从哪一个思潮来看,象五四时代,比如说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比较大,那么后来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比较大,那么在有些时代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由于过分的排斥传统,所以大家的思考就不能向这个方面走,他不会考虑这个问题。比如说在批林批孔的时代,批林批孔的时代,虽然是表扬法家,批判儒家,但是没有人想怎么样建立一个民族化的哲学,哲学的民族性怎么体现。或者象文化革命前期,甚至五十年代后期,这方面大家都不太考虑,觉得这个,可能旧的中国哲学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完全没有什么用了,我们可能是有这样的一种影响,所以还是,应该说是有影响的。就是到了今天,我想大家可能还是这方面考虑得比较少,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现代化的过程有关系,就是当处在一个现代化受挫的时代,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的民族自信心不强,在这个时候比较少,当然有些人还能够顽强的表现、提倡,追求这些东西,但是大多数人就比较少考虑这个问题。但是随着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良好的这种前景的出现,现代化,我想现在大概没有人怀疑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的能力了,所以我想,刚才我讲以前大家少考虑这个方面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观 众:你谈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民族性里,谈二者之间能统一起来,但是我的担忧就是说,我认为二者之间很难统一起来,因为现代化它本身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但是我认为里面肯定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政治,还有一个是经济,还有一个是军事,也就是说,在这种非常现实的意义的影响下,在诉求中国哲学的民族性,有没有可能,也就是说在现实中有没有可能。因为现在老子和庄子对我们现在非常陌生,对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是美国的大片和麦当劳,这些对我们是非常熟悉的。
陈 来:你说的这个现象当然是存在的,但是我想,这可能是个过程,可能经过一段各个过程,现代化越来越平稳,这些大家看的大片也看烦了,慢慢会有一些内在的,一些精神性的一些东西的要求出现,它会重新亲近老子、庄子、孔子,这些书,所以我想,不必悲观,可能现在只是个过程,再过一段看,这个情况我相信会好转。我觉得,一个民族越现代化,那么它的文化的民族化的意识将来也会慢慢的越来越自觉,越来越强烈。另外,我觉得就是说,你讲政治、军事、经济这个力量的问题,因为中国力量弱嘛及所以大家都对自己的东西没兴趣,就对最强的,世界上最强的是美国,就对美国的东西有兴趣。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那么一般的民众可能会受这个影响,但是我觉得有识之士,他会……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纪到九十年代以来,我想我们是中国最强的一个时代。象如果五十年代、四十年代,乃至三十年代、二十年代,中国的处境显然比现在差,中国的国力,显然综合国力比现在差,可是仍然我们看到,我刚才举了很多的发展民族哲学的,发展中国性的这些哲学家,象我刚才提到的冯友兰先生,包括金岳霖先生的《论道》,冯友兰先生也认为是中国的哲学,那么象熊十力先生,象梁漱溟先生,还有一些其他的先生,还是有的。当然,哲学家总是少的,不管是做哪一种哲学,是这种中国性的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都是少的,在人口比例上还是少的,但是我不悲观,我是认为,还是,即使在现代,仍然是有这样的人,而且会越来越多。
观 众: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记得梁漱溟先生好象有一个这样的假设,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近现代不跟西方这样的碰撞的话,那么中国肯定会按照它以前的那种模式发展下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伦理道德等等等等的观念肯定不会象现在这样,我不知道这段话是梁漱溟哪本书上的话我忘了,我的意思就是您能评价一下梁先生这个假设吗?
陈 来:这个呢,梁先生讲的就是说,在世界上有三大的文化的系统,就是中国、印度和欧洲,那么这三个系统的文化呢,它的路向是不同的,他说,西方人的路向它是一直往前走,就是拼命地往前奔,是这么一种心态,见到挡着它的,想办法克服,把它战胜,是这么一种东西。中国人呢,是一个调和持中的这么一种路向,注重把人际关系搞好,不是拼命奔钱,我挣钱,我认为一万不够,十万、一百万、一千万,不是那个心态,他就是关系搞好,注重人际关系,它叫做调和持中的这种路向。第三种是印度人,他认为印度人他不向前看,他也不是调和持中,他向后看,就是他看来生,那种人对现实比较悲观,因为他是注重来生。所以他体现在实践上来讲,他认为是比较消极,他是这种看法。但是,梁先生呢,他认为这三个民族本来都是各走各的,本来是互相碰不到的,但是因为历史的发展,它有个规律,就是什么呢?就是人类呀,一定要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才能解决第二个问题,解决第二个问题才能解决第三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西方的这个,它是一个面对自然的问题,它是个面对自然,我要战胜自然,不断地克服,要发展,这个硬道理在这儿,他说这是人类的第一个课题,假如你这第一个课题没解决,你一直在走第二个路,或者第三个路,这个走不通,最后还得回来再这样走。所以中国和印度本来这样走,结果一看西方这条路走得很顺,他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受到它的影响,中国人印度人还要回来这样走。但是他说,……所以梁先生说,我们现在都要学西方,走他的第一条道路,所以梁先生不是保守的,他是要学西方的,全盘承受,把全盘都承受它,加以改造。学这个东西,把这个第一条路走顺。可是走顺了,不是说这个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一切都好,走到一定程度,他就认为,就该走我们的第二条路了,我们的中国文化,注重人际关系,社会的平等,调和,就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了,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第二条路,这也就是中国文化里面原来的理想,就是注重人的平等、仁爱这些东西,就要走这条路了。走到这条路以后,当然他讲,将来呢,因为西方注重自然,中国注重社会,将来再物质极大丰富,可能也许到共产主义吧,走印度人那条路了,那就是注重精神,一些精神的思考,印度的道理,他也是肯定的,只是他安排不同的历史时段来发展。这是梁先生的意思。
主持人:您提出来要把哲学现代化和民族化,那哲学一定是一个在您心中非常高尚的东西,现在呢,我想让您用一句话告诉我,而且非常感性的话告诉我,哲学是一样什么样的事物?
陈 来:哲学就是使你这个人能够增长智慧的一种东西。
主持人:哲学是使只有我这样的人……哲学是一种能使我增长智慧的东西。好,追求进步,学术倾听,世纪大讲堂向您道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谢谢陈教授,谢谢现场观众。
陈 来:你好,阿忆。
主持人:请坐。我听人说,如果是您跟一个哲学以外的老师说话的话,这个老师都会笑。但是如果您跟哲学老师说话呢,哲学老师只能是眼睛里发出深邃的光,一般是不会笑的。
陈 来:北大校庆的时候,有个记者也叫阿什么,阿旭大概是。
主持人:跟我的姓是一样的。
陈 来:给我照一张相,不许我笑,要我表现出一个深邃的、冷峻的目光。
主持人:是不是我们在网上轻易搜索,就可以看到您穿着风衣,在燕南园里(的照片)。
陈 来:没错,就是那张。
主持人:而且不管是在哪个网站去搜索,搜索您的第一条信息,就是这张照片。
陈 来:其实那根本不是我的性格。
主持人:您的性格是老笑。
陈 来:我的性格其实很随和,而且不能说喜欢笑吧,但是也不排斥笑。
主持人:让我们了解您一下,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哲学的想法的?
陈 来:我哲学意识应该是1969年。
主持人:1969年,您是?
陈 来:1969年那个时候,我是上山下乡,那时候我到内蒙古西部。
主持人:您在那么苦的地方,大家都是想弄个萝卜吃一吃就很好了,您在想哲学问题?
陈 来:那个时候虽然谈不上温饱吧,但是大家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并不是很高。而那个时候呢,社会环境啊,给大家造成一个力量,就是促使大家去学习这些东西,特别是哲学。当然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也好啊,毛泽东思想也好啊,那个时候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那个时候开始有哲学的这些想法。
主持人:据我所知您的本科是工学士。
陈 来:没错。
主持人:怎么没有当时就报哲学呢?
陈 来:因为我上大学那个时候,是不能自己选择志愿的,因为我是从农村出来,那个时候上面给你分配哪一个地方去上学,那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
主持人:那读这四年地质的时候您是不是非常痛苦?因为您也不喜欢它,是党给您派去的。
陈 来:那倒也不是,因为我对知识本身是有兴趣,虽然那不是我自己最心仪的专业,但是很多的知识对我来讲是新的,好多知识呢,也都是我自己自学的,所以大部分可以说百分之八九十的课程,我都是在这门课程的前一个学期甚至前两个学期就自己自学完了。所以很少有的课程是我被动的听老师学的,都是自己主动的把它学习来的。
主持人:那您当时地质学得好吗?
陈 来:因为我们那个专业一方面是地质类的课程,另一方面很多机械类的课程。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我觉得掌握起来不是那么难,我也有一定的兴趣。但是同时呢,我在当时那个时代,那时候叫又红又专嘛,就是你除了这些课,学的专业知识以外,还要寻求一些人生理想,所以我在当时的工科院校也念了很多很多的哲学的书,当然也包括历史,经济这方面的书。
主持人: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学哲学了?
陈 来:真正呢,当然是到1978年开始。
主持人:1978年您又考上了研究生了。
陈 来:研究生。这是1978年开始恢复中国的研究生制度,第一年我就考入北大。
主持人:谁是您的导师呢?
陈 来:我的导师是张岱年先生。
主持人:那很幸运。研究生完了以后又接着读博士了?
陈 来:没有,研究生念完了以后,到1981年我就开始在北大教书了,因为那个时候北大没有开始文科的博士的招生制度,所以到我教书的一年多以后,才又开始,这个时候我才转变为博士生的身份。
主持人:导师是谁呢?
陈 来:张岱年先生。
主持人:还是他,真是幸运。听到陈来老师这么幸运,我们也就能猜到,在一个大师的领导下,指导下,他能够把学问做得非常好,下面咱们就听听他这个好的学问是怎么化做了他今天的讲演,他的讲演题目叫《哲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好,有请。
陈 来:大家好,其实这个题目呢,《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我今天主要谈的还是民族化的方面,里面又牵扯到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就是说从整个文化来讲,不仅是哲学,应该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课题。
我们看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不断奋起、奋争,寻求现代化的一部历史。因此呢,可以说追求现代化,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的共识,我想这一点呢,大家都可以切身体会到。但另一方面,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也可以看作具有五千年历史和渊源的中国文化,它在受到冲击,处于失落,这样一个逆境里面,不断地寻求奋起,寻求新的自我肯定的这样一段历史。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在文化上面,除了现代化的意识出现以外,中国化和民族化的意识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在哲学上来看,一方面我们看到现代化的这个观念,它或隐或显的,影响到许多哲学家,他们关于哲学的那个理解,成为他们建构自己哲学的重要的动力。
那么另一方面呢,怎么使这个哲学的工作能够呈现出民族化的特点,也是很多的哲学工作者,他们内心没有间断的一个内在的冲动,而且随着这个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体现为各种不同的诉求和实践。这个现象呢,是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因为新的世纪到来,我们可以展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的前景是越来越灿烂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从前不太被注意的,关于这个文化的民族化的问题,我想现在提到日程上来了。 今天因为这个课题很大,我们只能就一个小的方面,提出一些浅显的例子,特别集中在我们北大的已故的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他的一些思考上面,来跟大家做讨论。第一个,我想回顾一个现象,这是一个具体的讨论吧,就是我们知道,二十世纪现代化这是个主流,民族化的问题呢,考虑得比较少。在三十年代的时候,有两个著名的哲学家,一个就是冯友兰先生,一个是金岳霖先生,这两位先生呢,就注意到有一个现象,他们就做这样一个讨论,就是说呢,比如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可是我们不会说,化学的民族化,电子学的民族化,我们不会提这类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子?那么在那个时代,三十年代的时候,冯先生和金先生呢,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语言里面,经常会说,英国哲学,英国文学,德国文学,德国哲学,可是我们比较少说英国化学,德国化学,这个我们比较少,这个语言现象怎么解释?那么他就做了一个叫“的”和“底”的分别,底就是瓶子底的那个底,汉语发言,在口语上都叫“de”,但是在文字上面有这个分别。他说,当我们说英国文学、德国文学,这个时候呢,我们讲的是英国底哲学,德国底哲学,或者英国底文学,德国底文学,这个“底”呢是一个形容词的意思,表示这个学术形态呢,它有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一个特性。那么当我们说英国化学或者德国化学的时候,不是指英国底化学,我们只是说英国的化学,德国的化学,这是什么意思呢?“的”在这个里面是一个所属的关系,表示我在这个地方发生,是在这个地方出现,并不表示说,它跟英国的语言,跟德国的语言,英国和德国的文化传统有什么特别密切的内在的关系。那么这里面呢,从这儿讨论,他们就发现“的”和“底”的用法,可以演变出一套宏观的理论,就是我们在人文科学里面呢,有很多很多都可以用到“底”的,特别是文学,因为文学是要用特定的民族的语言,那么哪种语言里面有它自己这种民族语言的一种特别的技巧,那么这种特殊的民族语言它会形成特殊的一些文学的趣味和文学的技巧,当然包括审美的特点。因此呢,它所体现出来的这些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里充满了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文学呢,一定是“底”,它是充满了这个文化,这个民族的传统的这些特色。科学,科学一般来讲,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科学,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写作,当然会用不同的民族语言来写,但是他所追求的是一些公共的、普遍的这些真理,这些原理,那么这些普遍的原理,虽然可能借助于某种特别的文字表达出来,但是这个文字和这个原理之间,照它来讲,没有那种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呢,他就指出来,说哲学到底是属于什么形态呢?他就发现,哲学处于文学和科学之间,兼有它们两种特点,一方面哲学也是追求这种公共的,普遍的这种原理,可是另一方面呢?哲学跟它这个民族的传统,跟它的语言也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从这个“的”和“底”的分别呢,他就发现,哲学也是可以有民族性的。 那么冯先生呢,他就以金岳霖先生为特点,他说金先生有两本书,一本书叫《论道》,说《论道》这个书啊,它是“中国哲学”,而不是“哲学在中国”。他说金先生还有一本书,叫《知识论》,他说这个《知识论》不算“中国哲学”,是属于“哲学在中国”。那这里面又有一个新的名词出现,就是“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或者说中国的哲学和哲学在中国。这个所要表达的分别,跟三十年代表达的“的”和“底”是一样的。那么三十年代他们用的,象冯友兰先生用的那个“的”和“底”的用法,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用,也有些人“的”和“底”是反过来用的,但是以后呢,现代汉语慢慢变化了,不管哪一种用法,他们的那种区分已经意义不大了。所以他又用新的语言来作区分,就是用中国哲学或者中国的哲学,表示有中国性的,表示有中国性的哲学,那么另外一种,叫做哲学在中国,照他来看,就是有两种,我们做哲学工作有两种,就是我们中国人做哲学工作有两种,一种我们做的叫做哲学在中国,那么这里面呢,不是刻意地去凸显,去表现,或者去继承,或者去发扬,那么跟中国哲学、古代哲学的资源有密切关系的,这个方向。那么另一方面是中国哲学,或者叫中国的哲学,那么这个方向呢,它是继承、发展,当然也有改造,跟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有密切关联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是他到晚年提出的,就变成“的”和“在”了,不是“底”和“的”,而是“的”和“在”,中国哲学,中国的哲学和哲学在中国,做这样的分别。那么这里表达的同样是,所谓哲学,中国哲学或者中国的哲学,这里面所凸显的中国性,其实就是个民族化的问题,这个民族化就是跟中国文化的传统,跟中国哲学的,古代的传统有密切联系的这样一个方向。那,我刚才讲,我们要以冯友兰先生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看,前面都涉及到他,那么他自己的观念是什么呢?我们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册,我们就看到,他说,中国需要现代化,哲学也需要现代化,这是第一句话。第二,他指出来,他说,他自己所谋求的,所致力的是作一个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就是他要作的这个哲学,一方面是一个近代化的哲学,一方面呢,又是一个中国性的哲学。那么要做这样一个哲学,他指出来,做这样一个哲学,不是凭空,我们没有任何基础,一下子就可以做出来,就是一定要跟传统有一个接续的关系,你这个中国性才能表现出来。那么另外呢,你如果仅仅是跟传统接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那不是近代化。所谓近代化呢,一定要引进西方的和世界其它的这些文化哲学资源,来重新了解、分析和构造我们的中国哲学。那么这是冯先生他自己一个追求。那么这个目标,这样一种工作的方式呢,他有时候用另外两句话来区分,来表达,他习惯上,是什么话呢?就是“照着讲”和“接着讲”,他喜欢用“照着讲”和“接着讲”这个话来区分,照他来看,照着讲,是保持中国性的一种方式,比如,古人怎么讲,我们也照着这个讲,那么这当然是一个中国性的表现。那么可是这个照着讲呢,它不是一个近代化的东西,那么只是重复古人,再现古人的讲法,这个不是冯先生的工作目标,所以他讲,我的工作目标是要采取接着讲的方式,那么什么是接着讲呢?接着讲就是一定要接引西方的这些的文化资源,对中国的传统的资源进行分析、重建,这样一条工作。所以照着讲和接着讲这个分别,我们习惯上呢,是把它作为说,照着讲就是不发展,接着讲就是发展,这个解释呢,是单一了一些,就冯先生的意思不止于此,就是冯先生不只是强调说哲学不能够故步自封,还是要发展,有照着讲和接着讲这个不同,那么冯先生讲的照着讲和接着讲,里面包含着近代化和民族化的统一这个问题,以前这个大家没有很好的注意。他说,只有用西方的哲学的方法,来分析和研究中国这个哲学资源,这个才是接着讲,所以冯先生他讲的接着讲,他不仅仅是说要发展,而且包含一个学术转型,不仅要转型,又在这个转型里面,要保持中国性,发展这个中国特色,中国性。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冯先生的一些努力吧。 那么哲学的这个民族性呢,怎么体现,或者有什么地位?他认为呢,可以说,用两个方面来讲,来表达,一个叫做“就哲学来说”,一个叫“就民族来说”。就哲学来说,他说呢,就哲学来讲,就是把哲学作为一个普遍的学科,普遍的一个类型的学问来说,那么各个民族的民族性的特色,在这里面是一个外在的形式的因素。可是呢,如果我们要就民族来说,那就不同了,比如说,我们就看爱因斯坦这个个人,那他长的什么什么样子,他的性格如何,甚至他的口音,他的各种爱好,都是这一个人区别其他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特点。所以哲学也是一样,哲学的民族性也是一样,照冯先生讲,如果就民族来说,一个国家的民族的哲学,它能够提供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人民,给他一些非常重要的,而别的东西,别的民族的东西所不能给予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满足,和精神上的愉快。他甚至提出来,包括能够促进这个民族的精神上的团结。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哲学的这种民族性,就不是可有可无,外在的东西了,就变成这个民族生存,它的精神生活,在精神上存在的重要的条件,变成相干的,内在的因素。那么这个民族性,就形式上的体现两个方面,一个呢,它的讨论是接着这个民族的哲学史来讲的,这是它体现它民族性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它的民族性体现在,它用它自己这个民族所熟悉的,跟它的这个文化传统密切关联的语言来讲述的,那么如果你,讲哲学,你是接着西方哲学来讲,不是接着中国自己哲学问题来讲的。那么这个呢,就不能体现这个哲学的民族性。那么这种接着讲,不是冯先生所讲的那种接着讲,所以冯先生所讲的这种哲学的民族性的接着讲,他是讲,你要接着中国这个文化的传统,中国哲学里面传统的这些问题来讲,那么这个叫做中国性的这种哲学。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问了,就是说冯先生这些思想呢,有的刚才我提到表达,特别是说,他说这个哲学的民族性的表现,能够促进这个民族精神上的团结,给这个民族以它自己别人所不能给予的一种满足,这个话当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讲的。今天呢,时代是不同了,我们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那么全球化的时代,这个民族性的问题,传统性的问题,现代性的问题,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怎么样来看?那么这就涉及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前面所提到的这些问题的互相的连接。那么我想这里面仍然可以提到冯先生在谈到民族哲学的时候,它的一个别的区别,“程度的不同”和“花样的不同”。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另外也处在一个多元文化盛行的一个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怎么看这 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另外也处在一个多元文化盛行的一个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怎么看这个问题,冯先生当时呢,应该说他有一些先见之明,或者他接触过这样的课题,他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广义地看文化,文化的这种冲突、变化,这种情况来讲,他说文化的这种差异,和对待差异,有两种基本的方式和不同,一种呢,这个文化的不同呢,是属于程度的不同,那么这种程度的不同呢,应该把程度低的改进为程度高的。比方说,牛车和汽车,牛车和汽车这个是程度的不同,那么牛车 呢,就应该改进为汽车,这是文化的程度上的差异,那么这里面,现代和全球化非常有意义,我想我们这一个世纪以来做的工作,都是很重要,要谋求这个东西。另外,他说,有些东西呢,文化之间的差异不是这种程度上的不同,是什么呢?是花样上的不同。你喜欢意大利歌剧,那我喜欢京剧。你喜欢吃这个烤猪排,我喜欢吃酸菜鱼,变成这样,变成一种文化的花样的不同,这种花样的不同呢,照冯友兰先生的看法,花样的不同,不是程度的不同,所以不存在哪一方面要改进在哪一方面,这是一个互相对话,互相理解,那么当然,也可以相互吸收,相互学习,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照冯先生的这个看法,我们对全球化也可以说有类似的看法,凡是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有关系,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有促进,能够使我们这些程度低的改进为程度高的东西,那我们要举双手欢迎全球化,促进全球化。但是如果全球化同时带来一种危险,会消解一切民族文化,把一些地方性的民族文化全部拉平,那么这样的倾向,我们在欢迎这个全球化的这个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有所警惕,我们也要注重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危险面前,怎么样能够注重来发掘和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和中国性,用我们自己的身份来讲,中国性这个问题。 刚才我讲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但是我的主题呢,因为时间的限制,和我个人研究的专业方向,我们是侧重在民族化这个方向。那么由于强调民族化呢,我们比较注重中国底哲学和那个中国哲学,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说哲学在中国,我们中国人做哲学,只能发展这种,不是这样。那么哲学在中国这个方向,我们同样也要大力发展,要继续发展。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在继续促进现代化、全球化的同时,我们觉得这一个方向应该受到大家较多的重视,我们要重新挖掘和总结二十世纪那些自觉地寻求哲学的中国性的重建,这些人,我们要总结他们的工作,看看他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有哪些思考,那么这些思考有没有什么道理。那么我们当然看到,在这一支发展中,是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象我们刚才提到的冯友兰先生,那么在冯友兰先生之外,也有其他的许多先生,比如说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以及所谓有些新儒家哲学的一些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呢,它跟冯先生的工作可能不太相同,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那几位先生,他们可能不是说仅仅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些资料和材料,而是注重中国哲学的那些精神的方向,那么以中国哲学内在的精神方向为依归,或者以中国哲学固有的那些观念和理念为主张,比照西方哲学的这些观念,把它加以阐发,把它加以表达。今天,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想继续推进这个方向的研究和发展,我们要总结他们的经验,要了解他们在这里面的一些苦心和成败,这有益于我们今后我们自己的哲学建设的工作。 最后我们可以总结讲几句话,就是当代哲学和文化的发展,显示出根源性、民族性、地方性,这些东西,和世界性、普遍性、现代性,这两组东西不是启蒙时代所理解的那种非此即彼的那种对立,而越来越被大家理解成为一种我们叫做对立的统一这样一种辩证的关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也就是说可以普遍化的。所以作为我们在参与迎接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一个成员,我们在一方面促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的同时,要深入的思考,考虑怎么样进一步的挖掘、再现和重建中国文化的中国性。这是我今天讲的一个基本的内容,谢谢大家。
主持人:好,先看一下来自凤凰网站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一个叫做“思想被我三姨所控制”的网友提的,他说,我真的认为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我的这个想法来源于我的三姨,有一天,我朋友结婚,我给他们买了一束鲜花,回家后,我姨问我,买花干啥,我说朋友结婚送礼。三姨回答,要是我,就不买那东西,我买两瓶水果罐头。我蓦然发现,这就是中国现实,她连鲜花都不喜欢,何况是哲学?您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两个哲学实用的好例子,说服我,我再去说服我三姨。
陈 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哲学有没有实用性。那哲学的实用性是要比较广义的看,比如说哲学包括很多的门类,哲学里面包括很多的门类,不是我们现在、以前所讲的,只是一个对世界普遍规律的一个了解,不是那么简单。比如哲学里面有一门学问叫做伦理学,伦理学是讨论怎么样做人的问题,这个是很实际,这就是很古老的学问,你到哪里,在我们中国社会里要碰到做人的问题,哲学,特别我们中国传统的哲学,是要跟你讨论怎么样做人,做人这个问题重要不重要。这就是一个很实用的。比如说,象新的问题,比如说现在有所谓的克隆人,这类的问题,克隆什么什么东西,那么引起很多叫做生命伦理,一些新的伦理学的问题,那么哲学有一支就是伦理学,伦理学就要讨论这些课题,研究这些问题,这个就是很实用的。那么再比如说,哲学有一个门类是美学,美学当然是在理论上讨论审美的,但是美学呢,也跟我们这个生活中的审美现象有很多很密切的关系。
观 众:陈教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以前一般的观点都认为,中国的哲学就是一种儒家的思想,但是现在有些人认为,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哲学占过统治地位,因为在象秦朝以前是百家争鸣,秦朝法家占统治地位,然后汉朝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一种改造,这时候它已经不是原来那种真正的儒家思想了,到唐宋时期,然后佛家,还有一些宗教思想开始占有一定的地位,然后到明清,中国正统的哲学思想已经不太明显,这种概念非常模糊了,您对这种观点是怎么看的?中国究竟有没有一个哲学真正占过统治地位?
陈 来: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它是有发展过程,我们的概念、我们的理解里面是要允许它发展的,不能说,儒家只能是孔子和孟子讲的那个,如果讲得比孔子、孟子多了就不是儒家了,比如说董仲舒,董仲舒他讲当然跟孔子、孟子那个时代有点不同,他吸收了一些阴阳家的讲法,吸收了一些别的东西,包括一些这个……当时甚至某些,当时的那些比较原始的自然科学的一种讲法,这种感应论,这种讲法。但是不等于说他就不是儒家。那么到宋代以后,就是所谓宋明理学,宋明理学里面也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很多佛教的一些理论思维,但是这不等于它就不是儒家,所以儒家本身它是有一个发展的。那么至于说,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哲学占主导地位,那么这个呢,当然是各个时代不一样,这不能有一以贯之的讲法,比如说在先秦,先秦是百家争鸣嘛,但是百家争鸣里面呢,虽然有比较主要的,比如百家争鸣里面,在早期是儒墨,儒家和墨家,儒墨为显学,这两家势力最大。你刚才讲了,到秦国的时候,法家呢,通过政治取得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时间比较短。那么到魏晋的时候,是新道家出现,玄学,玄学是新道家出现,到了隋唐,当然佛教的影响是比较大。但是如果我们看,从十世纪到十一世纪以后,这段历史,这个酝酿着新的变化里面,儒家思想可以说占了一个最重要的地位,虽然这个时代里面还是有佛教、有道教,有所谓儒释道三教,甚至还有三教合一的提法,到了明代的后期。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可以说儒家思想就占了比较主导的、中心的地位,特别是它的新的形式,所谓新儒学,就是理学,而且一直接续到我们的所谓前近代,就是跟我们现在这个近代最近的传统,我们现在最近的传统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应该实事求是,应该承认这个。
观 众:您刚才说冯友兰先生在三十年代的时候,他的主要工作是以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哲学为素材,引用西方近代哲学观点来审视来继承中国的传统哲学,那么为什么冯友兰先生不倒过来一下,就是以中国的传统哲学和思想为基础,来吸收和批判外国就是近代的那些哲学观点?就是说,冯友兰先生不选择后者,而选择前者,在三十年代这种历史背景下,有没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陈 来:我想,因为冯先生在三十年代他是一个比较注重现代化的,是比较注重现代化的一个观点。一方面是社会的现代化,一方面是哲学的现代化,他是比较注重这个的。所以呢,当时的知识分子,我想普遍象你讲的那样,非常关切,怎么样从西方引进很多先进的东西,一些好的东西,我们缺乏的东西,来帮助中国进一步地发展。所以我想,那个时代应该说,不就政治层面,帝国主义当然都是要批判的,就是你刚才提到,为什么冯先生不选择以中国的思想为基础来批判西方,是吧?我想当时呢,不仅是冯先生,一般来讲没有这个潮流,那么当然了,冯先生在这个时代,他注重现代化,所以他在经济上,在文化上,他都非常注重吸收西方的东西。那么但是因为他同时又是个中国哲学家,他就想把这两者结合,所以他采取的,比如说《新理学》这本书,他写一本书叫《新理学》,不是老的理学了,是新的理学,新的理学就是接着讲,照着讲就是老的理学了,什么叫新理学?新理学就是那些概念,还是中国的概念,但是那个讲法,和那个问题的组织方式,这个就变成一个西方了,这是他选择的一个路径,这个选择呢,当然是跟整个当时这个时代,大家怎么样思考东西文化的问题,考虑中华民族的现实处境那是联系在一起的,是跟这个背景有一定的关系的。
主持人:好,下面看两个来自凤凰网站的网友的提问。先看这一个。这个网友的名字叫“会跳迪斯科的现代大儒”,他说请问陈老师,哲学是否有一个真正的分支叫生活哲学?据说林语堂和周国平就是这样的哲学家,就是生活哲学家,他们写的书都是畅销书,好象现在的大学教授就是看不起那些能写畅销书的教授,我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复兴哲学,促进哲学现代化和民族化,您怎么看林语堂和周国平,会不会看不起他们?
陈 来:那不会了。我想他讲的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这些人的工作是有意义的,而且应该受到重视,我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另一方面,这个,他讲的另一方面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就是说,因为这个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不管是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学科,还是在现代教育制度里面的一个教学的领域,它确实没有生活哲学这一门。
主持人:根本就没有这一分支?
陈 来:它没有这个名称叫生活哲学这一门,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不等于不讨论生活问题,我刚才讲了,伦理学里面当然是讨论生活问题,象林语堂里面讨论的问题,象周国平所讨论的问题,有些是属于人生哲学,在伦理学里有一个表达叫人生哲学,是跟人生哲学有关系,但是他们的表达呢,可能是比较具体的,比较文化的,比如林语堂,那么这个呢,在广义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跟人生哲学有关系的一种表达。但是就哲学里面,我刚才说作学术研究领域本身来讲,人生哲学呢,它也有它理论上的一套做法,就是这个学科里面它有一套规矩,就是要做人生哲学怎么样做理论的表达,这些规矩当然不是不可以打破,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做人生哲学的人呢,就是看不起前面提到这两位先生的工作,据我了解,应该不是这样。只是说,他们不是选择这样的方式,是选择比较理论化的建构方式,而不是选择象林语堂和周国平,他们这种比较具体的、具项的,甚至文学性比较强的那种表达。所以就我个人来讲,我不会说看不起,我很佩服,我很佩服写畅销书的,因为我写不出畅销书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畅销书都是好书,这也是同样的道理。我想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主持人:这位网友呢通过您的这个回答,知道了您不会看不起这两位写所谓生活哲学的作家兼哲学家,但是他不知道,我觉得我应该替他追问一下,您会不会不仅是不讨厌他们,而且跟他们一样,也去写这样的书?
陈 来:我其实呢,向来是肯定做这种比较有点普及性的哲学工作的学者,所以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的主要的方向一定是理论、学术的研究这些方面,我自己,可以说我的职业,我的工作性质,当然也包括我个人的兴趣,是不大会向那个方向发展的。
主持人:行,我听明白了。
主持人:好,先看一下,下面一个网友的问题,这个网友叫“喜欢老梁”,他说梁漱溟和冯友兰都是中国哲学家,但两个人却截然不同,老梁因为直抒心意,而三缄其口,老冯批林批孔,晚节不保,直到他们行将就木,老梁也几乎没有原谅过老冯。据我所知,陈老师曾经是为冯友兰小传写过序,想必呢,有幸认识冯老前辈,不知道您怎样看这两位前辈?
陈 来:那当然,因为冯先生是我们的老师,跟我个人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也给他做过助手,一直到他去世。他讲的这段公案,我想不是……他的了解可能还不够细致,另外这个问题牵扯比较复杂,先说简单的吧,就是说他说梁先生始终没有原谅冯先生,这个讲法呢,我想是不对的。就是梁先生,他曾经跟一个人讲话,批评过冯先生在批林批孔的时候的一些著述、言论,当然冯先生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梁先生,就是讲这个过程,然后把这个冯先生写的自传类的书叫《三松堂自序》,现在在《三松堂全集》的第一卷,把它送给梁先生,那么梁先生后来就来联系,还是要跟冯先生见面。
观 众:刚才你说,就是上个世纪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激进主义的批判态度是主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割裂了我们与传统的关系,那么您现在也提倡哲学的民族化,那这种割裂给哲学的民族化带来哪些困难呢?
陈 来:对,我觉得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比如说,不管从哪一个思潮来看,象五四时代,比如说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比较大,那么后来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比较大,那么在有些时代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由于过分的排斥传统,所以大家的思考就不能向这个方面走,他不会考虑这个问题。比如说在批林批孔的时代,批林批孔的时代,虽然是表扬法家,批判儒家,但是没有人想怎么样建立一个民族化的哲学,哲学的民族性怎么体现。或者象文化革命前期,甚至五十年代后期,这方面大家都不太考虑,觉得这个,可能旧的中国哲学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完全没有什么用了,我们可能是有这样的一种影响,所以还是,应该说是有影响的。就是到了今天,我想大家可能还是这方面考虑得比较少,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现代化的过程有关系,就是当处在一个现代化受挫的时代,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的民族自信心不强,在这个时候比较少,当然有些人还能够顽强的表现、提倡,追求这些东西,但是大多数人就比较少考虑这个问题。但是随着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良好的这种前景的出现,现代化,我想现在大概没有人怀疑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的能力了,所以我想,刚才我讲以前大家少考虑这个方面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观 众:你谈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民族性里,谈二者之间能统一起来,但是我的担忧就是说,我认为二者之间很难统一起来,因为现代化它本身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但是我认为里面肯定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政治,还有一个是经济,还有一个是军事,也就是说,在这种非常现实的意义的影响下,在诉求中国哲学的民族性,有没有可能,也就是说在现实中有没有可能。因为现在老子和庄子对我们现在非常陌生,对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是美国的大片和麦当劳,这些对我们是非常熟悉的。
陈 来:你说的这个现象当然是存在的,但是我想,这可能是个过程,可能经过一段各个过程,现代化越来越平稳,这些大家看的大片也看烦了,慢慢会有一些内在的,一些精神性的一些东西的要求出现,它会重新亲近老子、庄子、孔子,这些书,所以我想,不必悲观,可能现在只是个过程,再过一段看,这个情况我相信会好转。我觉得,一个民族越现代化,那么它的文化的民族化的意识将来也会慢慢的越来越自觉,越来越强烈。另外,我觉得就是说,你讲政治、军事、经济这个力量的问题,因为中国力量弱嘛及所以大家都对自己的东西没兴趣,就对最强的,世界上最强的是美国,就对美国的东西有兴趣。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那么一般的民众可能会受这个影响,但是我觉得有识之士,他会……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纪到九十年代以来,我想我们是中国最强的一个时代。象如果五十年代、四十年代,乃至三十年代、二十年代,中国的处境显然比现在差,中国的国力,显然综合国力比现在差,可是仍然我们看到,我刚才举了很多的发展民族哲学的,发展中国性的这些哲学家,象我刚才提到的冯友兰先生,包括金岳霖先生的《论道》,冯友兰先生也认为是中国的哲学,那么象熊十力先生,象梁漱溟先生,还有一些其他的先生,还是有的。当然,哲学家总是少的,不管是做哪一种哲学,是这种中国性的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都是少的,在人口比例上还是少的,但是我不悲观,我是认为,还是,即使在现代,仍然是有这样的人,而且会越来越多。
观 众: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记得梁漱溟先生好象有一个这样的假设,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近现代不跟西方这样的碰撞的话,那么中国肯定会按照它以前的那种模式发展下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伦理道德等等等等的观念肯定不会象现在这样,我不知道这段话是梁漱溟哪本书上的话我忘了,我的意思就是您能评价一下梁先生这个假设吗?
陈 来:这个呢,梁先生讲的就是说,在世界上有三大的文化的系统,就是中国、印度和欧洲,那么这三个系统的文化呢,它的路向是不同的,他说,西方人的路向它是一直往前走,就是拼命地往前奔,是这么一种心态,见到挡着它的,想办法克服,把它战胜,是这么一种东西。中国人呢,是一个调和持中的这么一种路向,注重把人际关系搞好,不是拼命奔钱,我挣钱,我认为一万不够,十万、一百万、一千万,不是那个心态,他就是关系搞好,注重人际关系,它叫做调和持中的这种路向。第三种是印度人,他认为印度人他不向前看,他也不是调和持中,他向后看,就是他看来生,那种人对现实比较悲观,因为他是注重来生。所以他体现在实践上来讲,他认为是比较消极,他是这种看法。但是,梁先生呢,他认为这三个民族本来都是各走各的,本来是互相碰不到的,但是因为历史的发展,它有个规律,就是什么呢?就是人类呀,一定要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才能解决第二个问题,解决第二个问题才能解决第三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西方的这个,它是一个面对自然的问题,它是个面对自然,我要战胜自然,不断地克服,要发展,这个硬道理在这儿,他说这是人类的第一个课题,假如你这第一个课题没解决,你一直在走第二个路,或者第三个路,这个走不通,最后还得回来再这样走。所以中国和印度本来这样走,结果一看西方这条路走得很顺,他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受到它的影响,中国人印度人还要回来这样走。但是他说,……所以梁先生说,我们现在都要学西方,走他的第一条道路,所以梁先生不是保守的,他是要学西方的,全盘承受,把全盘都承受它,加以改造。学这个东西,把这个第一条路走顺。可是走顺了,不是说这个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一切都好,走到一定程度,他就认为,就该走我们的第二条路了,我们的中国文化,注重人际关系,社会的平等,调和,就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了,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第二条路,这也就是中国文化里面原来的理想,就是注重人的平等、仁爱这些东西,就要走这条路了。走到这条路以后,当然他讲,将来呢,因为西方注重自然,中国注重社会,将来再物质极大丰富,可能也许到共产主义吧,走印度人那条路了,那就是注重精神,一些精神的思考,印度的道理,他也是肯定的,只是他安排不同的历史时段来发展。这是梁先生的意思。
主持人:您提出来要把哲学现代化和民族化,那哲学一定是一个在您心中非常高尚的东西,现在呢,我想让您用一句话告诉我,而且非常感性的话告诉我,哲学是一样什么样的事物?
陈 来:哲学就是使你这个人能够增长智慧的一种东西。
主持人:哲学是使只有我这样的人……哲学是一种能使我增长智慧的东西。好,追求进步,学术倾听,世纪大讲堂向您道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谢谢陈教授,谢谢现场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