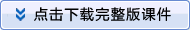从打结谈起王诗宬主持人:追求进步,学术倾听,世纪大讲堂问候您。
在上个世纪的100年里,中国人跟数学比较亲近的是70年代末,那时候有一位大数学家,他教给我们哥德巴赫猜想,但同时他也暗示我们,做数学家呢,一定要耐得住寂寞,而且数学是一件抽象、乏味的劳动,但是不是这样呢?北大数学所的副所长王诗宬教授呢,一定反对这个说法。好,有请王教授,请坐。
我刚才说到,70年代末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陈景润,您可能比较早知道,陈景润出来以后呢,造成了很多人选择学业和职业的一个分水岭,这之前呢,肯定好多人是想当诗人的,因为70年代之前,那时候当诗人谈恋爱比较容易,比较吸引女青年,但是,过了1977年以后呢,好多人想当数学家了,而且那些想当数学家的人物当中还包括我。您当时是1978年考上北大的研究生?
王诗宬:对。
主持人:会不会也是受了陈景润先生的影响?
王诗宬:其实我好像不是,我当时知青插队的,喜欢的东西还是很多,比较典型的比如喜欢物理、喜欢数学、还有喜欢中国文学史,当时也看一些哲学的书。然后,我想是非常偶然的,我1977年到北京来玩儿,当时就坐车,332路坐到这儿了,去颐和园,然后看见北京大学四个字,我就随手跳下车,跳下车以后,当时我脑子里正在想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就是六个人在一起,假如没有三个人两两认识的话,一定有三个人两两不认识,我就因为当时就想着这件事情,然后就碰到一个老师问他,他说你去问姜伯驹,姜伯驹(的办公室)现在就在我办公室对面。
主持人:您当时就知道姜伯驹先生是一位数学家吗?
王诗宬:我知道他,那时候我知道他。因为当时刚好那个时候《光明日报》登过他一次,而且他1962年的时候写过一本小册子,非常通俗的《邮递员一笔画》,就是邮递员送信的路线,那时候我看过这个小册子。
主持人:这么说您还是很早就有选择数学作为您终生学业的这么一个情况?
王诗宬:没有,那个时候真的完全没有这样的目的。
主持人:如果是一般人坐车到了北大西门的话,一定不会想什么六个人、什么两两、什么三个人不认识。
王诗宬:这个不是个专业,是个兴趣,只是你很喜欢,有时候我脑子里经常…,昨天我看黑板上写几句诗,那我真的不一定要以诗人为职业,但是的确我碰到他以后,那个时候我还是个知青,他说为什么不来,那你来试试学数学吧。
主持人:实际您不是受陈景润先生的影响,是在北大西门外碰到一位现在也不知道是谁的教授,受他影响?
王诗宬:我想是一定程度上的,跟我原来有所准备也有关,真的。那个时候你一个知青嘛,得到一个北京大学老师的鼓励,觉得那就来吧,就试了一试,后来第二年就来了。
主持人:是这样。来大讲堂做主讲人的这些重要嘉宾,他们都是西装革履,像我现在这样,而您是第一位穿着T恤衫来的人。
王诗宬:因为是这样的,我真的就是说…,从前我插队的时候就是剪这个头,衣服也是这样的,料子没有这个好,现在的就是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是这样的,这么说吧,你既然问我,我从来没有有过西装,尽管比如说我在美国呆过七年,但我没有穿过西装,不过我觉得穿西装也挺好,不穿也挺好的。
主持人:我为了向您靠拢。
王诗宬:我从前就没有,我觉得西装挺好,真的还是很简洁。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希望大家觉得我这样也很好。
主持人: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您的资料,就意外的得到了这么短的一段话,这段话一共只有三行半,但是我几乎是三行不知道什么意思,他说“您的研究方向是低维拓扑,在三维拓扑学做出多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他关于纽结上循环手术的工作”,您看还通医学好像是,“关于图流形的复叠不变量理论、关于不可压缩的浸入曲面不见得能提升成嵌入曲面的发现都很有影响”,全不懂,“特别是在三维流形间的映射这个研究领域,他是国际上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受欧美同行推崇”。但是在我看来这个拓扑学就很陌生,我一看这两个字,我觉得这两个字看起来像是说中国的碑帖,如果听起来象是日本的相扑。
王诗宬:的确这样,当时早期翻译的时候的确跟碑帖有关系,就是拉拉扯扯把它弄平了,真的。
主持人:这个拓扑是什么意思?
王诗宬:那我只能最简单的告诉你,还是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拓扑学关心什么东西,比如说你拿一只篮球来、拿一个足球来,通常人们会认为足球和篮球不一样,因为一个比较大、一个比较小,或者你拿一只篮球来,这个篮球已经打了气了,很圆圆的,或者没有打气,稍微有点扁,通常人也会认为它不一样,因为它形状有点不一样,但是对拓扑学家来说,认为它们是一样的,那么拓扑学家认为什么东西是不一样的呢?他认为篮球和自行车轮胎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这个我也看得出来。
王诗宬:你也看得出来,好的,那我就告诉你,但是在各种各样的不一样里面,这个是拓扑学家所关心的,拓扑学家他关心更深层次上的不一样,因为一个足球也好、一个篮球也好、一个打了气的和不打了气的,你比如在上面画一个简单的圆周,一个封闭的曲线,拿剪子将它剪开,剪开以后这个球总会分成两块,这个是它们共有的性质,篮球也好、足球也好,乒乓球也好。但是拿一个自行车轮胎,自行车轮胎大家天天看见,放在这儿,你这个上头可以画一个圆,你看这个样子画一下,一剪剪断了以后变成一根管子,它还是一个,篮球它永远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足球也永远不会,但自行车轮胎会。
主持人:这个我明白了。另外我还想问您,您不觉得您现在这样的打扮,不像个大数学家,而像一个某美术学院的油画系的老师吗?
王诗宬:无所谓,我其实不想这件事情,但你问起来的话,我也无所谓,我觉得谁认为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了,但是首先我算不上大数学家,即使如果有的人认为我是油画系的这种画家的话,我还是很高兴的。他说他认为我是体育老师,或者认为我是一个什么-----
主持人:是这样。另外,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教授不仅能研究数学,还喜欢爬山,您爬的最高的山是哪座山?
王诗宬:最高的山我是跟北京大学登山队一起爬的,以前那个登顶的是莫仕塌格,7540米。
主持人:7公里,摞起来以后那么高的山。好像您在爬卓奥友峰的时候,路过了拉萨大学,还给他们讲过一堂课,叫做“什么叫弯曲”,这个我听得懂,这个叫直、这个叫做弯曲?
王诗宬:从这个开始吧,从这个开始。
主持人:那咱们就马上就请王教授给我们带来一个精彩的学术报告,报告的名字叫“从打结谈起”,但是这个“打结”呢,不是打劫银行的打劫,是打绳结的意思。好,有请。
王诗宬:谢谢。
打结大概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现象。我们所有人都在打结,你每天系鞋带,就是说吧,打结这种现象已经存在几千年了。你看通常我们认为,像这个样子我们就说还没有打结,这个就像我上面画的这根线,这个样子没有打结。像这个样子呢,我因为这个太短了,我弄不起来,像这个样子呢,你看上去是已经打了一个结了,但这个结是假的,你稍微一抖它就出来了,换句话说,就是说哪怕你把这个两头固定住了不动,一抖就出来了。那么这个结你就发现它是一个真的,就是说你把两头固定住了的话,你永远不能把它变成这个样子。下面这个结也是真的,你把两头固定住了的话,永远不能变成这个样子,而且这两个也永远不能互变,经验告诉你。数学上为了把这个两头固定住的话去掉,就想个办法把它封闭起来,第一个封闭起来就变成一个通常的圆圈,这样的圆圈我们叫做没有打结,这个样子封闭起来就变成这个,这个其实看上去是很复杂,其实它也没有打,你把这个东西一拉拉出来,一抖就抖散了,那么这个东西你永远抖一千年,但是不要抖断了,它都抖不散,下面这个也抖不散,而且这两个不能互变。 打结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天天都碰到的。刚才我说过了,第一像上古结绳而系,其实不单是上古结绳而系,一直到大概非常最近吧,50年代的时候,他们这些做社会调查的人,我看那个报告,到一个少数民族叫多隆族,那个时候,他们50年代的时候居住在大山里面,一家人一家人离得很远,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然后要走很远的路程才能碰到一块,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的,没有电话,什么现代工具都没有。他们大概处在一种很原始的方式,比如一家的儿子要跟一家的女儿要结婚,那么通常这家人的家长和另外一家的家长,就走到一个大山的某一个地方碰了头,碰了头以后他们就要约定,回去要准备啊,准备但是多少天呢,他们的记数的能力很差,他们就是每个人都习惯的从腰里解一个带子下来,然后就在带子上打结。比如他们说,这是我说的,26天以后结婚,那么就在带子上打26个结,他们这个非常简单的,就是说他们不能数很大的数,但是他们知道一一对应,就是这边拿出一个来、那边拿出一个来,两个都一样多的结,然后各自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每天早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就把结松开一个,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再松开一个,两边都松,松到还有最后一个结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杀猪宰羊了。
现象中另外一种现象就是说,天上一个鸟,一个鸟窝,鸟在天上飞,飞、飞、飞…,再飞回去的时候,回到鸟窝里的时候,它在空中飞行的路线常常就是一个结,是一个真正的结,人是永远打不起结来的,人在地球上走,你出去走一圈,然后再回到家里面去,你想象你的脚上扣一根绳,这根绳在路上面永远不互相碰,无论你怎么走,走到最后回家的这根绳打起来的时候,它一抖就抖开了,这是永远不能打结的,所以鸟的本事比人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给你一根线,你穿来穿去、穿来穿去,然后把它一打打起来,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母亲在打毛线,拿两根针在那儿挑,最后到完了的时候,打一个疙瘩。所以原来你给她一根线,她扔给你的时候是一件毛衣,你穿在身上绝对抖不开的。 所以纽结这种东西尽管用了几千年,它从来没有成为科学的一个分支,大概真的很认真的成为科学的一个分支的时候是上上世纪末,上上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大概学物理的人都知道有个开尔文,开尔文就是以前从古希腊以来,人们都是觉得,他要研究现象,研究物质是什么东西构成的,就说物质是由某种颗粒构成的吧,它在一个层次上比如说是分子,如果分子解释不了,不能再进一步解释的时候,就说是由更细的东西构成的,那这个东西就叫原子,要是原子再不能解释,那我就再往下,所以叫分离法,从古希腊以来。当时所有英国的绅士都特别喜欢抽烟,一团一团的烟圈在空中环绕着,他当时看了以后,(突然)心生一亮,他说也许这个分离法的解释世界的方式是不对的,他说也许这个构成我们物质的基本的离子是个纽结,物质的不同性质呢,是因为它打结的方法不同而形成的,因为他当时非常有声望,所以于是有一些物理学家,尤其是英国物理学家,以泰特为首的,他们非常相信他的这种说法,于是他们就开始要找纽结表,他要把纽结列出来,如果你比如说物质是由原子构成的,那它就要列一个原素周期表,同样的,你说如果构成物质的基本东西是纽结的话,那你还要做一个纽结的表。 他们认为他们把所有自交数小于等于九的纽结全列出来了,但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说他们怎么能知道他们不遗漏?第二,他们怎么能知道,比如说这两个就不一样了。比如说这三个纽结,看起来很不一样,其实它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就是只要你在空间进行滑动,动来动去,完全不要拉扯断,可以把其中的这个互相互变,我们当然没有时间做这种事情,而且常常其实就是说,当时这个泰特他们花了20年的时间造了这个纽结表,造了这个纽结表,造完了以后,他们自己觉得从经验上说来,他们认为他们这个里面没有重合的、也没有遗漏的,但在数学上是没有证明的。 后来物理学家还是迅速的放弃了这个开尔文的学说,所以物理学家就把这个纽结忘掉了,不是忘掉了,就是不再研究这个东西。但对数学家来说,就突然有一个任务,第一次发现这张表在他们面前,数学家在某种意义上比较有雄心,或者比较没有事可做,他就说为什么这个表就是对的?然后他们就是研究,当时刚好在上(上)个世纪末,由于天体力学的原因,庞凯莱研究天体力学的时候,产生了拓扑学这个分支,然后拓扑学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拿来研究纽结,然后他们就真的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了从上世纪初,可以说一直到现在仍然在研究,当然把这个表弄清楚了,大概到60、70年代时候,慢慢就清楚了。
大概一直到本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由于很多意外的重要的发现,一下子把纽结推到数学的非常中心的地位。反正我不知道,大概你们知道一个诺贝尔奖,杨振宁得了诺贝尔奖了,数学里没有诺贝尔奖,但是数学里有一个奖叫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是还是相当出名的,大概最有名的奖之一吧。得菲尔兹奖的人里面应该说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跟拓扑学有关的,近年里面的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跟纽结有关的,主要说明它处于一个非常中心的地位。
但我今天并不想讲,它在数学里会是什么样、什么样子的,我就想说,自从物理学家想解释世界上的现象,造出了第一张纽结表,后来把它忘掉了,数学家就在那儿天天玩儿,玩儿了七八十年,在证明它相同与不相同的过程中发展了大量的数学工具,然后后来意想不到的,它在化学,结晶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中找到了一些应用。就是早期大家学中学化学的时候都看到,所有的分子式,分子式都是写在纸上的,从来不自交,就是自然的简单的分子都是写在纸上的,后来合成化学发现以后,人们就合成很多很多分子,这分子的话,真是打结的,真是在空间打结的,你看这个就是在1989年合成的,这个里面就出现一个事情叫“手性”。所谓的手性关心的是什么样的性质呢?你比如左手是右手的镜面像,它是它的镜子里的像。当然你不要很挑剔,比如我这个上头缺了一刀有个疤,这边没有疤,这是大概说的,它是它的镜面像。于是乎,它不但在拓扑上是一样的、几何上是一样的,但是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把这个左手移动到右手的位置,或者换句话说,我比较相信一个人伸给你一只手,尽管他这个两只手一个是一个镜子里的像,你马上就会认出来它是左手还是右手,好像早上穿鞋子,不会把左脚穿上右脚一样,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它互为镜面像,但是不能从其中一个变形为另外一个的东西,叫手性,手性非常不一样,同样的分子结构,手性不一样,往往可能体现出不同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来,尤其是在制药学的时候,特别是这个样子。这种例子最多,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氯霉素眼药水,氯霉素眼药水的分子它就是有手性,用具有正确手性的氯霉素眼药水点你眼睛的时候,你眼睛才能治好,用另外一种相反手性的眼药水(点你眼睛)的时候,你眼睛会变得更糟糕。于是就是说,判定分子有没有手性,就成为一个课题,大多数的时候,早期化学家很多时候是用经验的,因为早期是非常平面的,很多是用经验来判别。这个东西就没有手性,这是1840年就知道了,高斯,大家知道高斯,高斯这个学生就发现了这个现象。上面这个三叶结就有手性,他的镜面像是什么样子呢?你看你把这个东西交叉起来是这样的,这个在前,这个在后,那你往镜子里一照,前后刚好对调的。所以,画它的镜面像的时候,这个下行的,变成上行的,这就是它的镜面像,你回去试试,你永远不能把这个变成这个,你假如,有很大的耐心和时间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变成这个。这是1914年第一次被证明。
这是1982年发现在实验室里的,他们合成一种物质,首先合成一个线键,一个线状的东西,然后就是两根链,这些都是模型,原子,或者原子团,这中间是共价键,合成以后,它们又互相合成,合成一个梯子,然后他们最后就把这个两头呢,封闭起来,那封闭起来的时候,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上面跟上面的端点封闭起来了,下面跟下面的端点封闭起来了,另外一种是上面的端点和下面的端点交叉的封闭,形成一个梯子,叫莫比乌斯梯,他们当时就是不能判断,这个东西线度非常小,在高倍显微镜下不能判断,这个封起来以后,究竟是这样子得到的,还是这样子得到的。但是他们希望知道它的生成物是什么东西。这种梯子稍微动一下,可以平摊下来,摊成这个样的东西,可以完全化在平面里面,不自交的,但这个梯子是永远不能,你做不到这一点。完全放在平面里的东西,是没有手性的。理由非常简单,它完全放在平面里,放一个镜子在这儿,得到一个非常对称的像,你现在把镜子抽走,把这个东西平行地移动,就移动到自己了。所以完全放在平面里的东西是没有手性的。科学家用核磁共振的方法,最后得到的是生成物是有手性的,所以他推出来说这个生成物里一定有这样的东西,这是1982年的,他们就向数学家提出来说,能不能在数学上证明这个东西一定有手性,然后这个事情是在1986年的时候被证明的。
DNA大家就是看到这个梯子,这个梯子跟刚才那个梯子没有关系,你现在看到一个梯状的东西,就是双螺旋结构,酶在DNA上作用的时候,可以引起DNA重组,这个大概是现在分子生物学里头非常重要的课题,他们很关心就是说,酶的作用机理是什么东西,就是酶怎么样引起DNA重组?就是DNA有三个结构,第一个结构叫碱基顺序,这是最重要的,大家知道遗传信息就包含在里面;第二个就是双螺旋在螺旋,它在转,就是双螺旋结构,双螺旋结构基本上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呢?是由碱基顺序,以及就是说整个DNA在空间的位置,因为有时候互相之间有点引力,但大致是每过一个梯子转35度,大致是如此。第三个就是,现在很多尤其在小生物里,很多DNA,就是这个梯子是封闭的,可以是封闭的,它可以是像无限长的鱼线,但也可以是封闭的,如果是封闭的情况呢,那这个时候这个中心线,这个整个梯子,你把它像个纽结一样,所以碱基顺序叫第一种结构;双螺旋叫第二种结构;中心线叫第三种结构。
1971年的时候,生物学家,把同一种DNA,叫底物,同一种底物是不打结的,把它放到一个交泳,就是一个电,一种流质里面,让它带电,带电以后呢,然后给这个电泳池加一个电场,所有的东西就开始往前跑,就是不同位置上的频谱表示不同的速度,最后他们观察到一个现象,这个频谱是离散的,换句话说,就是它跑的速度是离散的,而且有的离散它比较小,就像我这个比较小的,有的呢比较大,那么他们当时就想知道这种现象反应了什么东西,怎么能从这种现象说明酶的作用机理。那现在还是拿我手中这根带子做一个样板,你看我手中是一根带子,它是有宽度的,它有两条边,我现在把这个边,看我这个带子,我现在转这个带子,我把它转、转、转,转了以后我把它封闭起来,封闭起来以后你会发现这是这样一个东西,这个时候,它这个缠绕现象其实可以打结,这是我手上的弄得比较简单,没有打结,就是弄一个封闭的,它这个缠绕的现象它有两种缠绕,一个就是当这个带子本身往下走的时候,它自然的,它会转,你发现没有,这个带子本身在转;第二,这两股带子,它也在缠绕,像油条一样、或者像辫子一样,那么,如果我把这第一种东西,比如我给它取一个名字,第一种这种转的现象叫“拧”,第二种现象因为它是两股,我把它叫做“缠”,那么我发现,我可以打开这个缠,我把这个缠可以打开,这样子我这个缠就被完全打开了,那么当我缠被完全打开的时候呢,拧就加大了,这个拧就很明显,对吧?我让这个缠加大,拧就变得平坦,这个是数学家发现的一件事情。
在说这个之前,我必须要说一个概念,就是叫环绕数。环绕数你看,这个最上边的小图上面有两个圆圈,像这种情况就是环绕数是1,我们叫做环绕数是1,你给一个定向以后,下面这个呢,这根线绕另外一根线绕了两圈,但是走向相反,箭头反掉了,是负2,像最里面一根,它虽然也是这两个圈永远抖不开的,但这个时候呢,就从环绕数来说呢,它一个是向上的、一个是向下的,所以是零,这是一个数学概念,叫环绕数,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守恒律,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守恒律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这个拧数我们没有定义,但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现象了,就是拧的个数和缠的数目加在一块刚好等于环绕数,等于什么环绕数呢?就是说我这个带子原来放在这儿,这是一根带子,它有两个边,两个边就是两个圆圈,它两个圆圈之间有个环绕数,所以它等于这个东西。所以环绕数它是一个整数,但是这个拧数和缠数呢,都是连续的,就是它不一定要取整数,所以环绕数是这样一个量,刚才这个公式是数学家发现的公式,1969年发现的,后来他们就拿这个公式去解释刚才那个现象。就是说我这个东西作用以后,作用以后它进行了重组,重组以后的话,你可以想象,它有的东西在这个里面,有的它蜷缩得很厉害,蜷缩得很厉害的时候,它这个在电场的作用下它受到的阻力很小,它跑得比较快,有的东西呢,它比较松散,比较松散它受到的阻力就比较大,所以它跑得就比较慢。就是这个对DNA而言,它这个转的速度是完全由碱基顺序所决定的,他们后来把这个生成物打捞上来,发现一下,发现碱基顺序并没有改变,碱基顺序跟以前一样,所以换句话说,拧速应该是跟以前一样,那唯一的引起这种有的紧、有的松的原因,他们就觉得是因为缠数改变了,因为刚才一个等式是拧数加缠数等于环绕数,那是因为环绕数改变了,环绕数改变了刚好就是说这个DNA的一股突然断开了,断开了以后就是这根,断开以后又重接一下,这个断开、重接刚好不改变碱基顺序。
但是呢,对于改变了环绕数的,环绕数改变1,换句话说呢,它就把这个整个拧数和缠数的和呢,做了一个离散的跳跃,所以因此使得它这个速度产生变化。还有一种频谱间隔特别大的是什么原因呢?他们分析就是因为它同时断开,同时断开又同时接上,这个时候环绕数的改变是2,所以这个之间的频谱就非常大了,当时也是一个很轰动的事情,第一次成功的用数学来解释了DNA的这种机理。
我结束这个演讲之前说几句话,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在说哲学还是说什么原理,就是说一个事实,就是从实践里发现问题,发现问题然后经过理论的探讨,最后呢,再回到实践中去,这个就是分子生物学家首先观察的这种现象,然后数学家用理论把它解释出来,这个对不对呢?再拿到实践中去,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这既验证了数学的这种有用,也验证了本身原来分子生物学家的假设是正确的。我们再到更宏观的看来,纽结论本身,它是由物理学的这种需要而产生的,而来因为它不对,至少不能解释物理现象,物理学家就把它忘掉了,它就纯粹的变成一个理论的东西,数学家很愉快,尽管没有任何应用,数学家很愉快的在不停的孜孜不倦的做,耗费自己的时光。然后在做了很多很多年以后,最后终于在生物学和化学中有了应用,从宏观上讲,这个也是一个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过程,不过这个过程不应该这么简单化,就是好象总是起源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实际上,我觉得,真理探索它是一个无限的循环的过程,所以叫实践理论,实践理论,我愿意画这么一个图,人们比较喜欢看到实践的东西,不喜欢看到理论的东西,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理论的东西象纽结一样的循环往复,出来一段,又是一个纽结,出来以后又是一个纽结。所以我最后打算结束这段话的时候,用我当年插队时候念过的毛泽东的一个话,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往复循环,以至无限,我的报告完了。
主持人:谢谢王教授,下面我们看一下来自凤凰网站网友的提问。首先有一位网友叫做“火狐狸”,他说“我觉得在数理化中,数学最没干头,可您还干得挺起劲儿,我认为要干数理化,就得得诺贝尔奖,但诺贝尔有物理奖,有化学奖,唯独没有数学奖,所以您干得再好,也比不上杨振宁和李远哲,所以,您干嘛不写点先锋戏剧,或搞点国际政治,弄个文学奖或和平奖享受享受?”
王诗宬:我想,首先我从前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知道,数学上没有诺贝尔奖,但是我还是做了,做了这么多年,所以可见的……当然,我先说一句,即使它有,我大概也不会得到,但是我做的时候就不在乎它有,做了这么多年了我也没在乎,我何必还要在乎它有没有诺贝尔奖呢?我感到很愉快,做了这件事情。
主持人:另外,我们还想知道,为什么诺贝尔这老头,不设一个诺贝尔数学奖?有人说是这位老先生跟他的女婿不和,而他的女婿是数学家。
王诗宬:我怀疑故事不是这样的,我能听到的故事不是这样的,首先这是一个故事,有个瑞典数学家非常有名,叫勒维他,前面讲的完全是故事,以前就是说他喜欢的一个女子,后来跟了这个数学家勒维他,他当时的个人的魅力不如勒维他。
主持人:比他女婿还要厉害。
王诗宬:不是这样的,这都是传说而已,并不是女婿,而且是非常随便的,很多人都被讨论过无数次了,大家一再说,这个只是社会上的想象,诺贝尔不见得这么小气。
主持人:那您想他是什么原因呢?
王诗宬:我想他当时他比较看重一个东西,能够直接对社会有……他认为的,至少他认为直接比较有社会效应,比如说他不光没有(数学奖),很多奖都没有,很多方面,比如说对天文也没有,对数学也没有,对考古也没有。
主持人:他可能把天文算到物理里面了吧?
王诗宬:有可能,对,有可能。但是我认为他当时就是像物理化学这种,还有医学这种一开始就有了,他认为这种东西,能够对人类的生活产生最直接的效应,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个应用化学家,制造炸药的。
主持人:下一位网友叫“我等你过了那条街”,他说“在您的讲话中,似乎把凯尔文勋爵说得位置很高,但我所知道的凯尔文好像没干过什么好事,他在1895年曾宣布,人们很快就会明白X光不过是个童话,1901年他又胡说,断言无线电这玩意儿不可能成功,我真不知道这家伙的眼力怎么这么差,还能当上英国科学领袖,这让我觉得权威不过尔尔,当然您和他们还是不一样的,您至少年轻的时候比他们长得漂亮。”他大概是想让您说说凯尔文勋爵,他怎么眼力这么差,然后,很多科学家经常还要提到他。
王诗宬:一个人做过很大贡献,人能力总是很有限的,做了一个很大贡献,他以后可以经常保持沉默,那么大家就会一直觉得他很(了不起),但是他有可能,有时候什么事都说,什么事都说,那你总会要说错好多事情的,时代在前进。
主持人:爱因斯坦也没说错这么多东西?
王诗宬:凯尔文当然不如爱因斯坦那是毫无疑问的,那时候爱因斯坦还没有出世呢,噢,不是,爱因斯坦还没有成名呢,1905年才成名的。
主持人:还是奥地利一个小职员。好,现场观众如果有哪位想跟王教授直接交流可以(举手)。
观 众:王老师,我想问您,您所研究的纽结理论和您打结什么的?
王诗宬:其实,我跟你这么说吧,我其实就是做理论的人常常说来可笑,虽然理论上我可以证明某一个结跟某一个结你永远不能变过去,但真打的时候,他们打得比我又好又利索,我年轻的时候,我插队的时候,那个时候挖水渠,我挖出来的一条水渠,边上总有一点犬牙,我反复在那儿练,始终练,有的老乡挖出来以后直得不得了,一点点都没有那个(犬牙),一锹一锹插下去捱着走,我觉得我始终就练不出那个功夫来,其实有的人有时候在某一方面虽然听起来做了一点事情,其他方面可能很差。
主持人:孔子登泰山的时候,后人描述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是孔子下了山以后呢,就告诉大家“学者要述而不做”,就是我们可以说,但是我们什么都不做,王教授这一点做得很好。
王诗宬:没有,我还是想做,我还是努力做,但是有的时候做不好。
主持人:嗯,下一位。
观 众:王老师您好,您刚才讲的纽结这个问题,从您的心底里面您认为物质世界到底是来自于纽结表,还是来自于经典的可分的理论?
王诗宬:我自己的感觉是,到现在为止,纽结论不能够成功的解释,就是基本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能够用纽结为基本元素来解释世界有很多成功的这种想法,所以整个现在的发展仍然是细分,就是从希腊来的细分法,大家去寻找微观粒子,我想是这样,但并不妨碍有些物理学家,世界上它是曾经从另外一个角度,他说他们现在比如像奥斯汀、伯克利有些人说,再细节我也不懂,就是所谓叫拓扑物理、几何物理,有这种想法的人仍然有,未来什么样的不知道,就是到现在为止,仍然用粒子解释这个、用微粒解释是非常成功的,解释了很多现象,我们的世界变得这么繁荣、变得这么物质化。
主持人:好,接下来再看两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叫“阿拉伯数字”,最近有一套数学丛书叫做《通俗数学名著译丛》,看完后发现一个无情的事实,那就是中国古代虽然取得不少数学成就,出现了一些大数学家,但这套译丛中,没有一部涉及中国古代数学,对此我深感痛心,并要问这是为什么?”
王诗宬:我想中国数学古代还是非常辉煌的,中国数学它总的来说,我不太知道这套丛书是什么样子的,我个人不太知道,我觉得中国古代数学,它更多的强调实用和计算,它在某些方面做得的确是比如像,有很多事情应该说,但是古希腊,打一个简单的比方说,比如说这个古希腊的毕达格拉斯定理,中国以前叫勾股定理,但是中国往往它是这样的,它是非常具体的知道,比如说三、四、五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但是它没有提炼成为像这种A的平方加B的平方等于C的平方,这个样子的一个公式。还有比如像圆周率也是一样的,应该说刘辉、祖冲之圆周率算得都非常辉煌,还有解方程,都曾经达到非常辉煌的地步,但这种辉煌的地步它主要是我自己的认识,首先我本人是…,我自己认为就是说,近代的思辩的科学,仍然希腊大概还是起了非常最主要的影响,它把它抽象化,抽象化以后,然后在里面开始进行进一步推理,对很多新的东西的发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假如不能写成A的平方加B的平方等于C的平方的话,那可能像无理数这种事情几乎不会发现,因为生活中不会出现无理数,光光去为了量东西,你要量得多准确、算得多准确,有理数足够了,而且无理数的确也没有用,在生活实践中没有用的,比如说你随便量东西或者是算东西、称东西、卖东西永远用不到无理数,那么就不会到无理数的发现。
还有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如果我们当然从前古代也知道很多很多几何现象,很多事实能够做很好的圆、很好的三角形、很好的正四边形,但是它没有一个所谓叫公理系统,然而欧几里得,他就说有公理系统,大家学过平面几何的都知道,我最前面设5条公理,这是最简单的,他想把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推出来,这个五条公理,它里面最著名的就是说其中叫第五公设,就是叫平行公理,就是我们非常简单的过一条直线外面的一点,最多只能做一条直线和它平行,这个早期的叙述非常麻烦,他们当时想呢,把这个东西从前四条推出来,这个事情可能在别人看来是非常无聊的,我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就把它当做公理嘛,但是数学家他愿意做这个事情,在昏天黑地中做了一千多年。最后终于有些人发现,这是个很长的故事了,发现它推不出来,这个第五条是独立的,换句话说你假定你假设过这一点以外,有更多的直线和这条直线平行,那所有的矛盾都不会出现,这个最后导致了双曲几何的发现,而现在我们经常在物理上说时空弯曲,假如没有这个样子的,最初的(思考)当然这个后来导致了很多深远,几何学上的很多深远的东西,我想相对论也很难说它有发展的基础,应该说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想是从希腊,源自希腊这套思辩的数学,就是说你看着中间没有用的,其实它起了很多的…,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更有主导的地位,应该说中国的数学在古代的计算方面的成就是非常辉煌的。
主持人:是实用的,不实用的东西我们也不研究。好,下一个问题呢,叫做“澳门上空的鹰”这位网友,他说“直到今天99%的数学仍掌握在像您这样的不到1%的人的头脑中,所以我们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数学究竟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我认为数学过分远离公众并不是一件好事,我想象数学在多年前还是一种乐趣,即使它为少数人所有,但这些少数人的动人故事却为大多数人所有。比如清华数学系主任熊庆来荡舟西湖,统一了数学概念的中文译法,他还买菊花取悦于他的太太,还在南方杂货铺里发现了华罗庚小店员,可现在数学故事怎么越来越少了呢?”这是他的感叹。
王诗宬:我想是,其实这种故事还是有很多的,不过就是大家现在这个…我估计跟整个社会更加多元化也有关系,大家感兴趣的事情更多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比如说你随便打开一个《南方周末》,拿一个什么东西,各种各样其他的很容易写出来的故事可能更多了。
主持人:《南方周末》上的故事张柏芝和谢霆峰比较多。
王诗宬:虽然我是不买花的,不过我觉得现在买花给太太的人也还是有的,就是说只是现在大家不报道了。但是你前面说的一个事情,他说的确无疑有他正确的一面。第一就是说,所谓叫数学,数学它应该停留在很多不同的层次上,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座的每个人都学过很多数学,这种数学什么样呢?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在今后的一生中,得益于数学,不在于得益于对某一个具体的(知识的掌握),他说这个定理我从来没有用过,而在于这种思维方式,他比较清楚的考虑一些问题,比如说学过一点概率、学过一点统计,他听到一些话的时候,他能够分析一下这个代表多少,反正我也是乱说了,就是的确就是还是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你说什么叫做数学?因为数学在各个不同的层次上,有些东西是相当前沿的,相当前沿的恐怕也只有少数人能来做,因为大家来做,因为这个东西毕竟跟你做牙医不一样,给人修了牙、做了牙就可以挣钱的,这个东西不挣钱,不挣钱的东西不需要太多太多的人做,社会,尤其现在的社会我想是这样子的。
主持人:好,谢谢您。
观 众:王老师您好,想请问一下您对中国结有没有研究,这种结与其他结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谢谢。
王诗宬:我真的是非常抱歉的,我最近看到了中国结,我还曾经说过什么时候要研究研究它,还没有来得及,就是从去年过年的时候。没有,这个结这么说吧,这个结它有个特点,它是艺术品,艺术品相当对称,具有高度对称性,你看的至少,很多纽结是没有对称性的,稍微奇怪一点,凡是作为艺术品的东西它非常强调对称,它是一个非常高度对称的结,我能说的就这么多。因为对称的东西可以做艺术品,而现在有很多更多的这种,在某种意义上纽结正在进入生活,你看现在很多这种-----包括中国,比如我估计好像在那个地方,中关村那边现在就有个大个三叶结雕塑,现在很多人做茶壶、做杯子的时候,做那个东西的把柄的时候也会做出一个纽结来,在这个意义上面,它成为艺术的一部分。
观 众:请问一下王教授,这个绳圈和这个莫比乌斯带,还有克莱茵瓶有什么关系?
王诗宬:绳圈是一维的,莫比乌斯带和克莱茵瓶是二维的,一维、二维你可以理解,像平面就是二维的,莫比乌斯带和克莱茵瓶都是所谓一种曲面,叫做不可定向曲面,就是说它这个莫比乌斯带,你既然说这个事情,我估计在座的人都知道这个莫比乌斯带,莫比乌斯带就是这样一个东西,还是很容易简单的,就是刚才你看到的,你现在如果把这个东西折成这个样子的话,那就是一个正常的带子,像我们的环圈一样,我这个纸太短了,要这个样子,折出来就是一个莫比乌斯带,又叫作莫比乌斯帽儿,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说,这个样子折出来的时候,你要想从这边到这边,你不经过边界,不经过这个边界你是永远爬不过去的,但这个不需要,这个东西你看,你只要耐心的顺着中心线走,走,最终就走到里面去了,它就是单层的;克莱茵瓶是更复杂了,克莱茵瓶你拿两个莫比乌斯带,把两个莫比乌斯带,当然这个莫比乌斯带你这个样子一粘以后呢,这个样子一粘以后,两个边变成一个边了,你拿两个莫比乌斯带把它沿边粘起来就得到克莱茵瓶,这个克莱茵瓶不能放在我们空间里,放不进去的,我们这个三维空间放不进克莱茵瓶,克莱茵瓶是最简单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这个东西不能放在我们的三维空间里,要把它嵌入到我们的一个空间就需要四维空间,这个已经到四维了。
观 众:它们可以推广吗?
王诗宬:可以推广,作为一个高维纽结,但是最有意义的还是这种纽结,因为我们现实生活的世界是三维的,可以推广,有高维纽结论。
提问:就是现在这方面有这些理论吗?
王诗宬:有,高维纽结论比低维纽结论简单。分类学来得更简单。
观 众:请您预计一下这个绳圈对物理学的发展?
王诗宬:我现在回答不出来,而且这个东西,我会一说一大堆,而且没头没尾的,这个就是圈,一方面就是数学物理的方法运用到绳圈上了,就叫杨米尔斯方程,就是说这种东西,跟这个打结有关。还是就是打结可以用辩群形成,辩群就是strand(一些股缠绕),太多的东西我不知道,而且我说出来一大堆,我估计这个事情我不能说,我回不来。
观 众:谢谢王教授。
王诗宬:其实我问别人问题的时候,比别人问我问题的时候要多得多,因为一个人的,他总是有大量的事情不懂得。
主持人:经常的情况下,您是提问题的人,而不是回答问题的人。
王诗宬:我想我提的问题比回答的问题更多,虽然我是教员。
主持人:心理学家说像您这样的人是还没有老,已经走向衰老的人总爱回答别人的问题,经常跟人说“孩子啊,我们那时候不是这么生活的”。
这位网友叫“天高云淡”,他的话写得很长,他说“杨振宁在回忆父亲杨武之给他的影响时说,父亲是大数学家,但他教给我的不是数学,而是数学精神,正是这种数学精神,使数学成了一种高级趣味,造就了一批好书,比如说《数论妙趣》”,不知道您听说过没听说过。
王诗宬:没有,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主持人:他说“比如说《数论妙趣》,它把高斯称之为“数学之皇后”的数论描写得生动有趣,读来真是一种享受,而《数:科学的语言》这本书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数学文化”;还有一本书叫《无穷之旅》,他把神秘的无穷大描述得淋漓尽致,而康桥数学家康威的《制胜之道》采集了几乎有史以来所有的数学游戏,我特别想知道,讲课如此有意思的王教授,您有什么类似的著作可以推荐给我们吗?让我们为之陶醉一把?”
王诗宬:我真的还没有,不过你在讲的事情我比较熟悉,刚才说的康桥的就是剑桥康威,康威现在在普林斯顿,他其实就研究的这种东西,当然他研究的东西非常多,他这个人非常聪明,就是比较罕见的这种聪明的人,就是数学家有两种,物理学家也是一样,有的人他做这种东西需要很深刻、很深刻的理论,之前你要学大量的东西,然后才能去做,康威他不一样了,他白手起家,什么东西他都不要的,属于那种,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对刚才说的这个纽结表就有好多改进,他现在在普林斯顿。我没有这个样,我真的没有,有时候也有人建议过我,我没有,我就是觉得随便说容易,真写下了很花时间,而且我也不见得写得好,假如有人愿意将来跟我一块写,还有比如说我不会电脑,不会电脑画图也很费事,就是将来有机会,我也不见得很好,可以写一点东西,以后。
主持人: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王教授是连这个光驱是怎么打开,它是干嘛的都不大清楚,是非常罕见的一个完全不懂计算机的数学家。
王诗宬:也不是,我可以往里面敲打一点东西,这个还是可以的。
主持人:别人帮您打开以后,您再那儿敲点东西还是可以的。
王诗宬:所以他们经常说的话,包括他们说,王老师您还不是小菜一碟,其实我是zero根本就完全不知道。
主持人:真的不明白,我看到王教授这样的,我就给他讲了,说《读者文摘》上曾经登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有一个老太太,她买了电脑以后,回家呢,还给电脑公司写了封信,表扬电脑公司,说他们想得非常周到,她一摁光驱出来以后,说连我放咖啡的地方都有,实际是放光盘的。 好,请这位。
观 众:我想问一下王教授,您能讲一下您爬山的经历吗?就是从什么时候爬山?或者是都什么时候…
王诗宬:我以前就喜欢旅行,真的开始爬山也并没有成功过,后来在1989年的时候爬过膝力马扎罗,是在向导的带领下的,第一次非常成功的爬山是1993年,跟北京大学登山队一块儿去的,学了很多东西,受到了很多训练,然后有时候我又爬过一些其他的山。我想既然你问这个问题了,我只想说一句话,当时我看那个电影,就是上个周末看那个电影叫《垂直极限》,大讲堂里放,开始的时候很兴奋,看了以后心里头很惆怅,就是说比较惆怅吧,就是说它其实一个抢险,抢险主要是一个人,一组人掉到冰裂缝里去了,等待抢救,完全是好莱坞的演员拍的,但是我心里很惆怅的就是说台上演得轰轰烈烈,下面牵肠挂肚、掌声雷动,其实从演员里面到听众里面,也许我是真正唯一掉进过冰缝,等人来救的,当时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主持人:当时是什么样子?
王诗宬:这个讲起来很长,但是所有的这种事情都非常简单,我因为只是一个人掉下去的。
主持人:别人还可以看到你是吧?
王诗宬:有一个人,但的确有些事情是真的,有些事情比如说我当时对那个人说,如果天已经很晚了的话,如果没有人过来的话,我让那个人回大本营,走的时候怕这个口上迷失掉,我们有个船,我说那你就把这个船埋在这儿做一个标记,它那个上头是把一个人的人躯弄上去做一个…
主持人:您这个时候想的都是生死问题吧?to be or not to be,已经不是那个什么六个人,如果三个人认识,一定那三个人…
王诗宬:完全不是、完全不是,非常简单,对,我想也许我就在这儿了,真是这个样子的,非常简单,所以这个事情也很好,所以使得我以后遇到什么人地生疏,一些愉快不愉快的事情,你要跟我说有什么好处,或者你想象我现在还很好,居然坐在这儿,向这么多人讲话,心里头很释然,不太计较小的事情。
观 众:我突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很多搞拓扑的数学家都非常喜欢爬山,伏瑞得曼和斯麦尔,他们也都很喜欢爬山,这个您能不能谈一谈,就是为什么会…
王诗宬:我唯一的解释是拓扑是研究形状的,山的形状太好了、太美丽了。我真的不知道,我知道伏瑞得曼喜欢爬山,他说的我想说一句话,他说的斯麦尔和伏瑞得曼都是得过菲尔兹奖讲的,分别一个是证明五维以上的庞凯莱猜测对、一个是四维的庞凯莱猜测对。伏瑞得曼我跟他一块儿跑过长跑,两个人。
主持人:是你跑赢了还是他跑赢了?
王诗宬:他比我先,但是他没有他的太太先,他太太差点就入选美国的奥林匹克运动队,她跑赢了。
主持人:在节目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呢,我还是一如既往的请您用一句话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您今天的讲题是从打结谈起,那您讲了这么多呢,您用一句话告诉我们,您最想告诉我们大家的是什么?
王诗宬:那我就是刚才那个上头已经说过了,就是“探索真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循环反复、一直无限”。
主持人:就是要告诉大家一句话“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
好,谢谢王教授、谢谢现场观众。
王诗宬:谢谢大家。
在上个世纪的100年里,中国人跟数学比较亲近的是70年代末,那时候有一位大数学家,他教给我们哥德巴赫猜想,但同时他也暗示我们,做数学家呢,一定要耐得住寂寞,而且数学是一件抽象、乏味的劳动,但是不是这样呢?北大数学所的副所长王诗宬教授呢,一定反对这个说法。好,有请王教授,请坐。
我刚才说到,70年代末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陈景润,您可能比较早知道,陈景润出来以后呢,造成了很多人选择学业和职业的一个分水岭,这之前呢,肯定好多人是想当诗人的,因为70年代之前,那时候当诗人谈恋爱比较容易,比较吸引女青年,但是,过了1977年以后呢,好多人想当数学家了,而且那些想当数学家的人物当中还包括我。您当时是1978年考上北大的研究生?
王诗宬:对。
主持人:会不会也是受了陈景润先生的影响?
王诗宬:其实我好像不是,我当时知青插队的,喜欢的东西还是很多,比较典型的比如喜欢物理、喜欢数学、还有喜欢中国文学史,当时也看一些哲学的书。然后,我想是非常偶然的,我1977年到北京来玩儿,当时就坐车,332路坐到这儿了,去颐和园,然后看见北京大学四个字,我就随手跳下车,跳下车以后,当时我脑子里正在想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就是六个人在一起,假如没有三个人两两认识的话,一定有三个人两两不认识,我就因为当时就想着这件事情,然后就碰到一个老师问他,他说你去问姜伯驹,姜伯驹(的办公室)现在就在我办公室对面。
主持人:您当时就知道姜伯驹先生是一位数学家吗?
王诗宬:我知道他,那时候我知道他。因为当时刚好那个时候《光明日报》登过他一次,而且他1962年的时候写过一本小册子,非常通俗的《邮递员一笔画》,就是邮递员送信的路线,那时候我看过这个小册子。
主持人:这么说您还是很早就有选择数学作为您终生学业的这么一个情况?
王诗宬:没有,那个时候真的完全没有这样的目的。
主持人:如果是一般人坐车到了北大西门的话,一定不会想什么六个人、什么两两、什么三个人不认识。
王诗宬:这个不是个专业,是个兴趣,只是你很喜欢,有时候我脑子里经常…,昨天我看黑板上写几句诗,那我真的不一定要以诗人为职业,但是的确我碰到他以后,那个时候我还是个知青,他说为什么不来,那你来试试学数学吧。
主持人:实际您不是受陈景润先生的影响,是在北大西门外碰到一位现在也不知道是谁的教授,受他影响?
王诗宬:我想是一定程度上的,跟我原来有所准备也有关,真的。那个时候你一个知青嘛,得到一个北京大学老师的鼓励,觉得那就来吧,就试了一试,后来第二年就来了。
主持人:是这样。来大讲堂做主讲人的这些重要嘉宾,他们都是西装革履,像我现在这样,而您是第一位穿着T恤衫来的人。
王诗宬:因为是这样的,我真的就是说…,从前我插队的时候就是剪这个头,衣服也是这样的,料子没有这个好,现在的就是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是这样的,这么说吧,你既然问我,我从来没有有过西装,尽管比如说我在美国呆过七年,但我没有穿过西装,不过我觉得穿西装也挺好,不穿也挺好的。
主持人:我为了向您靠拢。
王诗宬:我从前就没有,我觉得西装挺好,真的还是很简洁。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希望大家觉得我这样也很好。
主持人: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您的资料,就意外的得到了这么短的一段话,这段话一共只有三行半,但是我几乎是三行不知道什么意思,他说“您的研究方向是低维拓扑,在三维拓扑学做出多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他关于纽结上循环手术的工作”,您看还通医学好像是,“关于图流形的复叠不变量理论、关于不可压缩的浸入曲面不见得能提升成嵌入曲面的发现都很有影响”,全不懂,“特别是在三维流形间的映射这个研究领域,他是国际上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受欧美同行推崇”。但是在我看来这个拓扑学就很陌生,我一看这两个字,我觉得这两个字看起来像是说中国的碑帖,如果听起来象是日本的相扑。
王诗宬:的确这样,当时早期翻译的时候的确跟碑帖有关系,就是拉拉扯扯把它弄平了,真的。
主持人:这个拓扑是什么意思?
王诗宬:那我只能最简单的告诉你,还是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拓扑学关心什么东西,比如说你拿一只篮球来、拿一个足球来,通常人们会认为足球和篮球不一样,因为一个比较大、一个比较小,或者你拿一只篮球来,这个篮球已经打了气了,很圆圆的,或者没有打气,稍微有点扁,通常人也会认为它不一样,因为它形状有点不一样,但是对拓扑学家来说,认为它们是一样的,那么拓扑学家认为什么东西是不一样的呢?他认为篮球和自行车轮胎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这个我也看得出来。
王诗宬:你也看得出来,好的,那我就告诉你,但是在各种各样的不一样里面,这个是拓扑学家所关心的,拓扑学家他关心更深层次上的不一样,因为一个足球也好、一个篮球也好、一个打了气的和不打了气的,你比如在上面画一个简单的圆周,一个封闭的曲线,拿剪子将它剪开,剪开以后这个球总会分成两块,这个是它们共有的性质,篮球也好、足球也好,乒乓球也好。但是拿一个自行车轮胎,自行车轮胎大家天天看见,放在这儿,你这个上头可以画一个圆,你看这个样子画一下,一剪剪断了以后变成一根管子,它还是一个,篮球它永远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足球也永远不会,但自行车轮胎会。
主持人:这个我明白了。另外我还想问您,您不觉得您现在这样的打扮,不像个大数学家,而像一个某美术学院的油画系的老师吗?
王诗宬:无所谓,我其实不想这件事情,但你问起来的话,我也无所谓,我觉得谁认为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了,但是首先我算不上大数学家,即使如果有的人认为我是油画系的这种画家的话,我还是很高兴的。他说他认为我是体育老师,或者认为我是一个什么-----
主持人:是这样。另外,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教授不仅能研究数学,还喜欢爬山,您爬的最高的山是哪座山?
王诗宬:最高的山我是跟北京大学登山队一起爬的,以前那个登顶的是莫仕塌格,7540米。
主持人:7公里,摞起来以后那么高的山。好像您在爬卓奥友峰的时候,路过了拉萨大学,还给他们讲过一堂课,叫做“什么叫弯曲”,这个我听得懂,这个叫直、这个叫做弯曲?
王诗宬:从这个开始吧,从这个开始。
主持人:那咱们就马上就请王教授给我们带来一个精彩的学术报告,报告的名字叫“从打结谈起”,但是这个“打结”呢,不是打劫银行的打劫,是打绳结的意思。好,有请。
王诗宬:谢谢。
打结大概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现象。我们所有人都在打结,你每天系鞋带,就是说吧,打结这种现象已经存在几千年了。你看通常我们认为,像这个样子我们就说还没有打结,这个就像我上面画的这根线,这个样子没有打结。像这个样子呢,我因为这个太短了,我弄不起来,像这个样子呢,你看上去是已经打了一个结了,但这个结是假的,你稍微一抖它就出来了,换句话说,就是说哪怕你把这个两头固定住了不动,一抖就出来了。那么这个结你就发现它是一个真的,就是说你把两头固定住了的话,你永远不能把它变成这个样子。下面这个结也是真的,你把两头固定住了的话,永远不能变成这个样子,而且这两个也永远不能互变,经验告诉你。数学上为了把这个两头固定住的话去掉,就想个办法把它封闭起来,第一个封闭起来就变成一个通常的圆圈,这样的圆圈我们叫做没有打结,这个样子封闭起来就变成这个,这个其实看上去是很复杂,其实它也没有打,你把这个东西一拉拉出来,一抖就抖散了,那么这个东西你永远抖一千年,但是不要抖断了,它都抖不散,下面这个也抖不散,而且这两个不能互变。 打结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天天都碰到的。刚才我说过了,第一像上古结绳而系,其实不单是上古结绳而系,一直到大概非常最近吧,50年代的时候,他们这些做社会调查的人,我看那个报告,到一个少数民族叫多隆族,那个时候,他们50年代的时候居住在大山里面,一家人一家人离得很远,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然后要走很远的路程才能碰到一块,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的,没有电话,什么现代工具都没有。他们大概处在一种很原始的方式,比如一家的儿子要跟一家的女儿要结婚,那么通常这家人的家长和另外一家的家长,就走到一个大山的某一个地方碰了头,碰了头以后他们就要约定,回去要准备啊,准备但是多少天呢,他们的记数的能力很差,他们就是每个人都习惯的从腰里解一个带子下来,然后就在带子上打结。比如他们说,这是我说的,26天以后结婚,那么就在带子上打26个结,他们这个非常简单的,就是说他们不能数很大的数,但是他们知道一一对应,就是这边拿出一个来、那边拿出一个来,两个都一样多的结,然后各自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每天早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就把结松开一个,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再松开一个,两边都松,松到还有最后一个结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杀猪宰羊了。
现象中另外一种现象就是说,天上一个鸟,一个鸟窝,鸟在天上飞,飞、飞、飞…,再飞回去的时候,回到鸟窝里的时候,它在空中飞行的路线常常就是一个结,是一个真正的结,人是永远打不起结来的,人在地球上走,你出去走一圈,然后再回到家里面去,你想象你的脚上扣一根绳,这根绳在路上面永远不互相碰,无论你怎么走,走到最后回家的这根绳打起来的时候,它一抖就抖开了,这是永远不能打结的,所以鸟的本事比人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给你一根线,你穿来穿去、穿来穿去,然后把它一打打起来,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母亲在打毛线,拿两根针在那儿挑,最后到完了的时候,打一个疙瘩。所以原来你给她一根线,她扔给你的时候是一件毛衣,你穿在身上绝对抖不开的。 所以纽结这种东西尽管用了几千年,它从来没有成为科学的一个分支,大概真的很认真的成为科学的一个分支的时候是上上世纪末,上上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大概学物理的人都知道有个开尔文,开尔文就是以前从古希腊以来,人们都是觉得,他要研究现象,研究物质是什么东西构成的,就说物质是由某种颗粒构成的吧,它在一个层次上比如说是分子,如果分子解释不了,不能再进一步解释的时候,就说是由更细的东西构成的,那这个东西就叫原子,要是原子再不能解释,那我就再往下,所以叫分离法,从古希腊以来。当时所有英国的绅士都特别喜欢抽烟,一团一团的烟圈在空中环绕着,他当时看了以后,(突然)心生一亮,他说也许这个分离法的解释世界的方式是不对的,他说也许这个构成我们物质的基本的离子是个纽结,物质的不同性质呢,是因为它打结的方法不同而形成的,因为他当时非常有声望,所以于是有一些物理学家,尤其是英国物理学家,以泰特为首的,他们非常相信他的这种说法,于是他们就开始要找纽结表,他要把纽结列出来,如果你比如说物质是由原子构成的,那它就要列一个原素周期表,同样的,你说如果构成物质的基本东西是纽结的话,那你还要做一个纽结的表。 他们认为他们把所有自交数小于等于九的纽结全列出来了,但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说他们怎么能知道他们不遗漏?第二,他们怎么能知道,比如说这两个就不一样了。比如说这三个纽结,看起来很不一样,其实它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就是只要你在空间进行滑动,动来动去,完全不要拉扯断,可以把其中的这个互相互变,我们当然没有时间做这种事情,而且常常其实就是说,当时这个泰特他们花了20年的时间造了这个纽结表,造了这个纽结表,造完了以后,他们自己觉得从经验上说来,他们认为他们这个里面没有重合的、也没有遗漏的,但在数学上是没有证明的。 后来物理学家还是迅速的放弃了这个开尔文的学说,所以物理学家就把这个纽结忘掉了,不是忘掉了,就是不再研究这个东西。但对数学家来说,就突然有一个任务,第一次发现这张表在他们面前,数学家在某种意义上比较有雄心,或者比较没有事可做,他就说为什么这个表就是对的?然后他们就是研究,当时刚好在上(上)个世纪末,由于天体力学的原因,庞凯莱研究天体力学的时候,产生了拓扑学这个分支,然后拓扑学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拿来研究纽结,然后他们就真的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了从上世纪初,可以说一直到现在仍然在研究,当然把这个表弄清楚了,大概到60、70年代时候,慢慢就清楚了。
大概一直到本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由于很多意外的重要的发现,一下子把纽结推到数学的非常中心的地位。反正我不知道,大概你们知道一个诺贝尔奖,杨振宁得了诺贝尔奖了,数学里没有诺贝尔奖,但是数学里有一个奖叫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是还是相当出名的,大概最有名的奖之一吧。得菲尔兹奖的人里面应该说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跟拓扑学有关的,近年里面的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跟纽结有关的,主要说明它处于一个非常中心的地位。
但我今天并不想讲,它在数学里会是什么样、什么样子的,我就想说,自从物理学家想解释世界上的现象,造出了第一张纽结表,后来把它忘掉了,数学家就在那儿天天玩儿,玩儿了七八十年,在证明它相同与不相同的过程中发展了大量的数学工具,然后后来意想不到的,它在化学,结晶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中找到了一些应用。就是早期大家学中学化学的时候都看到,所有的分子式,分子式都是写在纸上的,从来不自交,就是自然的简单的分子都是写在纸上的,后来合成化学发现以后,人们就合成很多很多分子,这分子的话,真是打结的,真是在空间打结的,你看这个就是在1989年合成的,这个里面就出现一个事情叫“手性”。所谓的手性关心的是什么样的性质呢?你比如左手是右手的镜面像,它是它的镜子里的像。当然你不要很挑剔,比如我这个上头缺了一刀有个疤,这边没有疤,这是大概说的,它是它的镜面像。于是乎,它不但在拓扑上是一样的、几何上是一样的,但是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把这个左手移动到右手的位置,或者换句话说,我比较相信一个人伸给你一只手,尽管他这个两只手一个是一个镜子里的像,你马上就会认出来它是左手还是右手,好像早上穿鞋子,不会把左脚穿上右脚一样,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它互为镜面像,但是不能从其中一个变形为另外一个的东西,叫手性,手性非常不一样,同样的分子结构,手性不一样,往往可能体现出不同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来,尤其是在制药学的时候,特别是这个样子。这种例子最多,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氯霉素眼药水,氯霉素眼药水的分子它就是有手性,用具有正确手性的氯霉素眼药水点你眼睛的时候,你眼睛才能治好,用另外一种相反手性的眼药水(点你眼睛)的时候,你眼睛会变得更糟糕。于是就是说,判定分子有没有手性,就成为一个课题,大多数的时候,早期化学家很多时候是用经验的,因为早期是非常平面的,很多是用经验来判别。这个东西就没有手性,这是1840年就知道了,高斯,大家知道高斯,高斯这个学生就发现了这个现象。上面这个三叶结就有手性,他的镜面像是什么样子呢?你看你把这个东西交叉起来是这样的,这个在前,这个在后,那你往镜子里一照,前后刚好对调的。所以,画它的镜面像的时候,这个下行的,变成上行的,这就是它的镜面像,你回去试试,你永远不能把这个变成这个,你假如,有很大的耐心和时间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变成这个。这是1914年第一次被证明。
这是1982年发现在实验室里的,他们合成一种物质,首先合成一个线键,一个线状的东西,然后就是两根链,这些都是模型,原子,或者原子团,这中间是共价键,合成以后,它们又互相合成,合成一个梯子,然后他们最后就把这个两头呢,封闭起来,那封闭起来的时候,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上面跟上面的端点封闭起来了,下面跟下面的端点封闭起来了,另外一种是上面的端点和下面的端点交叉的封闭,形成一个梯子,叫莫比乌斯梯,他们当时就是不能判断,这个东西线度非常小,在高倍显微镜下不能判断,这个封起来以后,究竟是这样子得到的,还是这样子得到的。但是他们希望知道它的生成物是什么东西。这种梯子稍微动一下,可以平摊下来,摊成这个样的东西,可以完全化在平面里面,不自交的,但这个梯子是永远不能,你做不到这一点。完全放在平面里的东西,是没有手性的。理由非常简单,它完全放在平面里,放一个镜子在这儿,得到一个非常对称的像,你现在把镜子抽走,把这个东西平行地移动,就移动到自己了。所以完全放在平面里的东西是没有手性的。科学家用核磁共振的方法,最后得到的是生成物是有手性的,所以他推出来说这个生成物里一定有这样的东西,这是1982年的,他们就向数学家提出来说,能不能在数学上证明这个东西一定有手性,然后这个事情是在1986年的时候被证明的。
DNA大家就是看到这个梯子,这个梯子跟刚才那个梯子没有关系,你现在看到一个梯状的东西,就是双螺旋结构,酶在DNA上作用的时候,可以引起DNA重组,这个大概是现在分子生物学里头非常重要的课题,他们很关心就是说,酶的作用机理是什么东西,就是酶怎么样引起DNA重组?就是DNA有三个结构,第一个结构叫碱基顺序,这是最重要的,大家知道遗传信息就包含在里面;第二个就是双螺旋在螺旋,它在转,就是双螺旋结构,双螺旋结构基本上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呢?是由碱基顺序,以及就是说整个DNA在空间的位置,因为有时候互相之间有点引力,但大致是每过一个梯子转35度,大致是如此。第三个就是,现在很多尤其在小生物里,很多DNA,就是这个梯子是封闭的,可以是封闭的,它可以是像无限长的鱼线,但也可以是封闭的,如果是封闭的情况呢,那这个时候这个中心线,这个整个梯子,你把它像个纽结一样,所以碱基顺序叫第一种结构;双螺旋叫第二种结构;中心线叫第三种结构。
1971年的时候,生物学家,把同一种DNA,叫底物,同一种底物是不打结的,把它放到一个交泳,就是一个电,一种流质里面,让它带电,带电以后呢,然后给这个电泳池加一个电场,所有的东西就开始往前跑,就是不同位置上的频谱表示不同的速度,最后他们观察到一个现象,这个频谱是离散的,换句话说,就是它跑的速度是离散的,而且有的离散它比较小,就像我这个比较小的,有的呢比较大,那么他们当时就想知道这种现象反应了什么东西,怎么能从这种现象说明酶的作用机理。那现在还是拿我手中这根带子做一个样板,你看我手中是一根带子,它是有宽度的,它有两条边,我现在把这个边,看我这个带子,我现在转这个带子,我把它转、转、转,转了以后我把它封闭起来,封闭起来以后你会发现这是这样一个东西,这个时候,它这个缠绕现象其实可以打结,这是我手上的弄得比较简单,没有打结,就是弄一个封闭的,它这个缠绕的现象它有两种缠绕,一个就是当这个带子本身往下走的时候,它自然的,它会转,你发现没有,这个带子本身在转;第二,这两股带子,它也在缠绕,像油条一样、或者像辫子一样,那么,如果我把这第一种东西,比如我给它取一个名字,第一种这种转的现象叫“拧”,第二种现象因为它是两股,我把它叫做“缠”,那么我发现,我可以打开这个缠,我把这个缠可以打开,这样子我这个缠就被完全打开了,那么当我缠被完全打开的时候呢,拧就加大了,这个拧就很明显,对吧?我让这个缠加大,拧就变得平坦,这个是数学家发现的一件事情。
在说这个之前,我必须要说一个概念,就是叫环绕数。环绕数你看,这个最上边的小图上面有两个圆圈,像这种情况就是环绕数是1,我们叫做环绕数是1,你给一个定向以后,下面这个呢,这根线绕另外一根线绕了两圈,但是走向相反,箭头反掉了,是负2,像最里面一根,它虽然也是这两个圈永远抖不开的,但这个时候呢,就从环绕数来说呢,它一个是向上的、一个是向下的,所以是零,这是一个数学概念,叫环绕数,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守恒律,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守恒律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这个拧数我们没有定义,但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现象了,就是拧的个数和缠的数目加在一块刚好等于环绕数,等于什么环绕数呢?就是说我这个带子原来放在这儿,这是一根带子,它有两个边,两个边就是两个圆圈,它两个圆圈之间有个环绕数,所以它等于这个东西。所以环绕数它是一个整数,但是这个拧数和缠数呢,都是连续的,就是它不一定要取整数,所以环绕数是这样一个量,刚才这个公式是数学家发现的公式,1969年发现的,后来他们就拿这个公式去解释刚才那个现象。就是说我这个东西作用以后,作用以后它进行了重组,重组以后的话,你可以想象,它有的东西在这个里面,有的它蜷缩得很厉害,蜷缩得很厉害的时候,它这个在电场的作用下它受到的阻力很小,它跑得比较快,有的东西呢,它比较松散,比较松散它受到的阻力就比较大,所以它跑得就比较慢。就是这个对DNA而言,它这个转的速度是完全由碱基顺序所决定的,他们后来把这个生成物打捞上来,发现一下,发现碱基顺序并没有改变,碱基顺序跟以前一样,所以换句话说,拧速应该是跟以前一样,那唯一的引起这种有的紧、有的松的原因,他们就觉得是因为缠数改变了,因为刚才一个等式是拧数加缠数等于环绕数,那是因为环绕数改变了,环绕数改变了刚好就是说这个DNA的一股突然断开了,断开了以后就是这根,断开以后又重接一下,这个断开、重接刚好不改变碱基顺序。
但是呢,对于改变了环绕数的,环绕数改变1,换句话说呢,它就把这个整个拧数和缠数的和呢,做了一个离散的跳跃,所以因此使得它这个速度产生变化。还有一种频谱间隔特别大的是什么原因呢?他们分析就是因为它同时断开,同时断开又同时接上,这个时候环绕数的改变是2,所以这个之间的频谱就非常大了,当时也是一个很轰动的事情,第一次成功的用数学来解释了DNA的这种机理。
我结束这个演讲之前说几句话,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在说哲学还是说什么原理,就是说一个事实,就是从实践里发现问题,发现问题然后经过理论的探讨,最后呢,再回到实践中去,这个就是分子生物学家首先观察的这种现象,然后数学家用理论把它解释出来,这个对不对呢?再拿到实践中去,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这既验证了数学的这种有用,也验证了本身原来分子生物学家的假设是正确的。我们再到更宏观的看来,纽结论本身,它是由物理学的这种需要而产生的,而来因为它不对,至少不能解释物理现象,物理学家就把它忘掉了,它就纯粹的变成一个理论的东西,数学家很愉快,尽管没有任何应用,数学家很愉快的在不停的孜孜不倦的做,耗费自己的时光。然后在做了很多很多年以后,最后终于在生物学和化学中有了应用,从宏观上讲,这个也是一个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过程,不过这个过程不应该这么简单化,就是好象总是起源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实际上,我觉得,真理探索它是一个无限的循环的过程,所以叫实践理论,实践理论,我愿意画这么一个图,人们比较喜欢看到实践的东西,不喜欢看到理论的东西,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理论的东西象纽结一样的循环往复,出来一段,又是一个纽结,出来以后又是一个纽结。所以我最后打算结束这段话的时候,用我当年插队时候念过的毛泽东的一个话,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往复循环,以至无限,我的报告完了。
主持人:谢谢王教授,下面我们看一下来自凤凰网站网友的提问。首先有一位网友叫做“火狐狸”,他说“我觉得在数理化中,数学最没干头,可您还干得挺起劲儿,我认为要干数理化,就得得诺贝尔奖,但诺贝尔有物理奖,有化学奖,唯独没有数学奖,所以您干得再好,也比不上杨振宁和李远哲,所以,您干嘛不写点先锋戏剧,或搞点国际政治,弄个文学奖或和平奖享受享受?”
王诗宬:我想,首先我从前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知道,数学上没有诺贝尔奖,但是我还是做了,做了这么多年,所以可见的……当然,我先说一句,即使它有,我大概也不会得到,但是我做的时候就不在乎它有,做了这么多年了我也没在乎,我何必还要在乎它有没有诺贝尔奖呢?我感到很愉快,做了这件事情。
主持人:另外,我们还想知道,为什么诺贝尔这老头,不设一个诺贝尔数学奖?有人说是这位老先生跟他的女婿不和,而他的女婿是数学家。
王诗宬:我怀疑故事不是这样的,我能听到的故事不是这样的,首先这是一个故事,有个瑞典数学家非常有名,叫勒维他,前面讲的完全是故事,以前就是说他喜欢的一个女子,后来跟了这个数学家勒维他,他当时的个人的魅力不如勒维他。
主持人:比他女婿还要厉害。
王诗宬:不是这样的,这都是传说而已,并不是女婿,而且是非常随便的,很多人都被讨论过无数次了,大家一再说,这个只是社会上的想象,诺贝尔不见得这么小气。
主持人:那您想他是什么原因呢?
王诗宬:我想他当时他比较看重一个东西,能够直接对社会有……他认为的,至少他认为直接比较有社会效应,比如说他不光没有(数学奖),很多奖都没有,很多方面,比如说对天文也没有,对数学也没有,对考古也没有。
主持人:他可能把天文算到物理里面了吧?
王诗宬:有可能,对,有可能。但是我认为他当时就是像物理化学这种,还有医学这种一开始就有了,他认为这种东西,能够对人类的生活产生最直接的效应,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个应用化学家,制造炸药的。
主持人:下一位网友叫“我等你过了那条街”,他说“在您的讲话中,似乎把凯尔文勋爵说得位置很高,但我所知道的凯尔文好像没干过什么好事,他在1895年曾宣布,人们很快就会明白X光不过是个童话,1901年他又胡说,断言无线电这玩意儿不可能成功,我真不知道这家伙的眼力怎么这么差,还能当上英国科学领袖,这让我觉得权威不过尔尔,当然您和他们还是不一样的,您至少年轻的时候比他们长得漂亮。”他大概是想让您说说凯尔文勋爵,他怎么眼力这么差,然后,很多科学家经常还要提到他。
王诗宬:一个人做过很大贡献,人能力总是很有限的,做了一个很大贡献,他以后可以经常保持沉默,那么大家就会一直觉得他很(了不起),但是他有可能,有时候什么事都说,什么事都说,那你总会要说错好多事情的,时代在前进。
主持人:爱因斯坦也没说错这么多东西?
王诗宬:凯尔文当然不如爱因斯坦那是毫无疑问的,那时候爱因斯坦还没有出世呢,噢,不是,爱因斯坦还没有成名呢,1905年才成名的。
主持人:还是奥地利一个小职员。好,现场观众如果有哪位想跟王教授直接交流可以(举手)。
观 众:王老师,我想问您,您所研究的纽结理论和您打结什么的?
王诗宬:其实,我跟你这么说吧,我其实就是做理论的人常常说来可笑,虽然理论上我可以证明某一个结跟某一个结你永远不能变过去,但真打的时候,他们打得比我又好又利索,我年轻的时候,我插队的时候,那个时候挖水渠,我挖出来的一条水渠,边上总有一点犬牙,我反复在那儿练,始终练,有的老乡挖出来以后直得不得了,一点点都没有那个(犬牙),一锹一锹插下去捱着走,我觉得我始终就练不出那个功夫来,其实有的人有时候在某一方面虽然听起来做了一点事情,其他方面可能很差。
主持人:孔子登泰山的时候,后人描述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是孔子下了山以后呢,就告诉大家“学者要述而不做”,就是我们可以说,但是我们什么都不做,王教授这一点做得很好。
王诗宬:没有,我还是想做,我还是努力做,但是有的时候做不好。
主持人:嗯,下一位。
观 众:王老师您好,您刚才讲的纽结这个问题,从您的心底里面您认为物质世界到底是来自于纽结表,还是来自于经典的可分的理论?
王诗宬:我自己的感觉是,到现在为止,纽结论不能够成功的解释,就是基本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能够用纽结为基本元素来解释世界有很多成功的这种想法,所以整个现在的发展仍然是细分,就是从希腊来的细分法,大家去寻找微观粒子,我想是这样,但并不妨碍有些物理学家,世界上它是曾经从另外一个角度,他说他们现在比如像奥斯汀、伯克利有些人说,再细节我也不懂,就是所谓叫拓扑物理、几何物理,有这种想法的人仍然有,未来什么样的不知道,就是到现在为止,仍然用粒子解释这个、用微粒解释是非常成功的,解释了很多现象,我们的世界变得这么繁荣、变得这么物质化。
主持人:好,接下来再看两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叫“阿拉伯数字”,最近有一套数学丛书叫做《通俗数学名著译丛》,看完后发现一个无情的事实,那就是中国古代虽然取得不少数学成就,出现了一些大数学家,但这套译丛中,没有一部涉及中国古代数学,对此我深感痛心,并要问这是为什么?”
王诗宬:我想中国数学古代还是非常辉煌的,中国数学它总的来说,我不太知道这套丛书是什么样子的,我个人不太知道,我觉得中国古代数学,它更多的强调实用和计算,它在某些方面做得的确是比如像,有很多事情应该说,但是古希腊,打一个简单的比方说,比如说这个古希腊的毕达格拉斯定理,中国以前叫勾股定理,但是中国往往它是这样的,它是非常具体的知道,比如说三、四、五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但是它没有提炼成为像这种A的平方加B的平方等于C的平方,这个样子的一个公式。还有比如像圆周率也是一样的,应该说刘辉、祖冲之圆周率算得都非常辉煌,还有解方程,都曾经达到非常辉煌的地步,但这种辉煌的地步它主要是我自己的认识,首先我本人是…,我自己认为就是说,近代的思辩的科学,仍然希腊大概还是起了非常最主要的影响,它把它抽象化,抽象化以后,然后在里面开始进行进一步推理,对很多新的东西的发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假如不能写成A的平方加B的平方等于C的平方的话,那可能像无理数这种事情几乎不会发现,因为生活中不会出现无理数,光光去为了量东西,你要量得多准确、算得多准确,有理数足够了,而且无理数的确也没有用,在生活实践中没有用的,比如说你随便量东西或者是算东西、称东西、卖东西永远用不到无理数,那么就不会到无理数的发现。
还有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如果我们当然从前古代也知道很多很多几何现象,很多事实能够做很好的圆、很好的三角形、很好的正四边形,但是它没有一个所谓叫公理系统,然而欧几里得,他就说有公理系统,大家学过平面几何的都知道,我最前面设5条公理,这是最简单的,他想把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推出来,这个五条公理,它里面最著名的就是说其中叫第五公设,就是叫平行公理,就是我们非常简单的过一条直线外面的一点,最多只能做一条直线和它平行,这个早期的叙述非常麻烦,他们当时想呢,把这个东西从前四条推出来,这个事情可能在别人看来是非常无聊的,我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就把它当做公理嘛,但是数学家他愿意做这个事情,在昏天黑地中做了一千多年。最后终于有些人发现,这是个很长的故事了,发现它推不出来,这个第五条是独立的,换句话说你假定你假设过这一点以外,有更多的直线和这条直线平行,那所有的矛盾都不会出现,这个最后导致了双曲几何的发现,而现在我们经常在物理上说时空弯曲,假如没有这个样子的,最初的(思考)当然这个后来导致了很多深远,几何学上的很多深远的东西,我想相对论也很难说它有发展的基础,应该说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想是从希腊,源自希腊这套思辩的数学,就是说你看着中间没有用的,其实它起了很多的…,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更有主导的地位,应该说中国的数学在古代的计算方面的成就是非常辉煌的。
主持人:是实用的,不实用的东西我们也不研究。好,下一个问题呢,叫做“澳门上空的鹰”这位网友,他说“直到今天99%的数学仍掌握在像您这样的不到1%的人的头脑中,所以我们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数学究竟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我认为数学过分远离公众并不是一件好事,我想象数学在多年前还是一种乐趣,即使它为少数人所有,但这些少数人的动人故事却为大多数人所有。比如清华数学系主任熊庆来荡舟西湖,统一了数学概念的中文译法,他还买菊花取悦于他的太太,还在南方杂货铺里发现了华罗庚小店员,可现在数学故事怎么越来越少了呢?”这是他的感叹。
王诗宬:我想是,其实这种故事还是有很多的,不过就是大家现在这个…我估计跟整个社会更加多元化也有关系,大家感兴趣的事情更多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比如说你随便打开一个《南方周末》,拿一个什么东西,各种各样其他的很容易写出来的故事可能更多了。
主持人:《南方周末》上的故事张柏芝和谢霆峰比较多。
王诗宬:虽然我是不买花的,不过我觉得现在买花给太太的人也还是有的,就是说只是现在大家不报道了。但是你前面说的一个事情,他说的确无疑有他正确的一面。第一就是说,所谓叫数学,数学它应该停留在很多不同的层次上,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座的每个人都学过很多数学,这种数学什么样呢?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在今后的一生中,得益于数学,不在于得益于对某一个具体的(知识的掌握),他说这个定理我从来没有用过,而在于这种思维方式,他比较清楚的考虑一些问题,比如说学过一点概率、学过一点统计,他听到一些话的时候,他能够分析一下这个代表多少,反正我也是乱说了,就是的确就是还是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你说什么叫做数学?因为数学在各个不同的层次上,有些东西是相当前沿的,相当前沿的恐怕也只有少数人能来做,因为大家来做,因为这个东西毕竟跟你做牙医不一样,给人修了牙、做了牙就可以挣钱的,这个东西不挣钱,不挣钱的东西不需要太多太多的人做,社会,尤其现在的社会我想是这样子的。
主持人:好,谢谢您。
观 众:王老师您好,想请问一下您对中国结有没有研究,这种结与其他结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谢谢。
王诗宬:我真的是非常抱歉的,我最近看到了中国结,我还曾经说过什么时候要研究研究它,还没有来得及,就是从去年过年的时候。没有,这个结这么说吧,这个结它有个特点,它是艺术品,艺术品相当对称,具有高度对称性,你看的至少,很多纽结是没有对称性的,稍微奇怪一点,凡是作为艺术品的东西它非常强调对称,它是一个非常高度对称的结,我能说的就这么多。因为对称的东西可以做艺术品,而现在有很多更多的这种,在某种意义上纽结正在进入生活,你看现在很多这种-----包括中国,比如我估计好像在那个地方,中关村那边现在就有个大个三叶结雕塑,现在很多人做茶壶、做杯子的时候,做那个东西的把柄的时候也会做出一个纽结来,在这个意义上面,它成为艺术的一部分。
观 众:请问一下王教授,这个绳圈和这个莫比乌斯带,还有克莱茵瓶有什么关系?
王诗宬:绳圈是一维的,莫比乌斯带和克莱茵瓶是二维的,一维、二维你可以理解,像平面就是二维的,莫比乌斯带和克莱茵瓶都是所谓一种曲面,叫做不可定向曲面,就是说它这个莫比乌斯带,你既然说这个事情,我估计在座的人都知道这个莫比乌斯带,莫比乌斯带就是这样一个东西,还是很容易简单的,就是刚才你看到的,你现在如果把这个东西折成这个样子的话,那就是一个正常的带子,像我们的环圈一样,我这个纸太短了,要这个样子,折出来就是一个莫比乌斯带,又叫作莫比乌斯帽儿,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说,这个样子折出来的时候,你要想从这边到这边,你不经过边界,不经过这个边界你是永远爬不过去的,但这个不需要,这个东西你看,你只要耐心的顺着中心线走,走,最终就走到里面去了,它就是单层的;克莱茵瓶是更复杂了,克莱茵瓶你拿两个莫比乌斯带,把两个莫比乌斯带,当然这个莫比乌斯带你这个样子一粘以后呢,这个样子一粘以后,两个边变成一个边了,你拿两个莫比乌斯带把它沿边粘起来就得到克莱茵瓶,这个克莱茵瓶不能放在我们空间里,放不进去的,我们这个三维空间放不进克莱茵瓶,克莱茵瓶是最简单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这个东西不能放在我们的三维空间里,要把它嵌入到我们的一个空间就需要四维空间,这个已经到四维了。
观 众:它们可以推广吗?
王诗宬:可以推广,作为一个高维纽结,但是最有意义的还是这种纽结,因为我们现实生活的世界是三维的,可以推广,有高维纽结论。
提问:就是现在这方面有这些理论吗?
王诗宬:有,高维纽结论比低维纽结论简单。分类学来得更简单。
观 众:请您预计一下这个绳圈对物理学的发展?
王诗宬:我现在回答不出来,而且这个东西,我会一说一大堆,而且没头没尾的,这个就是圈,一方面就是数学物理的方法运用到绳圈上了,就叫杨米尔斯方程,就是说这种东西,跟这个打结有关。还是就是打结可以用辩群形成,辩群就是strand(一些股缠绕),太多的东西我不知道,而且我说出来一大堆,我估计这个事情我不能说,我回不来。
观 众:谢谢王教授。
王诗宬:其实我问别人问题的时候,比别人问我问题的时候要多得多,因为一个人的,他总是有大量的事情不懂得。
主持人:经常的情况下,您是提问题的人,而不是回答问题的人。
王诗宬:我想我提的问题比回答的问题更多,虽然我是教员。
主持人:心理学家说像您这样的人是还没有老,已经走向衰老的人总爱回答别人的问题,经常跟人说“孩子啊,我们那时候不是这么生活的”。
这位网友叫“天高云淡”,他的话写得很长,他说“杨振宁在回忆父亲杨武之给他的影响时说,父亲是大数学家,但他教给我的不是数学,而是数学精神,正是这种数学精神,使数学成了一种高级趣味,造就了一批好书,比如说《数论妙趣》”,不知道您听说过没听说过。
王诗宬:没有,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主持人:他说“比如说《数论妙趣》,它把高斯称之为“数学之皇后”的数论描写得生动有趣,读来真是一种享受,而《数:科学的语言》这本书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数学文化”;还有一本书叫《无穷之旅》,他把神秘的无穷大描述得淋漓尽致,而康桥数学家康威的《制胜之道》采集了几乎有史以来所有的数学游戏,我特别想知道,讲课如此有意思的王教授,您有什么类似的著作可以推荐给我们吗?让我们为之陶醉一把?”
王诗宬:我真的还没有,不过你在讲的事情我比较熟悉,刚才说的康桥的就是剑桥康威,康威现在在普林斯顿,他其实就研究的这种东西,当然他研究的东西非常多,他这个人非常聪明,就是比较罕见的这种聪明的人,就是数学家有两种,物理学家也是一样,有的人他做这种东西需要很深刻、很深刻的理论,之前你要学大量的东西,然后才能去做,康威他不一样了,他白手起家,什么东西他都不要的,属于那种,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对刚才说的这个纽结表就有好多改进,他现在在普林斯顿。我没有这个样,我真的没有,有时候也有人建议过我,我没有,我就是觉得随便说容易,真写下了很花时间,而且我也不见得写得好,假如有人愿意将来跟我一块写,还有比如说我不会电脑,不会电脑画图也很费事,就是将来有机会,我也不见得很好,可以写一点东西,以后。
主持人: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王教授是连这个光驱是怎么打开,它是干嘛的都不大清楚,是非常罕见的一个完全不懂计算机的数学家。
王诗宬:也不是,我可以往里面敲打一点东西,这个还是可以的。
主持人:别人帮您打开以后,您再那儿敲点东西还是可以的。
王诗宬:所以他们经常说的话,包括他们说,王老师您还不是小菜一碟,其实我是zero根本就完全不知道。
主持人:真的不明白,我看到王教授这样的,我就给他讲了,说《读者文摘》上曾经登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有一个老太太,她买了电脑以后,回家呢,还给电脑公司写了封信,表扬电脑公司,说他们想得非常周到,她一摁光驱出来以后,说连我放咖啡的地方都有,实际是放光盘的。 好,请这位。
观 众:我想问一下王教授,您能讲一下您爬山的经历吗?就是从什么时候爬山?或者是都什么时候…
王诗宬:我以前就喜欢旅行,真的开始爬山也并没有成功过,后来在1989年的时候爬过膝力马扎罗,是在向导的带领下的,第一次非常成功的爬山是1993年,跟北京大学登山队一块儿去的,学了很多东西,受到了很多训练,然后有时候我又爬过一些其他的山。我想既然你问这个问题了,我只想说一句话,当时我看那个电影,就是上个周末看那个电影叫《垂直极限》,大讲堂里放,开始的时候很兴奋,看了以后心里头很惆怅,就是说比较惆怅吧,就是说它其实一个抢险,抢险主要是一个人,一组人掉到冰裂缝里去了,等待抢救,完全是好莱坞的演员拍的,但是我心里很惆怅的就是说台上演得轰轰烈烈,下面牵肠挂肚、掌声雷动,其实从演员里面到听众里面,也许我是真正唯一掉进过冰缝,等人来救的,当时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主持人:当时是什么样子?
王诗宬:这个讲起来很长,但是所有的这种事情都非常简单,我因为只是一个人掉下去的。
主持人:别人还可以看到你是吧?
王诗宬:有一个人,但的确有些事情是真的,有些事情比如说我当时对那个人说,如果天已经很晚了的话,如果没有人过来的话,我让那个人回大本营,走的时候怕这个口上迷失掉,我们有个船,我说那你就把这个船埋在这儿做一个标记,它那个上头是把一个人的人躯弄上去做一个…
主持人:您这个时候想的都是生死问题吧?to be or not to be,已经不是那个什么六个人,如果三个人认识,一定那三个人…
王诗宬:完全不是、完全不是,非常简单,对,我想也许我就在这儿了,真是这个样子的,非常简单,所以这个事情也很好,所以使得我以后遇到什么人地生疏,一些愉快不愉快的事情,你要跟我说有什么好处,或者你想象我现在还很好,居然坐在这儿,向这么多人讲话,心里头很释然,不太计较小的事情。
观 众:我突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很多搞拓扑的数学家都非常喜欢爬山,伏瑞得曼和斯麦尔,他们也都很喜欢爬山,这个您能不能谈一谈,就是为什么会…
王诗宬:我唯一的解释是拓扑是研究形状的,山的形状太好了、太美丽了。我真的不知道,我知道伏瑞得曼喜欢爬山,他说的我想说一句话,他说的斯麦尔和伏瑞得曼都是得过菲尔兹奖讲的,分别一个是证明五维以上的庞凯莱猜测对、一个是四维的庞凯莱猜测对。伏瑞得曼我跟他一块儿跑过长跑,两个人。
主持人:是你跑赢了还是他跑赢了?
王诗宬:他比我先,但是他没有他的太太先,他太太差点就入选美国的奥林匹克运动队,她跑赢了。
主持人:在节目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呢,我还是一如既往的请您用一句话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您今天的讲题是从打结谈起,那您讲了这么多呢,您用一句话告诉我们,您最想告诉我们大家的是什么?
王诗宬:那我就是刚才那个上头已经说过了,就是“探索真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循环反复、一直无限”。
主持人:就是要告诉大家一句话“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
好,谢谢王教授、谢谢现场观众。
王诗宬: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