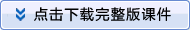第九讲
我们上次课讲到了魏晋玄学。在中国历史上,哲学的发展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第二个时期是魏晋时期,那是第二次的百家争鸣,第三次是宋明。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三次发展的哲学含义,我们就对中国哲学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我们上节课讲了魏晋玄学的主题——自然和名教的关系。围绕着这个主题产生了好几种不同的解答。一个是主张自然为本,名教为末,它的代表是王弼的贵无论;一个是主张名教为本,自然为末,它的代表是裴頠的崇有论;第三种是自然名教是一回事,它的代表是郭象的独化论;第四种是只要自然,不要名教,这是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都有一套理论,都有一派风格,都是了不起的人物。鲁迅先生当年花了很多时间校勘嵇康集,他的性格是现代的嵇康。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自然名教之辩这一哲学问题,仍然是人类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自然是理想,名教是现实,那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如果名教是现实的,不能否认的东西,那它就是必然的,可是人不能只是生活在必然中,还要求自由,这就构成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如果说名教是社会组织,是个既存事实,我们也可以说是个名教社会,但是它是否符合我们的价值呢?这就构成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这都是古今中外都碰到的问题。这也就是历史的悖论。康德在完成了三大批判后,又对历史理性进行了批判。他发现历史理性有一个内在矛盾,叫做历史理性悖论。即历史的合规律性和历史的合目的性的矛盾。目的是指人类的价值理想。这种矛盾就是自然名教的矛盾。一个是现实,一个是理想;一个是必然,一个是自由;一个是事实,一个是价值。所以魏晋玄学讨论的是普遍的哲学问题,西方人感觉到了,中国人也感觉到了。可是在这普遍的哲学问题中间有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是不同的。康德所讲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是指西方的历史。在当时的欧洲,拿破仑征服了欧洲,颁布了拿破仑法典,这给康德等德国哲学家提供了一个理想。当时的德国有大小三百多个不统一的邦国,通过武力的征服则违背了德国人生活的目的性。这是历史的合规律性和历史的合目的性之间产生的矛盾。就魏晋来说,黄巾大起义后,东汉政权没了,三国鼎立,连年征战是事实的必然。东汉非崩溃不可,因为它太腐败了。它的灭亡是合规律的结果,这恰恰是魏晋玄学提出的问题。
那么我们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呢?是从抽象的哲学出发,还是从具体的历史处境呢?这牵涉到我们怎样搞哲学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思路:理一与分殊。理一是普遍的道理,分殊是各时代民族不同的具体的历史背景。是从理一到分殊,还是从分殊到理一呢?我从这个课的开始就讲一个观念,就是全世界没有一个普遍的唯一的哲学,哲学没有标准答案。所有的哲学都是从具体的分殊开始的,正因为如此,才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如果只讲普遍,从普遍出发,那就会搞成教条主义。所以魏晋玄学讨论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问题。当时的哲学家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特殊处境出发,而上升到自然和名教的关系,提出不同的解答。加上“将无同”共有五种解答。哪一种是对的呢?每种解答都是偏见,性之所好。所以说哲学是说出一个道理的偏见。哲学是多元的。
我们进一步考虑魏晋玄学为什么那么繁荣。这要联系魏晋那个时期的整个社会历史环境来考虑。因为并不是任何时代环境都能产生出哲学的。哲学是在苦难时代产生出来的。我们经常听说苦难出诗人,诗穷而后工。只有承受苦难,才能超越而重生灵感。“文章憎命达”,哲学也是如此。魏晋时代是乱世、分裂的时代,当时有这样的话:“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许多玄学家都死于非命。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当时都发生了。到底怎样的社会秩序是合理的?每一种选择都是一种理想,用这种理想来批判现实,使人们在那个苦难的年代在精神上有个支柱,有各寄托,有个追求。所以,每一个哲学家都有一种批判意识,同时又具有深厚的社会价值理想。只有与历史共命运的时候,你才能理解那个时代人的矛盾和痛苦,才会理解阮籍遇歧途痛哭而返的做法。中国的哲学家都是诗人哲学家,你读一读他们的诗就可以体会得到。鲁迅的《彷徨》特引用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在民国的黑暗时代,就像屈原、嵇康、阮籍一样而思索。屈原的《天问》提出了许多的哲学问题。它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呢?是苦难、苦闷、碰撞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类就是这么伟大!在别人将无同的时候,哲学家、大思想家一定要说出一种道理来。所以,在当时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强烈的理想追求。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名教自然之辩所做的几种选择。王弼的“自然为本,名教为末”蕴含着什么批判意识呢?当时的统治者提倡名教,司马氏以孝治天下,而司马氏篡夺曹氏政权,用后人的话说是欺负孤儿寡母。司马氏用名教杀人。王弼说名教是自为的东西。所有的名教只有符合自然才能像天地自然一样和谐。人类社会像自然那样和谐,不是更好么?“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阮籍更有批判意识。他们认为名教是杀人工具。鲁迅的《狂人日记》讲封建礼教“吃人”,就是用白话翻译了嵇康、阮籍的话。但是仅仅批判还不行,还要有个理想,这在当时就是“无君论”,认为世上最糟糕的是权力。这种思想可以说来源于道家。道家分统治者为四等。最好的统治者是“太上有之”,其次“亲而誉之”,第三等是“畏之”,第四等是“侮之”。魏晋时期的统治者是“畏之”、“侮之”。另一种理想是“虚君共和”,即共和理想。所以,哲学的抽象思考比如什么有无、自然、名教等等的问题背后都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理想,这是哲学的生命力所在。今天我们讲玄学的目的不在玄学本身,而是要懂得从理一到分殊的哲学探索之路。只有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从社会苦难中生发出来的思想才具有普遍意义,才可以和西方、印度的哲学进行对话、沟通。不同的时代、文化所提出的问题也不相同。比如康德提出的历史理性的悖论是德国的现实状况和拿破仑征服欧洲大潮流的矛盾中产生的。
难道哲学仅仅讨论这些问题么?那么关于我怎么活着,怎样活得幸福等的问题就不是哲学问题了么?其实,这种关于一己生存的问题是同上述哲学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魏晋时代,每一位哲学家都把自己对社会、历史、国家的思考与个人的安身立命联系在一起。孟子早就说,知识分子应该“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些都是哲学,从古到今,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如何独善其身,求得个人幸福,这里面也有很深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围绕着两个字:“逍遥”。怎么才叫逍遥?自由自在,心安理得。中国人的答案与西方人也不一样。逍遥的确是一个哲学问题。刘小枫写了一本书叫《拯救与逍遥》。他做了一个绝对判断说,基督教文化中不讲逍遥,只讲拯救,中国文化则相反,这是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拯救靠上帝,逍遥靠自己。实际上,拯救的目的还是逍遥。刘小枫把这二者对立了起来。把这种关系搞清楚,才可以把中西哲学的不同,中国哲学发展的线索,尤其是魏晋时期从逍遥走向佛教的发展线索理清楚。
逍遥一词出自《庄子》。庄子以诗人的想象,在《逍遥游》的开篇讲述了一个寓意深刻的寓言。究竟是大鹏逍遥,还是小鸟逍遥呢?其实二者都是有待的,都不逍遥。庄子追求的是无待,是精神逍遥。无待包括三个方面,即无己、无功、无名。能做到这三点就可以达到精神的绝对自由。这个理想特别难实现,因为它是空的。到了魏晋时期,对逍遥的追求有不同的说法。王弼讲“以理化情”。理不是抽象的,而是有情感的。情是升华到理的情感理性,是“应物而无累于物”。嵇康、阮籍也有他们的逍遥观。他们认为,在社会中间,名教中间是得不到逍遥的,但是在自然中是可以得到的。嵇康“手挥五弦,目送飞鸿”,超化到自然宇宙的和谐之中。这种境界是远离社会,不食人间烟火的。这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的境界很相似。王弼、嵇康的境界是很难做到的。到了郭象,对此做了新的解释。郭象认为,有待就是无待,物事各有自性,其为逍遥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不羡慕别人,各得其乐。这种理论很符合今天环保主义者的理论。俗话说“麻雀不跟燕子飞”。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那是儒家的理想。可是魏晋时期做不到。这各种各样的理论都包含了哲学家内在的困惑。即使是郭象提出了大鹏、小鸟各有其乐,他本人最后也没得好死。他是在“八王之乱”中死于非命,他也没法逍遥。可是这个理论有很现实的意义,在中国哲学史中有普遍的哲学意义。郭象在大鹏小鸟同样逍遥中提出了一富有启发意义的玄之又玄的理论,那就是“独化于玄冥之境”。它蕴含着一套社会理想,那就是整个社会都是一种“自为而相因”的结构。这种关系是无需谁来管理的。这相当于亚当?斯密所讲的市场经济理论中的“看不见的手”。每个个体是自为的,但是从整体上看,他们又是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构成一个大的和谐的体系。莱布尼兹的哲学单子论讲每一个单子都有个先天的和谐。上帝把各个单子结合在一起,构成大的和谐。这跟郭象的理论很像。
逍遥是每一个人所碰到的问题。我们就是不能逍遥。嵇康似乎是在自然的大化中得到一种逍遥,然而,他也落得杀头的下场。郭象的理论似乎高一点,但他也死于非命。但是这种种的讨论激发的哲学思考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哲学遗产。
郭象的理论虽然高,但是到了后来就碰到佛教了,出现了佛玄合流。当时有个有名的僧人叫支道林,他也讲逍遥。他批评郭象说,如果每个人都通过满足自己的自性而获得逍遥,那是有问题的。比如桀纣,他们的自性是杀人,做了许多坏事,这是逍遥么?我们也可以问郭象,像小偷、杀人犯、贪污犯,他们也有逍遥么?照郭象的看法,还有没有价值标准存在,如果没有,那不就成了价值虚无主义了么?所以,逍遥与否,必须有一高于自性之上的超越性的价值存在,必须拯救自性,必须有一绝对的权威。那就是至人之心,佛性。它是判断的权威。就人类来说,我们要接受道德、宗教价值权威的指导。只有把自性提高到与佛性合二为一地步,才能谈论逍遥与否。桀纣是不能逍遥的,因为他们的自性离佛性太远了。郭象解说逍遥的理论被称为“郭理”,支道林提出“至人之心”,反对郭象,广为人接受,被称为“支理”。于是,玄学就渐渐地被佛学取代了,中国就进入了佛学时代。
中国为什么进入佛学时代,为什么接受佛学呢?佛教填补了当时的精神的真空。中国的佛教不是像印度佛教那样求得个人的解脱,而是为了“逍遥”。我们前面讲过,中国接受的大乘佛教有两派,空宗和有宗。空宗的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四大皆空。所有的事物都是无自性的,都是因缘凑合而成。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不真故空。但是中国人在事实上很难接受这种观念,所以,中国人在接受了空宗的理论以后,只是把它当作本体来说,就是比有、无高一点。所以中国的佛教就将空宗转化成性宗。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不同关键就在一个性字。什么都可以空,但是性是不可以空的。中国人讲人性善,性怎么可以空呢?当时的佛教理论讲佛性是不空的。中国人把性——也就是心——解释为自性清静心,也就是人人皆有的。人只要保持自性清静心,就可以逍遥,就可以成佛,就可以进入涅槃境界。心有两种,一种是自性清静心,还有一种是污染心。只要去处了污染心,就可以达到自性清静心。经过佛教的中国化,就把印度佛教的把一切看得很空的虚无主义回归到中国自己的人性本善的理论上。这是世界文化史上一个伟大的转变。接受的东西一定要以中国自己本土的东西作资源,用中国人的眼光去看佛教,可以改造它,可以接受它,然后把它化为己有。这对中国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宋明理学里的心性之学完全是受佛教的影响而发展出来的体系。
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自性清静心和污染心的关系怎么处理?这在后来高度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中,可以找到解答的方法。据说禅宗五祖弘忍为了传授衣钵,就令他的弟子作诗。有一个大弟子叫神秀,题了一首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当时的一个砍柴的和尚慧能看了以后,也题了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于是弘忍就把衣钵传给了慧能。这就开创了禅宗的南派和北派。一派是顿悟,一派是渐修。慧能的南派禅宗后来在中国发扬光大,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条修养身心和得道的方便法门,把佛教高深的理论、宗教的修行和我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挑水砍柴,无非妙道”,都有佛法的真理在里头。这就把宗教和现实的生活结合起来。唐末五代一片战乱,当时的禅宗大师们跑到深山老林,一面自力更生,一面参禅悟道。形成集体参禅、集体劳动的共同公社。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写诗作画,形成一种重要的禅宗文化。这是怎么搞出来的呢?无非是追求逍遥而已。但是为什么找逍遥一定要出家呢?难道现实生活中得不到逍遥么?可以的。这就是下次课我们要讲的宋明理学的内容。
| 课件名称: | 哲学导论讲义 |
| 课件分类: | 哲学 |
| 课件类型: | 电子教案 |
| 文件大小: | 116.36KB |
| 下载次数: | 4 |
| 评论次数: | 2 |
| 用户评分: | 9 |
- 1. 哲学导论讲义:第一讲
- 2. 哲学导论讲义:第七讲
- 3. 哲学导论讲义:第三讲
- 4. 哲学导论讲义:第九讲
- 5. 哲学导论讲义:第二讲
- 6. 哲学导论讲义:第五讲
- 7. 哲学导论讲义:第八讲
- 8. 哲学导论讲义:第六讲
- 9. 哲学导论讲义:第十一讲
- 10. 哲学导论讲义:第十讲
- 11. 哲学导论讲义:第四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