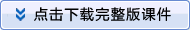DNA对社会关系的决定力究竟有多大
作者: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陈 甦
发布时间:2006-10-12
我们离开母系社会的时间已经不短了,但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情形可能依然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父亲想做亲子鉴定的原因。用DNA检验技术证明血缘关系,只需花上千余元,再抽取些许静脉血,即可检验,其正确率达到99%以上。DNA检验技术所具有的准确率高、方法简便、成本费用低等特点,使其成为今天的父亲们用来破解其妻不忠、其子不亲之疑惑的首选技术措施。可见,最新颖的科技成果往往被用来解决我们最古老的焦虑,好古者不必担心古风不存、传统难续。
如果亲子鉴定只是用来满足人们对生物学知识的好奇心,倒是法律无虞之事。问题是,DNA检验技术的普及化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亲子鉴定热,实际上在动摇许多人所追求的婚姻家庭关系稳定性。因为经鉴定证明亲子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后,父亲们在痛苦之余产生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冲动,往往就是不承认这个子女。在一个发生在西部的案例中,张某经亲子鉴定发现养育17年的女儿竟不是亲生,遂与其母离婚,并要求女儿的亲生父亲吴某给予赔偿。法院支持了张某的诉讼请求,判决吴某赔偿张某精神抚慰金1万元,并赔偿张某17年来垫付的子女抚养费6万余元。在另一个发生在东部的案例中,离异后争得儿子抚养权的父亲,在单独养育儿子10年后,经亲子鉴定发现儿子不是亲生,遂要求该子由其母亲抚养,并请求其母返还抚养费1.8万元,亦获得了法院的支持。法官们支持那些受欺骗并自认为是白养他人子女的父亲们的索赔请求,是可以理解并且是有所凭据的。然而,进一步的思考却在提示我们:这种支持或许倒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所在。
在支持名义父亲们诉讼请求的法官看来,只有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才是成立亲子关系的事实基础,如果既无血缘关系也未办理收养手续,名义上的父亲就没有抚养非亲生子女的义务。父亲们在受欺骗的情况下抚养非亲生子女,其抚养行为不是出于真实意愿,乃是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为他人抚养子女,因而有权请求非亲生子女的亲生父母返还垫付的抚养费用。可见,在这类案件的处理中,无因管理规则进入了法官的推理判断过程。但是,在这些非亲生子女还是一个未成年人时,就因一笔垫付费用的交付而被更换了父亲与家庭,对于这些同样是无辜且无助的非亲生子女来说,无因管理规则的适用是过于冷酷了。
在这些案件处理中,实际上存在着DNA决定社会关系的潜意识,并由此影响了案件处理规则的选择。依据DNA决定论,除了收养关系之外,有DNA联系才能构成亲子关系,该生物学上的父亲就须承担子女的抚养义务;没有DNA联系就不能形成亲子关系,社会学上的名义父亲就没有抚养非亲生子女的义务。然而,如果基于这类案件的情形再做一些假设,就会发现DNA决定论所影响的思路及案件处理规则实际上欠缺一般合理性。旨在使亲子关系社会效果合理化的法律,在其制度设计时需要更为复杂的价值衡量,而DNA实际上不能充任决定法律价值取向的单独依据。
假设之一:如果经亲子鉴定发现子女不是亲生,但却不知其亲生父亲是谁,或者其亲生父亲死亡或下落不明,此时非亲生子女的母亲也死亡或下落不明,在此情形下,名义父亲可否拒绝继续抚养未成年的非亲生子女。合理的制度选择是,名义父亲应当继续抚养未成年的非亲生子女,否则该子女将处于被遗弃的境地。设定亲子关系的法律规范时,在保障父系DNA遗传的延续性和保障子女成长环境的安全性之间,法律宁可选择后者,因为前者依赖于个人的本事,后者才需要法律的支持。尽管对非亲生子女的出生与抚养不是出于名义父亲的真实同意,但是未成年人获取生活保障的权利要大于成年人对其出生有真实同意的权利。如果妻子在丈夫强烈反对或不知晓的情况下生下孩子,丈夫在子女出生后仍应承担抚养义务。妻子隐瞒子女DNA的来源固然是一种巨大的欺骗,但这种欺骗虽大却不足以解除对非亲生子女的抚养义务,因为欺骗名义父亲的是其配偶而不是非亲生子女。人们在接受婚姻时,就必须接受婚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各种后果,包括配偶生产的DNA来源不明的子女。妻子不忠实,丈夫尽可以提出离婚,而非亲生子女却不应承担不忠实母亲行为的不利后果。既然非亲生子女在其婚姻存续期间出生,名义父亲就要承担抚养该子女的责任,而不能以失察配偶为由免责。在名义父亲与非亲生子女之间进行利益衡量时,法律不应倾向于失察配偶行为的父亲,而应倾向于对自己的出生没有任何选择与责任的未成年非亲生子女。
假设之二:非亲生子女成年后,经亲子鉴定发现与其父亲没有DNA联系,在此情形下,子女可否在偿还非亲生父亲所垫付的抚养费后,与其解除关系并不再承担赡养义务。现实中,大多是父亲带着未成年子女做亲子鉴定,而鲜有带着成年子女做亲子鉴定的,其间多少有点成年人的凌弱心态。实际上,子女当然也可以带着老父亲做亲子鉴定,既然名义父亲有权拒绝抚养非亲生子女,并可索讨垫付的抚养费用,子女当然可以在偿付抚养费用后不再承担对非亲生父亲的赡养义务;而且经过计算后,如果已经支付的赡养费用多于抚养费用,还可以要求非亲生父亲返还一部分赡养费用。显然,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处理规则,但这一规则却是拒绝抚养非亲生子女规则的合乎制度逻辑的推理结果,无亲子关系就没有抚养义务与没有亲子关系就没有赡养义务,两者就是一个等价的规则。或许有人责备这些成年子女,在他人将其抚养成人后却忘恩负义地拒绝赡养他们的抚养者。可是,对那些拒绝抚养未成年非亲生子女的人来说,放弃对叫过他们父亲并且给予他们天伦之乐的非亲生子女的抚养责任,是否也应该受到责备。看来,如果给予受配偶欺骗的父亲们过多的同情,在处理其与非亲生子女的关系时,就会忽略更为基本的法理,即共同生活形成的关系在法律效力上要大于DNA决定的关系。或有人言,受欺骗并抚养了非亲生子女的是名义父亲,如果他愿意接受子女非所亲生的事实,则其与非亲生子女间就形成了收养关系,因此,成年后的非亲生子女不能单方免除对非亲生父亲的赡养义务。但是,为什么要把成就亲子关系的选择权只放在父亲一边,同样需要保护的非亲生子女也需要这种选择权。
假设之三:在发现子女非所亲生之后,如果名义父亲基于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情感以及维护家庭完整的意愿,仍愿意与非亲生子女保持父子关系,但子女的亲生父亲却以血缘关系为据要将其带走。此时,法院应当支持谁的请求?是支持生物学上的父亲,还是支持社会学上的父亲?如果按照DNA决定论,生物学上的父亲无疑处于有利地位,因为他与子女之间存在DNA联系,属于自然血亲。但是,如果支持生物学上的父亲带走子女的请求,就等于给当年破坏他人婚姻忠诚的人再次破坏他人家庭完整的机会。给了非亲生子女以家庭保护与抚育温暖的社会学上的父亲,其维护父子亲情和家庭完整的请求,是更值得同情和支持的。如果社会学上的父亲坚持留下非亲生子女,其应当拥有比生物学上的父亲更为优先的权利,因为基于社会关系提出的请求在法律效力上应当大于基于生物关系提出的请求。
看来,在名义父亲和非亲生子女之间,实际上存在一个比DNA联系更值得法律维系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基于名义父亲与非亲生子女母亲之间合法婚姻形成的家庭关系,以及在此家庭关系中名义父亲与非亲生子女之间的共同生活关系。维系这种社会关系只需法律给定一个说法,以构成法律上亲子关系的依据,而“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就是一个可供选择的理由。当然,未经名义父亲和亲生父亲的同意,恐怕是事实收养关系规则在法理上的缺陷,但这是立法政策可以取舍的问题。生物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人们之间的生物联系,以致我们不得不改变既往的婚姻家庭关系规则。通常认为血亲有自然血亲和拟制血亲两种之分,而人工授精和胚胎移植实际上导致第三种血亲的出现,即“视为自然血亲”,其与自然血亲不同的是,子女与父亲甚至父母双方之间没有DNA联系,此点倒与拟制血亲相同;其与拟制血亲不同的是,经人工授精、胚胎移植所生子女的社会学上的父亲,在法律上应当视为生父而不是养父,由人工授精或胚胎移植形成的亲子关系,除非经过合法的送养手续,否则不得单方或双方解除,此点倒与自然血亲相同。由于以DNA检验技术支持的亲子鉴定太过于容易,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稳定特别是未成年人的生活安全,因此,法律不妨将所有婚生子女包括非亲生子女均视为自然血亲,即使经亲子鉴定发现父亲与子女之间不存在DNA联系,双方均不得以此为由解除亲子关系。为了特别保护未成年人,法律应当尽量为未成年人找到一个父亲,因而可以赋予亲子鉴定以“加法效果”,当未成年人没有社会学上的父亲可依靠时,可以通过DNA鉴定寻找其生物学上的父亲,并让其承担抚养义务。
亲子鉴定在确定配偶是否忠诚方面是有力的,但在解决亲子关系方面却应当是有限的。我们是DNA决定的,但我们的思想及其指示下的行为却不是DNA决定的。即使在决定人们的社会角色时,DNA有时也是有限的。变性技术的出现,可以使DNA上判断为男性的人在社会上充任女性的角色,或者是相反。可见性别亦有自然性别和拟制性别之分,这就是技术带给我们法律认知上的变化。技术所不能改变的,是我们对人生的热爱和对弱小的关怀。只是法律对这些人生热爱的保护不可能周延,对于满怀延续自己DNA遗传期望的准父亲们,法律只能告诉他:你要努力着并要小心点。
作者: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陈 甦
发布时间:2006-10-12
我们离开母系社会的时间已经不短了,但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情形可能依然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父亲想做亲子鉴定的原因。用DNA检验技术证明血缘关系,只需花上千余元,再抽取些许静脉血,即可检验,其正确率达到99%以上。DNA检验技术所具有的准确率高、方法简便、成本费用低等特点,使其成为今天的父亲们用来破解其妻不忠、其子不亲之疑惑的首选技术措施。可见,最新颖的科技成果往往被用来解决我们最古老的焦虑,好古者不必担心古风不存、传统难续。
如果亲子鉴定只是用来满足人们对生物学知识的好奇心,倒是法律无虞之事。问题是,DNA检验技术的普及化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亲子鉴定热,实际上在动摇许多人所追求的婚姻家庭关系稳定性。因为经鉴定证明亲子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后,父亲们在痛苦之余产生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冲动,往往就是不承认这个子女。在一个发生在西部的案例中,张某经亲子鉴定发现养育17年的女儿竟不是亲生,遂与其母离婚,并要求女儿的亲生父亲吴某给予赔偿。法院支持了张某的诉讼请求,判决吴某赔偿张某精神抚慰金1万元,并赔偿张某17年来垫付的子女抚养费6万余元。在另一个发生在东部的案例中,离异后争得儿子抚养权的父亲,在单独养育儿子10年后,经亲子鉴定发现儿子不是亲生,遂要求该子由其母亲抚养,并请求其母返还抚养费1.8万元,亦获得了法院的支持。法官们支持那些受欺骗并自认为是白养他人子女的父亲们的索赔请求,是可以理解并且是有所凭据的。然而,进一步的思考却在提示我们:这种支持或许倒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所在。
在支持名义父亲们诉讼请求的法官看来,只有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才是成立亲子关系的事实基础,如果既无血缘关系也未办理收养手续,名义上的父亲就没有抚养非亲生子女的义务。父亲们在受欺骗的情况下抚养非亲生子女,其抚养行为不是出于真实意愿,乃是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为他人抚养子女,因而有权请求非亲生子女的亲生父母返还垫付的抚养费用。可见,在这类案件的处理中,无因管理规则进入了法官的推理判断过程。但是,在这些非亲生子女还是一个未成年人时,就因一笔垫付费用的交付而被更换了父亲与家庭,对于这些同样是无辜且无助的非亲生子女来说,无因管理规则的适用是过于冷酷了。
在这些案件处理中,实际上存在着DNA决定社会关系的潜意识,并由此影响了案件处理规则的选择。依据DNA决定论,除了收养关系之外,有DNA联系才能构成亲子关系,该生物学上的父亲就须承担子女的抚养义务;没有DNA联系就不能形成亲子关系,社会学上的名义父亲就没有抚养非亲生子女的义务。然而,如果基于这类案件的情形再做一些假设,就会发现DNA决定论所影响的思路及案件处理规则实际上欠缺一般合理性。旨在使亲子关系社会效果合理化的法律,在其制度设计时需要更为复杂的价值衡量,而DNA实际上不能充任决定法律价值取向的单独依据。
假设之一:如果经亲子鉴定发现子女不是亲生,但却不知其亲生父亲是谁,或者其亲生父亲死亡或下落不明,此时非亲生子女的母亲也死亡或下落不明,在此情形下,名义父亲可否拒绝继续抚养未成年的非亲生子女。合理的制度选择是,名义父亲应当继续抚养未成年的非亲生子女,否则该子女将处于被遗弃的境地。设定亲子关系的法律规范时,在保障父系DNA遗传的延续性和保障子女成长环境的安全性之间,法律宁可选择后者,因为前者依赖于个人的本事,后者才需要法律的支持。尽管对非亲生子女的出生与抚养不是出于名义父亲的真实同意,但是未成年人获取生活保障的权利要大于成年人对其出生有真实同意的权利。如果妻子在丈夫强烈反对或不知晓的情况下生下孩子,丈夫在子女出生后仍应承担抚养义务。妻子隐瞒子女DNA的来源固然是一种巨大的欺骗,但这种欺骗虽大却不足以解除对非亲生子女的抚养义务,因为欺骗名义父亲的是其配偶而不是非亲生子女。人们在接受婚姻时,就必须接受婚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各种后果,包括配偶生产的DNA来源不明的子女。妻子不忠实,丈夫尽可以提出离婚,而非亲生子女却不应承担不忠实母亲行为的不利后果。既然非亲生子女在其婚姻存续期间出生,名义父亲就要承担抚养该子女的责任,而不能以失察配偶为由免责。在名义父亲与非亲生子女之间进行利益衡量时,法律不应倾向于失察配偶行为的父亲,而应倾向于对自己的出生没有任何选择与责任的未成年非亲生子女。
假设之二:非亲生子女成年后,经亲子鉴定发现与其父亲没有DNA联系,在此情形下,子女可否在偿还非亲生父亲所垫付的抚养费后,与其解除关系并不再承担赡养义务。现实中,大多是父亲带着未成年子女做亲子鉴定,而鲜有带着成年子女做亲子鉴定的,其间多少有点成年人的凌弱心态。实际上,子女当然也可以带着老父亲做亲子鉴定,既然名义父亲有权拒绝抚养非亲生子女,并可索讨垫付的抚养费用,子女当然可以在偿付抚养费用后不再承担对非亲生父亲的赡养义务;而且经过计算后,如果已经支付的赡养费用多于抚养费用,还可以要求非亲生父亲返还一部分赡养费用。显然,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处理规则,但这一规则却是拒绝抚养非亲生子女规则的合乎制度逻辑的推理结果,无亲子关系就没有抚养义务与没有亲子关系就没有赡养义务,两者就是一个等价的规则。或许有人责备这些成年子女,在他人将其抚养成人后却忘恩负义地拒绝赡养他们的抚养者。可是,对那些拒绝抚养未成年非亲生子女的人来说,放弃对叫过他们父亲并且给予他们天伦之乐的非亲生子女的抚养责任,是否也应该受到责备。看来,如果给予受配偶欺骗的父亲们过多的同情,在处理其与非亲生子女的关系时,就会忽略更为基本的法理,即共同生活形成的关系在法律效力上要大于DNA决定的关系。或有人言,受欺骗并抚养了非亲生子女的是名义父亲,如果他愿意接受子女非所亲生的事实,则其与非亲生子女间就形成了收养关系,因此,成年后的非亲生子女不能单方免除对非亲生父亲的赡养义务。但是,为什么要把成就亲子关系的选择权只放在父亲一边,同样需要保护的非亲生子女也需要这种选择权。
假设之三:在发现子女非所亲生之后,如果名义父亲基于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情感以及维护家庭完整的意愿,仍愿意与非亲生子女保持父子关系,但子女的亲生父亲却以血缘关系为据要将其带走。此时,法院应当支持谁的请求?是支持生物学上的父亲,还是支持社会学上的父亲?如果按照DNA决定论,生物学上的父亲无疑处于有利地位,因为他与子女之间存在DNA联系,属于自然血亲。但是,如果支持生物学上的父亲带走子女的请求,就等于给当年破坏他人婚姻忠诚的人再次破坏他人家庭完整的机会。给了非亲生子女以家庭保护与抚育温暖的社会学上的父亲,其维护父子亲情和家庭完整的请求,是更值得同情和支持的。如果社会学上的父亲坚持留下非亲生子女,其应当拥有比生物学上的父亲更为优先的权利,因为基于社会关系提出的请求在法律效力上应当大于基于生物关系提出的请求。
看来,在名义父亲和非亲生子女之间,实际上存在一个比DNA联系更值得法律维系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基于名义父亲与非亲生子女母亲之间合法婚姻形成的家庭关系,以及在此家庭关系中名义父亲与非亲生子女之间的共同生活关系。维系这种社会关系只需法律给定一个说法,以构成法律上亲子关系的依据,而“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就是一个可供选择的理由。当然,未经名义父亲和亲生父亲的同意,恐怕是事实收养关系规则在法理上的缺陷,但这是立法政策可以取舍的问题。生物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人们之间的生物联系,以致我们不得不改变既往的婚姻家庭关系规则。通常认为血亲有自然血亲和拟制血亲两种之分,而人工授精和胚胎移植实际上导致第三种血亲的出现,即“视为自然血亲”,其与自然血亲不同的是,子女与父亲甚至父母双方之间没有DNA联系,此点倒与拟制血亲相同;其与拟制血亲不同的是,经人工授精、胚胎移植所生子女的社会学上的父亲,在法律上应当视为生父而不是养父,由人工授精或胚胎移植形成的亲子关系,除非经过合法的送养手续,否则不得单方或双方解除,此点倒与自然血亲相同。由于以DNA检验技术支持的亲子鉴定太过于容易,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稳定特别是未成年人的生活安全,因此,法律不妨将所有婚生子女包括非亲生子女均视为自然血亲,即使经亲子鉴定发现父亲与子女之间不存在DNA联系,双方均不得以此为由解除亲子关系。为了特别保护未成年人,法律应当尽量为未成年人找到一个父亲,因而可以赋予亲子鉴定以“加法效果”,当未成年人没有社会学上的父亲可依靠时,可以通过DNA鉴定寻找其生物学上的父亲,并让其承担抚养义务。
亲子鉴定在确定配偶是否忠诚方面是有力的,但在解决亲子关系方面却应当是有限的。我们是DNA决定的,但我们的思想及其指示下的行为却不是DNA决定的。即使在决定人们的社会角色时,DNA有时也是有限的。变性技术的出现,可以使DNA上判断为男性的人在社会上充任女性的角色,或者是相反。可见性别亦有自然性别和拟制性别之分,这就是技术带给我们法律认知上的变化。技术所不能改变的,是我们对人生的热爱和对弱小的关怀。只是法律对这些人生热爱的保护不可能周延,对于满怀延续自己DNA遗传期望的准父亲们,法律只能告诉他:你要努力着并要小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