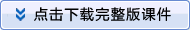民法中的人:抽象人还是具体人
常鹏翱
人民法院报2005年5月30日
俗话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但俗语有时也不能恰当地反映现实,我们且看这样一则实例:鳏夫张老汉无儿无女,每天以饲弄爱犬“欢欢”作为人生最大乐事和精神寄托,但天有不测风云,一天,在老汉牵着“欢欢”遛弯时,醉酒司机违章驾车将“欢欢”轧死,老汉痛不欲生,要求肇事者除赔偿经济损失外,还要赔偿其精神损害。
当代的法律人都知道,老汉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不能为法院所支持,因为在我国民事法律体系内,“欢欢”属于权利客体之“物”,一旦它受到物理上的损害,其主人只能得到经济利益补救,对由此而产生的情感利益损害,法律是爱莫能助的。这种逻辑在法律人看来很自然,但法律的门外汉未必会这样看待,他们基于朴素的生活情理,肯定会纳闷,法律为何不救助精神如此痛苦的老汉呢?看来,法网还是有漏洞啊!
显见,法律和情理在此出现了分离。那么,民法为何要采取这样的应对策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审视民法是如何看待“人”的。我们知道,商品经济形态是民法存续的根本,而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商品和人员具有高度的流动性,“陌生人”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这些陌生人均为利益和利润而奔波,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们之间的交往工具不是各自的个性、情感等具体要素,而是能被一般化的经济媒质。著名社会学家腾尼斯对此有形象的描述:商业和交往的物质基础,把所有的个人招集在广场上,磨掉他们的差异,“给大家以相同的表情、相同的语言和发音、相同的货币、相同的贪婪、相同的好奇心 ——抽象的人即一切机器中最最人为的、最有规则性的、最精密的机器,被设计和发明出来了,而且可以直观,犹如在冷静的、明晰的、寻常的真理中的一个幽灵。”
民法在涉及“物”的领域,反映了上述这种抽象人,他要么是“经济人”,眼里只有经济效用,没有情感波动;要么是,理性人”,心中只有谨慎准则,没有感性流露。德国民法典中的人形象就是“人们能够指望他们具有足够的业务能力和判断能力,在以契约自由、营业自由和竞争自由的基础上成立的市民盈利团体中理智地活动并避免损失”。台湾著名民法学家苏永钦先生更将这样的人界定为“始终是无色无味,不笑不愠”。就这样,人对物而得到愉悦或感伤之情、怀念或怜悯之心,因为没有经济媒质,就被民法过滤掉,剩下的只是抽象的人和物搭配起来的法律关系。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张老汉对“欢欢”情感利益不受民法保护了。
然而,与上述图像不同,在人身权范畴中,民法活生生地把现实之人临摹下来,这里的人有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一旦其情感世界受到创伤,相应的补救措施随即而来,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等不一而足,目的在于抚慰人受伤的心灵。这里的人是具体人,是生活在现实之中、不能用生硬单一的标准予以刻画的你我这样的肉体凡身,是有血有肉、性情十足的“情感人”或者“感性人”。虽然具体人与抽象人一样,有渴求平等正义、交换正义和金钱救济的欲望,但其拥有的情感世界恰恰是抽象人所缺失的部分。
两相对比,在涉及“物”的领域,民法抽取了具体生活个体角色的情感要素,人因此成了抽象人;而在人作为主体的领域(人格和身份),民法中人的则是具体人。这种形象的反差显得过于突兀,这不能不让人反思,抽象人的形象真的合理吗?
其实,现实中的人有基于具体人本性而自发的、但不同于民法构建的需求,这就是人对物的感情,请想想惟妙惟肖地折射这种关系的“敝帚自珍”、“爱屋及乌”等谚语,在这简单的生活现实面前,抽象人必须恢复其真实面目,使之成为怀有情感的每一个具体的人。客观地说,情感是难以捉摸的东西,它要受制于具体个体的经历、性情等特质要素,在现实中,很难用统一的标准来界定情感要素,“情人眼里出西施”的个性标准可能用的更多也更普遍。在这里,物的经济属性退居其次,甚至完全被人的情感所遮掩,物因此构成了抽象人通向完整之人的桥梁。在此,活生生的例子正是张老汉对“欢欢”的感情,而外人肯定不会对“欢欢”产生这种感情的。
如果民法将具体人的形象扩展到人之外的物的领域,那么,物的毁损完全可能导致受害人精神利益的不完满,这种精神损害在表现和性质上与因为人身权受侵害而产生的精神损害并无差别,同样表现为气愤、悲伤、痛苦、懊悔、忧愁、恼怒等精神上的异常和缺陷。既然在人身权领域中,具体人的情感利益要受保护,那么,具体人在物的领域中的情感利益不受保护,就不那么正当了。
正因为“欢欢”之类的物具有将抽象人面目具体化的特质,民法当然有必要揭开张老汉的“抽象人”面纱,让其恢复本有面貌。如果仍然套用抽象人的形象来衡量人的情感利益,那么,“欢欢” 之死给张老汉带来的精神震撼,会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民法不能提供完全救济的缺憾,在此,我们看到民法刚性过剩、柔性不足的尴尬,它没有超越物的经济层面,透视到物蕴涵的人的情感价值。这当然意味着,民法对人之形象所采用的抽象标准失去了效用,经济效率要为细腻情感让步。至此,民法中的人的形象发生了改变,其不再是单纯的抽象人,即使在物的领域,人也必须是抽象人和具体人的同一体,只有这样,才能增加民法控制现实生活的有效性和严密性。
常鹏翱
人民法院报2005年5月30日
俗话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但俗语有时也不能恰当地反映现实,我们且看这样一则实例:鳏夫张老汉无儿无女,每天以饲弄爱犬“欢欢”作为人生最大乐事和精神寄托,但天有不测风云,一天,在老汉牵着“欢欢”遛弯时,醉酒司机违章驾车将“欢欢”轧死,老汉痛不欲生,要求肇事者除赔偿经济损失外,还要赔偿其精神损害。
当代的法律人都知道,老汉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不能为法院所支持,因为在我国民事法律体系内,“欢欢”属于权利客体之“物”,一旦它受到物理上的损害,其主人只能得到经济利益补救,对由此而产生的情感利益损害,法律是爱莫能助的。这种逻辑在法律人看来很自然,但法律的门外汉未必会这样看待,他们基于朴素的生活情理,肯定会纳闷,法律为何不救助精神如此痛苦的老汉呢?看来,法网还是有漏洞啊!
显见,法律和情理在此出现了分离。那么,民法为何要采取这样的应对策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审视民法是如何看待“人”的。我们知道,商品经济形态是民法存续的根本,而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商品和人员具有高度的流动性,“陌生人”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这些陌生人均为利益和利润而奔波,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们之间的交往工具不是各自的个性、情感等具体要素,而是能被一般化的经济媒质。著名社会学家腾尼斯对此有形象的描述:商业和交往的物质基础,把所有的个人招集在广场上,磨掉他们的差异,“给大家以相同的表情、相同的语言和发音、相同的货币、相同的贪婪、相同的好奇心 ——抽象的人即一切机器中最最人为的、最有规则性的、最精密的机器,被设计和发明出来了,而且可以直观,犹如在冷静的、明晰的、寻常的真理中的一个幽灵。”
民法在涉及“物”的领域,反映了上述这种抽象人,他要么是“经济人”,眼里只有经济效用,没有情感波动;要么是,理性人”,心中只有谨慎准则,没有感性流露。德国民法典中的人形象就是“人们能够指望他们具有足够的业务能力和判断能力,在以契约自由、营业自由和竞争自由的基础上成立的市民盈利团体中理智地活动并避免损失”。台湾著名民法学家苏永钦先生更将这样的人界定为“始终是无色无味,不笑不愠”。就这样,人对物而得到愉悦或感伤之情、怀念或怜悯之心,因为没有经济媒质,就被民法过滤掉,剩下的只是抽象的人和物搭配起来的法律关系。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张老汉对“欢欢”情感利益不受民法保护了。
然而,与上述图像不同,在人身权范畴中,民法活生生地把现实之人临摹下来,这里的人有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一旦其情感世界受到创伤,相应的补救措施随即而来,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等不一而足,目的在于抚慰人受伤的心灵。这里的人是具体人,是生活在现实之中、不能用生硬单一的标准予以刻画的你我这样的肉体凡身,是有血有肉、性情十足的“情感人”或者“感性人”。虽然具体人与抽象人一样,有渴求平等正义、交换正义和金钱救济的欲望,但其拥有的情感世界恰恰是抽象人所缺失的部分。
两相对比,在涉及“物”的领域,民法抽取了具体生活个体角色的情感要素,人因此成了抽象人;而在人作为主体的领域(人格和身份),民法中人的则是具体人。这种形象的反差显得过于突兀,这不能不让人反思,抽象人的形象真的合理吗?
其实,现实中的人有基于具体人本性而自发的、但不同于民法构建的需求,这就是人对物的感情,请想想惟妙惟肖地折射这种关系的“敝帚自珍”、“爱屋及乌”等谚语,在这简单的生活现实面前,抽象人必须恢复其真实面目,使之成为怀有情感的每一个具体的人。客观地说,情感是难以捉摸的东西,它要受制于具体个体的经历、性情等特质要素,在现实中,很难用统一的标准来界定情感要素,“情人眼里出西施”的个性标准可能用的更多也更普遍。在这里,物的经济属性退居其次,甚至完全被人的情感所遮掩,物因此构成了抽象人通向完整之人的桥梁。在此,活生生的例子正是张老汉对“欢欢”的感情,而外人肯定不会对“欢欢”产生这种感情的。
如果民法将具体人的形象扩展到人之外的物的领域,那么,物的毁损完全可能导致受害人精神利益的不完满,这种精神损害在表现和性质上与因为人身权受侵害而产生的精神损害并无差别,同样表现为气愤、悲伤、痛苦、懊悔、忧愁、恼怒等精神上的异常和缺陷。既然在人身权领域中,具体人的情感利益要受保护,那么,具体人在物的领域中的情感利益不受保护,就不那么正当了。
正因为“欢欢”之类的物具有将抽象人面目具体化的特质,民法当然有必要揭开张老汉的“抽象人”面纱,让其恢复本有面貌。如果仍然套用抽象人的形象来衡量人的情感利益,那么,“欢欢” 之死给张老汉带来的精神震撼,会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民法不能提供完全救济的缺憾,在此,我们看到民法刚性过剩、柔性不足的尴尬,它没有超越物的经济层面,透视到物蕴涵的人的情感价值。这当然意味着,民法对人之形象所采用的抽象标准失去了效用,经济效率要为细腻情感让步。至此,民法中的人的形象发生了改变,其不再是单纯的抽象人,即使在物的领域,人也必须是抽象人和具体人的同一体,只有这样,才能增加民法控制现实生活的有效性和严密性。